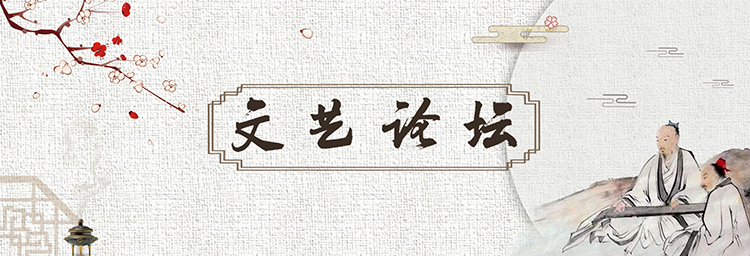

启蒙的学术与学术的启蒙
——论张光芒的文学研究及批评实践
文/傅元峰
摘 要: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为张光芒学术志业所在,他关于启蒙精神的探微发幽,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同时构成了他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思想根基,使他在当代文学发展路向的考察中卓尔不群,颇有创见。就学术史而言,张光芒启蒙的学术也是对当代学术生态进行剖析的参照样本:当代学术界,急需一场学术启蒙,以破除学术封建,将文学研究引入一个真正的现代性领域。
关键词:张光芒;启蒙;学术生态
一
张光芒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是富有思想向度的,他也是处在启蒙的围困中的研究者。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批评家,他的敏锐性和活跃程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自觉地把文学研究置于文化危机、理论贫瘠的矫治视野。他的批评之“破”与理论之“立”是结合在一起并互为阐释的。
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位学者,他选择了启蒙的学理基础和思想向度,不吝惜将自身陷入一种类似宿命的启蒙的哲学围困。从张光芒目前已有的言说来看,启蒙的理论困惑还远远大于社会、时代拯救需求所赋予他的部分使命的现实实现。对于一个启蒙话语的持有者,如果持续启蒙的操守,这种困惑无疑将贯穿他的学术生命过程。启蒙的辩证法必将成为他学术生命的辩证法。
而关于启蒙的若干中国式的知识困惑,全部可以在张光芒的著作中得到完满的答案。由于他的踏实勤奋,任何关于启蒙的基础综述,也许都要在他已有的阅读和阐释的范围内重复。为了接近这位以启蒙为专攻术业的学者,还是需要归纳一些事实。启蒙驳杂的思想体系既包含作为历史具象的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包含围绕人类进步而不断积淀的诸多哲学原质。在现代中国,启蒙的移植和自我生长具有双向的承传关系:它面向前现代性状态下的革命与建设冲动,相似于西方启蒙者面向中世纪的暗夜认定与战叫;它也将知识的力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用人类文明积累的真知照亮中国人灵魂的夜空,让他们听从理性和人性的召唤,告别蒙昧。两者在20世纪中国思想进程中杂糅为复合式的中国启蒙思想。中国启蒙的学理生长是开放的,作为某一特定思想潮流的启蒙,其能指随学术史的推延而不断被扩充,终于成为一个不能被确切定义的概念之一。近代中国对启蒙的话语选择带有明显的社会动机,并与意识形态有暧昧的重叠。因此,启蒙的话语归属并不十分确定。当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逐渐获得现代塑型的时候,启蒙就因循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衍生方向,依存在并不十分清晰的知识分子话语范畴中,与泥沙俱下的20世纪中国本土思想生成的困境伴随始终。
在此前提下,张光芒与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意识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现代性获得是可疑的,从而竭力在启蒙的思想谱系上续写新的内涵。从理性的呼唤到启蒙的“道德形而上”的招魂,从启蒙哲学的本体论尝试再到“新启蒙主义”[1]之理论方法的演练,这种不断的理论刷新带来的思想原创意义值得珍视。在现代中国,文化影响的力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相互配合,思想的原生土壤遭到了彻底破坏。儒、释、道等中国本土哲学元素流失,中国典籍的文化支撑力量几度成为知识分子文化血液净化时竭力驱除的异己成分。知识分子所为经常抹上强烈的功利色彩,他们大多不能超越历史情境,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范畴的提问提升到思想原生的领域。启蒙在中国语境内的功利化使它越来越脱离思想的基本特质,而成为社会历史知识的单调的物质积累,不再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2]的进步思想。张光芒的学术理路清晰地绘制出功利性启蒙之圉的突围路线,以个体的努力标示出中国思想的某种富有生机的生成现状。
二
正是将思维纳入启蒙的理论深化和不断的自我驳诘,才使张光芒成为清醒的思想者,使他对现象的评价屡有中的之见。比如,他认为“功利性极强的启蒙文学”反而“尴尬地陷于启蒙功能的无效缺失状态”[3];再如他认为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文化与文学转型从深层来说,经历了一个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4]的哲学转型,这些精辟的见解带有浓厚的辩证色彩,表明了他对启蒙和当代文学关系的精确认知。另如,他以五万字的篇幅对当下中国道德文化的本质及其现实逻辑规律的论证和揭示,让人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5]
他在哲学层面的文学观望并没有将他引入绝望,他尝试用自己的理论探索构建中国文学研究的哲学内涵,体现出思想重建的责任担当:“尽管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在西方冲击下才由知识精英明确提出的,但现代性目标的实现只能诉诸本土现实的社会力量,而无论这种力量是否已经成熟得足以承载起这一目标。”[6]从启蒙的突围,到本土话语重建,再到思想史向度上的现代性诉求,张光芒意识到话语殖民结束的时代应该尽早到来,他的理论创新热情体现在他的研究活动中,未曾有所间歇。
启蒙的专门探究从哲学高度上激荡出他复杂的研究兴趣点:道德形而上、文学转型研究、自恋主义、中产阶级写作、都市文学、“80后”现象[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论说风格切中当前文学的根本问题和敏感问题。在他的笔下,许多问题从学术问题的提出到学术话语的建构和学术思路的展开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在不期然间触到人们关心而难以找到切入点的话题。如他以“人心文化”的种种异化与畸变来概括当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8]再如他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既与199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也有着一些新型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学术话语的包装、与市场及政治的成功对接,以及思维方式与话语策略的转换。而新话语产生的动因与根源在于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化立场在当下的尖锐冲突,学术原创能力的低下等等。这股新的民族主义文化潮流隐含着一系列令人警惕的价值乖谬;其一表现为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其二表现为历史与文化上的“宏大叙事”的复兴;其三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大众愚昧心态与虚妄性格;其四则表现为整体性文化思维的复活。[9]显而易见,他一直保持着创新的活力与学术目光的敏锐。那些富有活力的研究和启蒙的历史总结与理论建设,共同构成张光芒学术研究的主体部分。它说明,启蒙的理论给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资源,而且也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学术基础。
启蒙所标志的张光芒的学术个性使他作为一名1960年代出生学人的学术锋芒展露出来。他的学术生命注定要融合文学研究、思想探险和哲学体悟等多种元素,而思想深度和思辨能力,哲学体悟与本体界说等环节恰恰是“60后”学人的知性强势。张光芒宽阔的学术视野与较强的学术话语更新能力使他成为颇受学术界关注的个体。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偏颇和哲学匮乏来说,这种学术存在无疑是值得珍惜的。
张光芒也同时处于学术年轮的悖谬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学术年轮显示出的学理更新值得关注。现有的研究现状表明,理论话语权逐渐在学科研究版图上获得世俗的学术资源控制权,学统的形成、话语权的争夺与意识形态成功的学术控制,构成当代中国恶劣的学术生态格局。在这个恶劣的学术环境中,一位学者如何摆脱场强作用,在学术权力的侵蚀力量中维持学术自足,坚守自我价值立场,逐渐成为学术生命延续的艰难课题。由于学科结构的前现代性特征,学术霸权已经体现为意识形态控制与学术话语权持有者的协作关系。这使得学科研究的张力外化为社会关系,而非学理对话,并导致了学术激情的变异和萎缩。张光芒已有的学术成果展示他对纯粹的学术权力的控制法则,这样的研究无疑将促进学术研究的正常生态环境的形成。
中国学术界缺乏对学术生态环境的深究。尽管思想的社会环境诉求并不绝对与思想生成有重要关系,但是,学术群落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体认和思想进程关系重大。往学术史的纵深处看,张光芒的学术生存背景,是代际关系必将被引入学科史研究的学术原始积累期。生于60年代,在学科代际相连的树状结构图中,他属于学术话语的创新领域和新生群落。由于学术领域的家族控制特征和亲缘意识,60年代学人与50年代及50年代前学人的关系具有相因相克的矛盾性。这使得60年代人的学术隆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抑和遮蔽。在这种环境中,张光芒依靠学术自身的话语力量,以学术探索的激情和学术对话与争鸣的魄力,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生命力。他呼告学术界:“由于中国现代性的求索历程是由许多思想家、美学家、文学家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言论与其内涵相互作用而显示出来的总体性的逻辑整合趋向,因而切忌对不同论者不同观点孤立看待,否则就会只看到矛盾悖论,而无法加以梳理。”[10]他所意识到的无法厘定的矛盾恰是当代学术研究的症结所在。在中国学界,发生过较多争鸣,然而,真正形而上层面的思想对话非常少。“新时期”以来的大多学术论争,都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或者说,当代文学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学理层面对话的学术素养,除了谩骂和自说自话的呓语外,对话与交流的学术争鸣并没有真正形成。张光芒引发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论争[11],可算作是较为成形的一次学术论争。事实上,论争的理论含量与对话的实质成果让所有参与的人都体验到了理论探险的快乐。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学术构成的代际特征将随着“60后”“70后”乃至“80后”学人的渐次登场而逐渐明了。在学术承传与演进中,学术观念的冲突、理式的整合必然将使现代文学学术史变得惊心动魄,富于悬念。年轻学者的学术结构更加科学和完备,同时也将沾染更多的学术体制的痕迹。这和以上时代的学人所感受的体制的宿命有所不同。老知识分子反抗体制,然而这也正是庸俗启蒙的悖论之一——他们所受的体制压迫已经在他们的文化承传中有所感染,这导致了极权的反对者当中有一批恰恰是新霸权的持有者。“跑点”“跑项目”“打招呼”的学术封建特征,正和“跑官”的文化心理实质相似。体制的倾轧在年轻学者身上体现为学术理路的科技理性方式的束缚。随着学术权力原始割据期的结束,在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体制反思意识和自反意识之前,庸俗学术甚至权术对年轻学者的影响将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启蒙研究,其中的学术启蒙必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核心环节。像很多60年代学人一样,学术权力的持有方式将成为一种抉择。笔者很乐意看到,张光芒的学术生命也将以他的方式接受这种测试,并选择启蒙话语向知识分子自我灵魂考验的一次勇敢的学理延伸,将自己的启蒙研究引入拯救学术危机的学术启蒙场域。
三
在知识分子与体制合谋,分配学术的物质资源,并接受体制的形式主义的检验的态势下,学术反思势在必行。学院派知识分子已被完整纳入这个学术流程中。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评析蔡元培“教育独立”的倡导时,陈平原认为20世纪中国学人很少考虑“政学分途的设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12]。政学合一的现状导致学术权力的行政色彩过分浓厚,学术承传主要体现为学术资源的权力割据,形成学术圈地运动。学术权力与学术利益相联系,学术权力的掌握者依照学术权力攫取学术利益,将价值立场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放在脑后。知识秩序和学术评价的权力动机导致了伪问题的生成和伪学术的泛滥。张光芒对启蒙领域的坚守与拓展,使他的学术研究长葆问题意识,有现实关注的现场感,但又往往能使现象与问题的实质水落石出,形成理论回馈。同时,启蒙的现代性呼应使他能够对学术权力保持一些警惕,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品与学品的双重进步。
面对当代学术危机,张光芒有充分的学术自觉,他是一位批评思想的追寻者。《启蒙论》所透射的学术含量和学术意义是丰厚的,它的学术价值正逐渐被学界发掘和认同。《启蒙论》密集的思辨和独特的话语结构体现出张光芒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基础和天赋。作者的知识结构相对同代学人而言较为完整,而且,难得的是他的思维形态是基于对文学现实的不懈的形而上探索。当代文学研究的哲学匮乏和思想原生物的缺失为张光芒的学术生命提供了一个贫瘠的背景,让他的生机和潜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点在他有关中国式的“混沌的现代性”[13]以及中国启蒙之“情理激荡”[14]理论的原创性探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思想衍生和哲学创新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学术史主要是文化影响史。理论译介和思想的趣味维系于西方,对话的氛围不浓,接受的热情高涨。这种学术影响的待哺心理有其矛盾性。一方面,它形成了积极的学术理路引导,促进了阻滞状态下的学术更新;另一方面,它吞噬了学者关注本土思想的精力和热情,使年富力强的学者陷入译介的迷狂之中。在译介热中,学术前沿被重组为一个无机的域外思潮的知识系统。这也正是张光芒自觉的和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所说的当下性追求的基于理论原创性的当下性……必须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理论界缺少‘元话语’的局面。”[15]
思想原生物的稀缺和学术积累的粗放经营局面使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混杂的状态。一次性研究、重复研究很多,没有体现学术承传与生长的有机特征。更多的研究者在进行域外理论视角的文学攀岩游戏,或者仅仅生吞活剥这些理论,将文学批评牵引到虚妄的境地。张光芒的学术成长表明,他努力让自己脱离这个嗷嗷待哺的学术病儿群落。正是由于类似于《启蒙论》的学术基础,张光芒的文学批评有其思想基础。唯其如此,当他发现莫言欲望叙事充斥着“对母性的勒索”[16]、张炜小说表现出从形而上到而下的轮回[17],当他揭示出更多被冠之“民间立场”的作家恰恰体现出“伪民间”[18]的叙事伦理的时候,不能不让人强烈感受到一种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思想力度,以及批评之“破”与理论之“立”之间相互激荡的审美张力。
他对文学现实的关注角度和言说方式与酷评者有所不同。纵向离析诸多文学酷评家,可以发现价值理念的混乱和理论根基的缺失,无根者无行、无知者无畏的批评现实让人担忧。而张光芒以自身研究的些许成果向学界证明,启蒙研究的最大成果正是在于,它以思想原生的试验行为规范了一个学者的学术理路与价值立场,并形成了稳固的批评根基。他充满忧虑地看到:“一些文学研究者感到了一种身份危机,一种学科的焦虑,他们担心的当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深化’,而是把这种转向作为一种越界。……对‘转向’问题的一系列焦虑其实主要来自于学科边界意识,一种形式主义化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对研究界某种传统秩序的维护。”[19]为此,他还尝试采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加强理论的深化与边界的拓展相结合的路径,并提出了带有个性特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概念。[20]对比处于学科焦虑中(没有这种焦虑则更加糟糕)的学者来说,张光芒的忧虑尤显其深刻性,这种忧虑颠覆性地刺痛了许多研究者。正如张光芒所意识到的那样,越界恐惧症不仅仅是一种新知面前的学术孱弱的表现,更是一场深刻的学术危机来临的征候。其症结在于,学界存在一种与前现代性特征、甚至是封建性特征极度相似的“传统秩序”。这是必须经由一场学术启蒙行动才能疗救的痼疾。从启蒙的向度看,张光芒学术示范的启蒙价值,也许更大于他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作为启蒙者,张光芒将如何拓展中国启蒙话语的理论可能性,又将如何以哲学围困的方式保持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充分张力,是他面临的关键问题。不管如何,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启蒙的功利性召唤依然充斥在他们的言说空间,救亡与启蒙的悖论被物质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合谋深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启蒙的学术依然是一种冒险。针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缺失与它所存有的严重问题,我想问询的是,张光芒们如何背负沉重的责任,突破庸俗启蒙的功用局限,把启蒙话语安置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守望范围,并将启蒙思想在中国文化语境内逼近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无论如何,对于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哲学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进程。
注释:
[1]张光芒:《“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4]张光芒:《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
[5]张光芒:《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跨学科视野中的当下中国道德文化及其现实逻辑》,《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第3期两期连载。
[6]张光芒:《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
[7]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及观点可分别参见张光芒:《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等。
[8]张光芒:《“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畸变——当下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
[9]张光芒:《民族主义文化思潮新面孔及价值乖谬》,《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4期。
[10]张光芒:《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研范式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11]2004年前后有二十几篇论文围绕这一争论发表见解,张光芒本人的相关论文被收入他的专著《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参见该书第四章“形而上启蒙与审美/道德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2页。
[13]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4]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页。
[15]张光芒:《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福建论坛》2006年第7期。
[16]张光芒:《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钟山》2007年第2期。
[17]张光芒:《天堂的尘落——对张炜小说道德精神的总批判》,《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8]张光芒:《“伪民间”与反启蒙》,《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19]张光芒:《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0]张光芒:《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构想及其必要性——以现当代文学学术史为例》,《云梦学刊》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傅元峰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