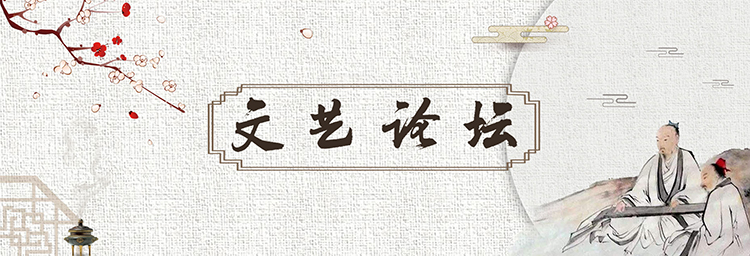

创意写作与高校作家培养
文/张永禄
摘 要:文化经济时代,审美成为重要的生产力,文化类的创作创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客观上要求高校文学专业重点培养文艺创作型的生产性人才,而非文艺批评家。新文科战略也要求高校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培养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来回应时代之需。我们要回归常识:作家可以培养,写作可以教授。美国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及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创意写作教育本土化任重道远,现存的几种模式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和体系化。
关键词:创意写作;生产性人才;文学专业;作家培养;中国模式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文化类的创作创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英、美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创意国家战略,把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作为国家发展的双驱动力。这意味着,高校文学专业以培养理论研究、批判者及教育者为主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需求。高校文学和艺术专业的培养重点应是艺术创作型人才,而不是文艺批评家。
这个转变对中文学科提出了很大挑战。长期以来,高校似乎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是:中文系做学术研究,不培养作家。作家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读书生活时提到,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罗常培先生认为“大学不培养作家,作家是社会培养的”[1]。19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曾经在上课时公开表示:“本专业不培养任何作家,请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马上转系。”[2]古典文学大家朱东润在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首节课上也告诫:“你们想写作自己业余做,复旦没有培养你们当作家的义务。”[3]近年来,陈平原、曹顺庆和葛红兵等一批学者反思中文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提出异议。曹顺庆就认为:“这些年,中文系没能很好地培养出作家,甚至就认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理直气壮的,甚至是错误的,应该好好反省。大学里当然能培养也应该培养作家。我个人认为,近些年来,没能很好地培养出作家,是我们中文系的失职。”[4]对于这两种相对的观点,需要我们站在时代高点,运用历史经验与写作逻辑相统一的观点,综合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大学教育的使命与职责定位以及写作(包括创意写作)的自身特点做出学理的思考,这有助于帮助我们清理不合时宜的认知和偏执误解,从而有助于大学健康有序发展创意写作教育,推动新时代作家观念更新与作家培养。
一、科学理解创意写作教育的内涵与使命
(一)创意写作的丰富内涵。“创意写作”的意指非常丰富,它可以是一门课程、一种理念,还可以是一门学科(专业),甚至是一种教育教学方法。“创意写作”作为一门课程,与“基础写作”等相对。2018年教育部专业目录中就把“创意写作”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选修课。欧美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已司空见惯,它们一般称其为“创意写作项目”(即纳入国家专项资助计划),这是创意写作发展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它帮助作家成为高校驻校作家,有稳定生活来源,能安心教书与写作。创意写作作为课程,与传统的基础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主要讲授的不是写作的基本理论,而是以写作工坊为标志性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如何提升写作的信心和开展具体的写作实践。
作为课程项目,欧美国家的创意写作课程开设非常普遍。教育主导者更多是把创意写作作为通识教育来开展,重点就是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名校非常重视写作课程,从大一到大四都开有类似创意写作课程,据苏炜教授介绍,写作课在耶鲁大学被誉为该校“金课”中的金课,是学生最难抢选的课程。[5]清华大学于2018年在全校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和借鉴了以上名校的做法。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高校(特别是理工科院校)意识到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不足,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其专业水平的长足发展,也对学生的整个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重视和开设写作课已经成为高校普遍共识。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有500多所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内在原因,但课程的普遍开设又导致了高校写作教育师资奇缺,这种情况和美国1940、1950年代创意写作教育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
创意写作还意味着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对创意写作抱有敌意的人经常质疑:“哪些写作是有创意的,哪些写作是没有创意的?”本质上讲,所有真正的写作都是有创造性的。美国著名创意写作教育学者唐纳利认为,“创意写作”和传统写作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的标志性的方法——工坊制教学方法,就像临床试验之于医学,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6]。通过工坊制教学,一群没有发表作品的学生教会了另一群从未发表作品的学生学会发表作品。工坊制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师徒制教学法,一群学生通过相互激发,相互讨论等集体合作互动的方式,迅速提升写作水平和能力,让作品达到发表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真正的主体,教师则是旁观者,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得到充分发展,积极性得到鼓励和保护。今天,工坊制模式越来越得到认可和推广,但对于创意写作来说,它是一种相对成熟而稳定的教学方法,可以作为其标志性教学法。
创意写作要发展,不可避免要成为专门学科,这是中外研究者的普遍共识。1937年爱荷华大学规定学生可以通过提交文学创作获得学位,标志着创意写作走上了学科化道路。据统计,至2017年,在以美国为主,包括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英语国家中,已有997个创意写作项目。其中,文学学士(BA)项目573个,艺术学士(BFA)项目41个,文学硕士(MA)项目148个,艺术硕士(MFA)项目218个,博士(PhD)项目49个。[7]我国高校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希望创意写作获得教育部认可,而不是自主增设或寄生其他学科门下。作为独立学科,创意写作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概念范畴与体系。在欧美国家出现了迈尔斯、麦克格尔、保罗·道森、大卫·莫利、格雷姆·哈珀、黛安娜·唐纳利等著名学者。以葛红兵、刁克利、王宏图、许道军、张永禄、谭旭东、陈晓辉、刘卫东、雷勇、高翔等一批学者在美国创意写作理论启发下,努力进行本土化建设,在潜能激发、创意成规、创意阅读、创意作者、创意思维、创意国家与社区、疗愈写作、数字化写作等方面进行探索。但目前基础研究刚起步,中国创意写作学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二)“创意写作”的使命。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其背后有一些相通的内涵与使命。从根本上说,创意写作是一种直面普通人创造力激发的教育改革运动。创意写作首先是源于美国的文学教育改革,其目的是改变欧洲古典学、修辞学和语文学等教育对当代人思想和情感造成的桎梏,早期试图通过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和进行新写作(相对于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写作)书写当代生活的写作训练方式,来发掘普通人的创造力和潜能,以摆脱欧洲文化对青年美利坚的“影响的焦虑”。创意写作教育坚信:每个人都有创造力,都有成为天才的潜质,这种潜质的激发借助写作工坊教育的方式得到激励和释放。被美国总统林肯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1837年在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提出“创意阅读和创意写作”的口号,“希望美国高校能够实现转型,成为真正致力于创意写作与创造性阅读的机构”[8];另一位创意写作教育重要推动者休斯·默恩斯于1925年出版了创意写作的重要著作《年轻的创造力》,论述校园写作(主要是通过创意写作教学)如何树立学生的创造精神,让青年的美国与年轻的创造力交相呼应,成为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分水岭:从自我表达向创造力培养转移[9]。
培养和发展年轻人创造力的方式有很多,为何恰恰是创意写作教育呢?这可能有偶然性因素,但更多则是和文学及文学创作的性质相关。在早期的创意写作者看来,文学研究和文学是不同的,前者以文学作为对象,文学研究是知识性活动,它以文本接受为首要原则,因此强调“积累、彻底性、准确性以及文本和语言、文本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但它“始终无法接受文学作品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文学不是研究对象,而是惊讶与欣喜的所在,不能仅仅加以了解,而要不断创造与再创造”[10]。因为文学是想象力的发展,是不断地创造与再创造,加之它具有公共性和入门低等优势,通过发展文学写作就自然成为培养年轻学生的基本途径。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主义理念的推广,与教育的民主化、多元化和大众化一道,加之美国新闻与报刊印刷业和影视业浪潮相继到来,大量的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提供者。苏炜曾指出:“美国80%以上的作家是通过大学的写作训练培养出来的。”[11]他们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意写作教育作为一种新人文学科,具有鲜明的人文性。[12]它既是对文学和文学创造的解放,也是对人创造力的解放。其核心口号是“写作可以教,人人可以成为作家”,其目的是通过以文学写作为中心的写作活动,把文学和自由联系起来。从文学阅读之门进入,通过工坊制写作活动,引导大众在写作中获得自我解放,走向个体的自由。从这个意义讲,承认和发掘普通人的创造力,通过写作方式让他们获得自由,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只有厘清了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发生学和其新人文学科使命,我们才不会望文生义地嘲笑、诘难或者困惑地追问“什么样的创作是创意的,什么样的创作不是创意的呢”,或者“不按照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品就没有创意吗”。
二、新文科战略要求高校培养写作人才来回应时代之需
结合新文科战略和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历史,发展创意写作是新文科对文学学科转型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高校发展创意写作是新时代之需。
(一)创意写作具有天然的新文科属性。“新文科”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启动和实施,对中国大学文科、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为创意写作在中国高校的发展提供合法性。“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这一纲领宣言把新文科定性为创造性文科,“创造性”或“创意性”(creativity)是新文科的灵魂和根本意涵。何为创造呢?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考证,creative在现代英文里有三重意涵,分别为original(原创的)、innovative(革新的)以及productive(生产的)。[13]这三个意涵对于新文科建设有根本性的意向指引,有助于我们把握新文科的基本精神和内涵旨意,也把创意写作和新文科属性紧密联系起来。
新文科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变。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发愤图强,逐步改变落伍状态,正从世界的幕后走向前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变化的世界需要教育跟着变化,包括文科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要积极为社会服务,培养当今和未来社会需要的新人才。同时,这也是文科教育发展的历史性新机遇,是中国文科教育走出西方理论霸权和“影响焦虑”的重要节点。
社会需求是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对于高质量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必将推动新文化和新文科的发展。现实社会需求下催生的文科内涵和形式才是原创的(original),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远大前程,也只有这样的新文科教育培养的人才才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包括创意写作在内的人文科学要走出高校封闭的体制内的自我循环,直面社会重大需求,做好社会服务。很显然,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特点要求高校为其培养专业化人才。具体到文学和艺术学科,则要求高校文学艺术专业重点培养艺术创作型人才,而不仅仅(或不宜主要)是艺术批评家。过去高校文学学科以培养文学研究、批判者及教育者为主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不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创意写作当以培养服务于文化市场的各种各样的作家为己任。
新文科要求文学等专业脱虚向实,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使命。著名的创造力研究家斯腾博格说“创造力是一种能提出或产出具有新颖性(即独创性与新异性等)和切实性(有用的,适合特定需要的)成果的能力”。[14]我们过去考量创造力,对新颖性很重视,但对切实性强调不够。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有意在纠正这个偏向,把满足社会和个体需要的切实性作为衡量新文科的重要衡量指标。
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小逻辑”就要服务和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以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和特色导向来进行专业改革,大力打造和扶持特色优势专业,积极升级改造传统专业,坚决淘汰不适合社会需求发展的专业。这个举措对传统的文史哲专业和学科提出了挑战。
对传统文科的改造升级是一个大课题,也是难题,需要花很大力气摸索和推行这个改革。但基本的方向可以大致确定:一是从传统文科门类里面“生长”出对社会需求有用的专业和学科方向来,比如新闻、出版、秘书等就是从文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学科;二是从素质和能力并重的教育改革中培育出新的学科,比如起源于美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就重视学生的创造素养和能力的教育,因其在促进教育民主化和人的自我解放上起到很大作用,进而无意中帮助美国文化产业的发达发挥重要作用而成为新的学科;三是推进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让传统文化成为活的新文化,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活力,产生巨大的精神动能,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文化经济时代,人们对高品质文化要求越来越强烈,这客观上要求大批高校文学专业的学生与艺术生一样要直面文化市场,成为艺术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解释者和批评者。
新文科要求高等教育落实到人身上,培养有创造力的中国青年。“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中国今日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新时代文科人才建设的根本问题。新文科要培养的不是传统文化的忠实拥趸,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粉丝,而是培养具有自信心、自豪感和创造性的中国青年。新文科培养的人才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唯有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保证才是胜出的法宝。国家在下一盘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的大棋,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新文科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呢?我们以为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力开展通识和专业并举的创造力教育。也就是把创造力教育作为大学生的必修通识课,在新文科的各个专业融进创造力教育,形成“创造力+专业”的课程教学与实践体系来育人化人。创意写作教育无疑契合创造力提升和创造性写作人才培养,具体到中文系就是培养作家,前述讨论创意写作的内涵时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美国高校开展创意写作的根本目的和效果也能很好地说明其可能性和效果。从这一点上讲,创意写作的根本意义溢出了其学科可能的范围和功能,也溢出了文学教育的属性,走向了人类的基本创造性和自由。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创意写作是天然的新文科,符合国家的根本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前景辽阔。
三、高校培养作家的路径和方式
传统意义上把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观点需要修正,否则的话我们无法走出天赋作家的精英主义观念。刁克利在推介多萝西亚的《成为作家》时指出:“在英语中作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创作的人,即‘写作’(write)这个动词加一个后缀,变成做这个动作的人(writer),所以,作家就是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人,与写作有关。在这几本书里,你会读到比如学生作家之类的词,即将来有可能成为作家,而现在的身份是在校学生的人。当然,也指任何从事写作的人,不管他的职业背景和身份是什么。换句话说,只要在写作,就可以称之为作家。所以,作家人人可为。另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作家,是一种身份和职业,即主要靠写作为生的人,或者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可以稳定以写作为业的人。”[15]我们习惯于从第二种意义上理解“作家”,而忘记了从第一种含义上去理解作家(第一个含义包含第二个含义),有的苛刻者甚至把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人降格称之为“写手”或“码字的”。在文化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解放“作家”观念,把对“作家”的理解和认定权回归到大众手中,坚持“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人”都是“作家”,让“写作”成为每个个体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习惯性行为,回到“作家人人可为”的常识。
那高校该如何培养作家呢?高校培养作家的方式与传统作家生成有何不同呢?传统作家基本是自学成才或者采用“师徒制”的私相授受。这需要学习者个人具备一定的悟性和意志力,有的人可能“运气不好”终生无所成就。但现代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是集体性、专门化和专业性的,它们强调的是包括创意写作在内的学科是有专门知识、技巧和规律构成,通过集体教授和习得可以获得。相比而言,这种方式有利于大批量人才快速有效地培养,这正是现代人才培养的特点与规律。作家阎连科曾发出“电梯说”的感慨:“前两天看了这套书(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意写作书系”——引者注),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栋七层高的楼房,像我这代人是从楼梯一层层走上来的,但其实它是有电梯的。等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五六十岁了。在中国确实一直在说作家是不可培养的,是没有方法的,看了这套书你就知道确实是有电梯存在的。”[16]
结合当前我国高校开展创意写作的各种路径和经验,我们以为高校开展对于作家的培养存在如下三种形式或状态。
第一,高校是新世纪作家存在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我国,作家存在的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处于中国作协系统的专业作家,这些作家属于所在地区的事业编制,旱涝保收,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作协系统控编严格,名额极其有限,多地逐步推广签约作家制以限制专业作家制数量;二是兼职作家,这类人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他们的主业或是记者,或是教师、作者、编辑等,写作是业余爱好;三是自由作家,以写作谋生,但不依附在作协体制内。这些年随着网络等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写作兴起,依靠文艺市场生存的作家慢慢增多,但除了一些头部作家外,腰部及以下的作家绝大部分生存一般。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17],像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余华、苏童、方方、东西、田耳、郑小驴等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转会”高校,成为“驻校作家”。随着高校扩招,大学功利化选择,以及创意写作教育的兴起等综合因素,高校向作家抛出橄榄枝。对作家来说,或“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或“进入高校,希望重新找回写作的状态”,或“在大学里聚众收徒,传播文学,似乎都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埋藏已久的梦想”[18]。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作家进校园,以文学和写作的名义与青年学子在一起,有利于作家的“业务”水平能力提升,这事实上也是一种形式的“作家培养”,这种作家模式与历史上的“校园作家群”现象形成了本雅明所谓的“星座化”。
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急剧扩张,招募了很多作家进高校教写作,这一方面对美国的创意写作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同时对作家自身也是很好的进步机会,至少因为生活的保障能让他们安心创作。美国校园作家的成熟和校园文学的几度繁荣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校园是作家成长和发展的理想环境。随着创意写作在全国中文系的普及,更多地方作家进入高校(专职、兼职),高校在作家系统的地位越来越高,以作家为纽带,慢慢使作协、作家和高校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会更多地为地方文旅产业、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这是大学教学改革,实现新文科专业的重要途径和趋势,也是作家实现和发挥个体价值的有效方式,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特色作家培养模式。过去,这种方式主要是依靠作家协会来实现,如今高校的优势可能更加明显。
第二,高校成为培养新一代作家的摇篮。创意写作教育的普及,促使中文学科内部出现分化,从传统的语言与文学的二分,转变为语言、文学和创作的三足鼎立。创作就是要培养现在或未来的作家,越来越多怀着“成为作家”梦想而进入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光明正大地写作,在校园作家指导下,在校园丰富的文学氛围与便利的文化资源补给下能迅速成为作家。这里面可能有几种情况需要区别认识,对于本身写作天赋很好的人,创意写作教育能早日发现,并帮助他们尽早尽快成才,即所谓写作天才和促成其早日成才。复旦大学陈思和在创办首个创意写作MFA硕士时坦言:“MFA(创意写作硕士)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19]
二是大多数写作天赋一般的写作者,在大学通过正确方法的引导和自我刻苦训练而成为优秀作家。这种培训是系统的、多层面的,从创意阅读开始,经过模仿写作和工坊制训练等,到作品朗诵和投稿比赛等环节历练,新一代作家就这样“打造”起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这些年创办创意写作,培养了不少学生,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诗刊》等大刊都发表过不少作品,还有不少学生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
三是以中国人大学的创造性写作教育为代表,该模式对国内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进行学位教育,对他们做进一步的文学提升。这个“作家”培养方式有点类似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与提升方式,但因它发生在高校,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和校园文化生活作为底蕴,因而有其独特性,影响力很大。
这三种模式的高校作家培养模式主要发生在985高校,看重第一种含义上的“作家”概念,以培养传统型作家为主。作家叶炜认为,它们主要是培养文学的“农耕者”。[20]应该看到,随着创意写作教育体系在我国的成熟,写作氛围会越来越浓郁,发表条件宽松和形式的多样化,一定会吸引更多有着文学梦的孩子加入创意写作教育中来。大学重新成为作家的摇篮,大小不一的大学写作现象和写作群的出现指日可待。
第三,高校承担为文化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人才。高校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有很多,《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开设“创意写作在中国”版块来介绍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大约30所高校的做法与实践。我们也曾经把高校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作家2.0提升模式;第二种是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专业作家(传统精英作家)培养模式;第三种是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21]叶炜也认为:“当下的中国创意写作实践已经出现了两个实践路径:一个是主要培养包括作家在内的创作人才,主要面向依然是文学;一个是培养创意人才,主要面向文化创意产业。而这两种探索路径对应的恰好是对于欧美creative writing一词的两种内涵不同的译介:创造性写作和创意写作。”[22]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创意写作对于创作人才的培养的一面,看作农耕时代紧盯着一小块文学之田的深耕细作,那么,对于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面,则可以看作是创意时代面向无限广阔的文化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如果说前一种面向,培养的是在固定园地上耕耘的‘农耕者’,那么后一种面向,培养的则是在广袤原野骑马闯荡的‘游牧者’。这一点,似乎也是越来越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共同看法。”[23]金永兵教授也坚持:“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范围更为宽泛,它指向的是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我将此定位为培养“写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作家’”。[24]
对于更多的高校中文系来说,创意写作培养的就是直面无限广袤的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即广义的作家培养。高校的人才培养要直接服务国家战略和国家重大现实发展需要。随着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意人才的聚集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衡量国力的核心指标,在目前世界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在GDP中均占据支柱产业地位,比如美国的创意产业占GDP总量的25%以上。这当然得益于美国创意写作教育对创意人才的培养。我国近年来确立了创意国家战略,特别是2016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不仅把文化类创作创意当作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把科技创新创意当作社会经济核定动力,这标志着中国的创意国家战略基本成型。考察美国高校创意写作教育的普及和对美国创意产业直接或间接推动力的历史和经验,我们更需要重视通过创意写作教育和创意写作+专业的教育方式来培养文化创意产业需要的创意人才,直白地说,就是文化产业上游需要的策划人、编剧人及原文稿、文本的写作人员和传播者等。恰如金永兵所言:“创意写作,不仅关乎如何写出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更涉及训练如何用各种符号语言来表达创意、制造创意,进而使创意成为已有文化产品的新的生长点。因此,创意写作的学科体系,培养的不是拘泥于某一类既有写作方法和风格的文字操作者、使用者,而是具有复合型知识体系、对文化语境的总体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创新者、创造者。”[25]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意写作要培养的人才有着无比宽广的前景和美好未来。如果高校能及时跟上社会现实需求的变化,大力推行创意写作这样的文学生产性人才的培养,那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前景也一定值得期待。
发展创意写作及教育,是世界性大趋势,也是中国文学教育的必然走向。但创意写作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从创意写作发展的欧美教训来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以实践性著称,不重视理论建设。中国创意写作教育一开始就要有建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自觉,这既是对欧美创意写作早期问题的规避,也是中国高校教育学科化特点的适应。创意写作理论建设中的一大难点是如何自觉确立和既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理论体系的区别,建立以作家为主体,以文化创意生活为旨归的生产性文学体系,即刘卫东所言的“以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为契机,凸显作家参与的文学知识生产,建构作家主体性,将文学创意导向创意城市的文学实践,是通向不同于话语生产的新的文学知识生产的潜在路径,走向更为开放、更有活力的文学知识生产”[26]。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中国当下,不能学科化的创意写作及其理论体系,迟早会重蹈现代写作学的覆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创意写作能获得专博的学科地位。其次,创意写作和作家培养的方式与路径,立足高校又要溢出高校,要以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形式让写作训练与作家培养“社会化”。社区化与工坊制的结合,是创意写作最有活力的地方所在。高校培养作家,并不是要把作家的写作活动空间框定在课堂或者校园,社区才是开放的创意空间。这与传统写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到群众中是一致的。最后,我们不仅仅要解放作家“观念”,也要解放作品“发表”观。在社会交往和社交媒体前所未有便利与繁荣的时代,校园作家要学会“推销”自己的作品,在各种社区空间“呈现”和“表演”自己的作品,让作家自己的作品成为公共艺术品或公共性艺术活动的内容。知易行难,完成以上三个难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创意写作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展开和理论提升中成长,在各种诘难中成熟。我们乐观地预测,中国未来作家会越来越多不是由社会培养,而是由高校培养,是由高校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来培养。
注释:
[1]汪曾祺:《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教学》,选自《汪曾祺论沈从文》,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43页。
[2]网易号:《念中文系就能当作家?北大杨晦教授:“本专业不培养任何作家”》,见https://www.163.com/dy/article/HA2ANH8G0543LPQ1.html.
[3]人民网:《作家在校园怎样教写作》,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939611422677732&wfr=spider&for=pc.
[4]曹顺庆:《中文系培不培养作家?能,而且应该!》,见https://www.163.com/dy/article/G2O6VJUV0514D3UH_pdya11y.html.
[5][11]中国作家网:《旅美作家、学者苏炜:中文写作该如何操练?》,见http://image.chinawriter.com.cn/n1/2017/0628/c405057-2936 7257.html.
[6]张永禄:《创意写作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建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0》,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页。
[7]高尔雅:《创意适当的创意写作教育: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上海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论文。
[8][10]D.G.迈尔斯著,高尔雅译,葛红兵审校:《美国创意写作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 51页、第49页。
[9]Duff J C. Hughes Mearns: Pioneer in Creative Education. The Clearing House: 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ssues and Ideas, 1966, 40(7).
[12]关于创意写作的人文性特征,具体参见张永禄:《论创意写作教育的人文性》,《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3]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文化研究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2页。
[14]斯滕伯格著,施建农等译:《创造力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5]多萝西亚·布兰德著,刁克利译:《成为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6]阎连科:《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44122544.
[17][18]叶祝弟:《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9]刘巽达:《作家能否“大学造”》,《光明日报》2014年11月5日,第2版。
[20][22][23]叶炜:《创意写作的分化:选择“游牧”还是“农耕”?》,《文学报》2023年7月27日,第8版。
[21]张永禄:《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爱荷华》,《田家炳中华文化中心通讯》2022年第1期(总第7期)。
[24][25]金永兵:《新文科与创意写作人才培养》,《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1—2)期,第26页。
[26]刘卫东:《文学知识生产的潜在路径与可能形式:基于创意写作研究的视域》,《中国文化论丛》2022年(第2辑),第326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翻译、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23&ZDZ2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张永禄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