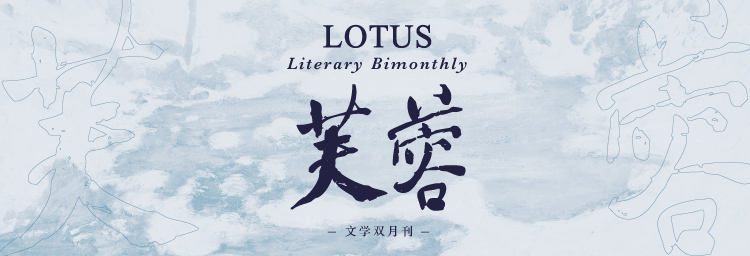

历史、社会与个人的叠合
——《遥远的古冬玲》读札
文/李德南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人、社会与历史,时常会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种联系,往往又在当下的语境中得到映照,当下性或当代性是种种联系得以持续的基本条件。也正因如此,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性质”。而历史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当代问题与历史问题彼此关联,历史问题往往是当代问题的成因,当代问题又构成认识历史问题的视域。这也是当代人之所以不断回望历史的动力。
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遥远的古冬玲》,就用了非常多的篇幅来展现历史、社会与个人的叠合。《遥远的古冬玲》主要从当下的场景展开,逐渐向着过去回溯,从而让过去与现在互为参照,互相照亮。这篇小说有一个堪称巧妙的开头:“时间一眨眼,古万全夫妇在南京,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已生活好多年。”“时间一眨眼”既暗示了历史视野的存在,也暗含作者个人对历史、对时间的态度。接下来,叶兆言则以说书般平易近人的叙述,将我们带进古万全夫妇现在生活的小区,带进他们平淡又不乏温情、没有大悲大喜又不乏种种小烦恼的日常生活,带进他们曾经生活的乡村世界——江南一个叫古家埭的村子,也带进四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光中。
随着叙述的推进,古冬玲,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也缓缓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是一个曾经从南京城到古家埭插队的知青。她的父母曾经是古家埭这个地方的人,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而作为插队的知青,古冬玲的到来或回归,给古家埭带来了很多很多。比如城市的种种事物。麦乳精、火车、汽车、粮票、凉鞋、钟山牌手表……这些事物以实物或想象的方式出现在古家埭人的现实世界或心灵世界当中。这些事物的出现,唤醒了古家埭人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和迷恋,也展现了乡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就好比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是的,古冬玲很重要。她连接着古家埭和南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古万全夫妇等人的情感和梦想。古万全曾经暗恋古冬玲,他的妻子马春妹则和古冬玲同住了一年多。对马春妹而言,古冬玲所过的生活才是她渴望的生活,古冬玲所在的世界才是她所渴望的世界。马春妹的生活和世界在别处,起码她是这样认为的。“古冬玲来到古家埭,不只影响了古万全夫妇,也震撼了村上所有的年轻人。毕竟她带来了不一样的青春气息,把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女孩形象,带到了偏僻的古家埭。”古冬玲还是牵引小说情节变化的关键人物。她太重要了,叶兆言深知这一点。当叶兆言将小说命名为《遥远的古冬玲》时,他对这篇小说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
《遥远的古冬玲》由始至终都关注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城乡之间的生活差异,是这篇小说所重点描写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又成为个人历史性的一部分,难以有根本的改变。就像小说中所写到的,虽然“时间一眨眼”,四十年就过去了,但是古冬玲的样子还是那个样子,腔调还是那个腔调。古万全夫妇也同样如此。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已有多年,骨子里却还是乡下人。
社会、历史和人总是互相影响,形成叠合的关系。人在社会当中,在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形成生成个体的具体历史。如赵汀阳所指出的,“人不是一个先验概念,只能在其演化生长方式中被说明,就是说,人的概念由人的演变来说明,人的意义存在于人创造的生活里,因此,只有历史性才能够解释人的意义,历史是对存在的赋值,时间本身无意义,而历史赋予时间以意义”。叶兆言也着意要写出社会和人的具体历史。《遥远的古冬玲》是一篇有历史感的小说。这种历史感有时带着诗性的色彩,即小说中所写的“遥远”的感觉——“遥远两个字很有意思,白驹过隙,物换星移,远远的,看不太清楚,它已经模糊了。然而看不太清楚和模糊,并不意味着就会消失。隔着时间长河,通过对空间的穿越,遥远的身影又会悄然出现。不知不觉中,遥远正对你凝视,遥远正与你相望。也许每个人心目中,都会保留一些不一样的遥远。”不妨说,遥远感就是幽微的历史感——它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是一种诗性的、朦胧的存在。
《遥远的古冬玲》展现了历史与当下、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物质层面的联系,也有政治、经济层面的联系。此外,还有文化层面的联系,传统中国的宗族观念在当代如何延续和变化,在这篇小说中有所反应。《遥远的古冬玲》写到古万全对古冬玲的暗恋,这里头既有古万全对古冬玲的独特感情,又蕴含着身处乡土世界的古万全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古万全之所以一直把这种爱慕之情埋藏在心底,原因也不止一个。比如城市和乡村的差异。他深知古冬玲作为下乡知青,虽然有了农村户口,但她最终是要离开的。她并不属于这里。此外,他们都姓古,是未出五服的古家后人,是叔叔与侄女的关系。同姓不结婚的文化传统禁忌,也是一个障碍。
《遥远的古冬玲》写出了当代中国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城市和乡村各自的变化。这种种变化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往往会被进行简化处理。在这篇小说中,叶兆言则更希望发挥文学作品的优势,写出其中微妙的复杂性。比如在今天,城市和乡村物质层面的、外在的差距,已经日益缩小。可是就心理结构而言,各自的出身也使得人们不会因为空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比如古万全和马春妹虽然住进了城市,但是心理、口音和形象,仍旧基本保持不变。叶兆言还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个人变化,是因人而异的。时代的变化也会使得人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古冬玲的亲家夫妻如今就常年住在乡下。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没经历过农村的苦日子,到了现在,就很能享受田园生活。因此,与住在城市相比,他们更喜欢住在乡下,所以选择了到乡下租用农民的房子,养鸡种菜。
在处理城市化进程这个问题上,叶兆言也注意到其中的复杂性。他并没有对乡土与城市做二元对立式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地认为城市生活就是好的,乡土生活就是坏的。他留意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世界确实过于贫穷。小说中写到的全村人排队在同一口铁锅里洗澡,就是一例。这种落后和贫瘠,确实不堪回首。而小说中写到城市生活时,叶兆言也有意安排了一个相对曲折的情节,那就是古冬玲一家的实际生活,并不是马春花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古冬玲一家实际上生活在逼仄的空间中,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享受着城市文明的益处。今天的城市世界也仍旧有其问题,而乡土世界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则克服了不少过往曾难以忍受的问题。这也是古冬玲的亲家夫妻选择住在乡下的原因之一。
在《遥远的古冬玲》中,叶兆言既对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进行了微观的描绘,也融入了宏观的思考。在书写城市和乡村的变化时,叶兆言把这种种变化放置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展开。历史的纵深视野,让小说的书写获得了厚度和深度。
《遥远的古冬玲》的美学风格也颇为值得注意。它有从容的叙事气度,有明晰的美学气质。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与现实是复杂的,叶兆言写来,却举重若轻。这得益于他对所写的题材有深透的理解。在涉及过去时,他会留心一段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层面的特点,会把人真正放置到那段历史当中。而写到当下的种种时,他的视野、笔墨和心态,也并没有显示出隔膜的迹象。他同样知晓、熟悉当下的生活,深知当前时代人们的情感诉求和价值观念是什么样的。甚至他的表述,也很有当前时代的气息。他在写作中也没有选择用很复杂的句式,而是以口语化的短句为主。他的小说语言,简约,却又无比生动;精熟,却不陈腐。这是一种让人特别有亲近感的表述方式。

李德南,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入选“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为思想寻找词语》《共鸣与回响》等。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粤派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李德南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