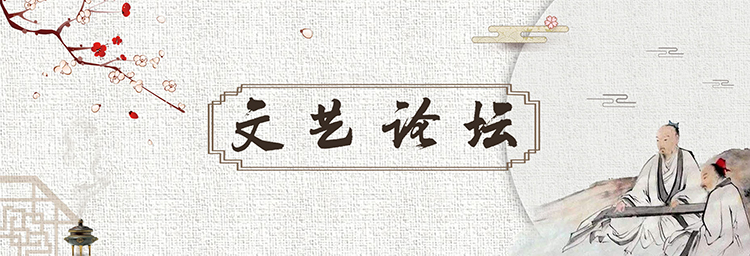

《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演出现场。
《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新杂技剧的探索及发展可能
文/董迎春 李丹
摘 要:2021年底,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创演的新杂技剧《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至今已在全国各地巡演近百场。作为一部以当代青年迷茫、矛盾与挣扎中追逐梦想为时代主题的杂技剧,《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吸纳了新马戏、后戏剧剧场的一些创作理念,在杂技剧场融合了中国特色的舞蹈、音乐、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和手段的跨界,形成了集观赏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臻境”追求,助推了当代杂技艺术发展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新杂技剧;哲理观照;形式创新;发展可能
一、现实题材的尝试与哲理观照
2004年国内诞生了首部杂技剧《天鹅湖》,杂技剧成为杂技剧场的主要形式,但此“剧”还是主要追求传统戏剧的戏剧性本体,杂技“本体语言系统完全有可能演绎叙事作品”[1],但当下新马戏、后戏剧剧场对“戏剧”探索更显丰富,这就催生了《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以下简称《青春》)杂技剧场的创造、创新的探索。
西方新马戏在中国本土的实践催生了“杂技剧”“新杂技”“新杂艺”“泛杂技”“新杂剧”“杂技剧场”等不同称呼和命名,彰显了国外新马戏与中国杂技剧发展中的对话与可能,杂技剧场中的戏剧元素、艺术跨界等创作理念的融入促成了新杂技剧场之“新”和在中国剧场舞台上的创新和发展。从题材上看,新杂技剧场《青春》将创作视野投射到当下广大青年群体的存在现状和思考上,聚焦青春的彷徨、苦痛与向上的姿态,以个体的生命体验、精神风貌呈现出社会的整体风貌和审美理想。它以“青春”作为主旨串联起整个剧场,在柔美与健朗的身体表达中塑造青年群体形象,于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中呈现青春时期的情绪状态与精神追求,以后戏剧淡化叙事和情节为理念,更集中以青年群体和青春个体的象征意味增加杂技剧场的情感表现,极大限度地勾连起不同年龄阶段个体的青春生命体验与杂技之美的召唤。
《青春》所演绎的青春故事规避了说教式、模板化,而以杂技节目和青春叙述的结合为本位,杂技的惊险高难象征了青春成长的辛酸苦辣。杂技剧场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审美形式上,“在它的直觉下面,同样有着深厚的社会内容”[2]。纵观全剧,杂技演员置身蓝黑色调的舞台中,无论是匍匐、倒地还是奔跑、跳跃、攀爬、目视前方,伴随着或缓慢或轻快的音乐,暗指着青春之路坎坷难免,每一个高难节目完成后的观众反应正是青春成长的疼痛和光明。“艺术激发想象,使进行审美欣赏的人彼此间共情成为可能”[3],其身体行为含蓄地契合内容表达,在舞台上呈现出对于青春、人生的哲理性思索,现场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体验到的是沉浸式的精神放松和哲理观照。
“青春”作为剧场的主题避免了同质化创作趋向,拓宽了杂技剧的表现空间和审美维度;身体造型与情绪传达的有节奏配合,使杂技的哲理表达与反思成为可能。杂技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传统艺术,新杂技剧场的舞台创作拓展了当代杂技的发展空间与可能,诸多杂技节目在舞台上得以传承和发展,而传统杂技又融入现代剧场的展演体系和创新发展中,新杂技剧场是中国杂技剧向前又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
二、杂技剧场的跨界与形式创新
当代杂技与戏剧、音乐、舞蹈以及新媒体技术等多种形式跨界融合。作为一部主题和形式新颖时尚的新杂技剧场,《青春》尤其突出的是吸取西方新马戏、后戏剧剧场中的现代舞的展示方式,对身体技巧进行颠覆式的解构与重组,借助声、光、电等技术营造亦真亦幻的舞台情境,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剧场效果。
1.《青春》的综合舞台。20世纪70、80年代起源于欧洲地区的新马戏启示了杂技剧的本土发展和现代转型。而新杂技剧场的内容和形式创新,则推动了中国杂技剧的进一步发展,它“离开了传统马戏的题材和气氛里深深蕴含的娱人的需求,它不提供仅仅搞笑的娱乐,也提出智性的刺激和艺术的分析”[4]。相较于戏剧冲突强烈、故事性强的杂技剧,《青春》整体步调舒缓,着重于情绪渲染和意境营造,是对新马戏戏剧性主题的一次创造性尝试和创新性发展。在舞台布景上,传统杂技节目大多追求繁复华丽,新马戏则追求简练,以表演者的感悟式表达取代单纯的炫技,同时以较少的杂技演员、干净的黑蓝灰色调、精简的道具让舞台瘦身,以简练的舞台形式诠释丰富的情感内涵。“新马戏的精神不是专注技巧,而是开发创意;不是拘泥形式,而是触动心灵”[5],该剧对“青春”主题的独创性阐发,在与音乐、舞美、灯光等现代艺术的融合创新中颠覆了以往的演出形式,是对新马戏注重主题戏剧性、追求舞台创意和前卫形式的综合性创造。
2.现代舞蹈推助《青春》现代表意。对于杂技剧场而言,极具形式感、创意性的现代舞蹈发挥着串联杂技节目、美化杂技动作、增强情感表达与艺术感染等功用,助推杂技舞台上的意境营造和主题表达。现代舞,承自20世纪初西方舞蹈艺术家伊莎多拉·邓肯,追求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张扬强烈的个性意识,运用肢体语言表达人物内在情感,以极富现代意味的舞蹈形式拓宽观众的想象空间。《青春》中杂技与现代舞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丰富了舞台内容和形式,柔与刚、力与美结合,以抒情化的身体技巧表现情感和心理状态。第一幕《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将杂技的柔术、绸带技巧与现代舞融合,展示了身体的灵活性、柔韧性和力量感,是生命挣扎与成长的具象化表达,使表演更具内涵和情感。现代舞蹈融入杂技剧场,使得杂技表达更自由、表意更集中。《青春》正是合理把握了现代舞与杂技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跨界交流、高度融合,拓展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推动了现代杂技剧场的发展。
3.声、光、电为《青春》技术赋能。“声音是剧场艺术的重要维度。”[6]杂技剧中最直观的声音即背景音乐,它营造了更为真实的舞台情境,促成舞台氛围的渲染,调动观众的体验感和沉浸感。《青春》的音乐总体上柔和舒缓,第四幕《我们都是主角》以原创歌曲《就算》轻快曲调作结,颇有拨云见日之状,整体氛围与该剧主旨表达相对应。杂技动作和音乐有节奏地配合,每一个动作的展开、停顿,速度的快与慢,力量的轻与重,都与音乐相配合,在完成动作的同时也表达了情绪。第三幕《夜空中最亮的星》开头,漆黑的舞台上只见转碟、空竹舞动,舒缓且有节点的音乐恰如夜空中繁星闪烁,增添了剧场的艺术感,使观众如临其境并增强其审美体验和智性探索。从光影效果上看,《青春》以黑、蓝、灰作为舞台主色调,形成了年轻化、时尚化、哲思化的剧场基调,同时通过亮度调节、方向变换等多种手段与表演内容相呼应,突出情感的转变或情绪的起伏,延伸了观众对舞台的想象空间。此外,《青春》特色还在于合宜地将当代青年的青春记忆与成长履痕予以纪实性、生活化的视频影像展示,拉近了观众与主题的情感距离,以一个个特写慢镜头与舞台上的独轮车、吊环等形成剧场互文性建构,是对人物形象的一种补充与阐释。显然,青春式的“声、光、电”的创新运用为杂技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段和表现形式,提高了舞台整体感染力、表现力。
《青春》是中国杂技剧又一创新和发展的成果,也是对新马戏、后戏剧表现技巧和创作观念的合宜挪用,借用综合舞台、融入时代主题的跨界审美,将青春梦想和杂技奇观交互生成,彰显了当代杂技创意与艺术呈现的新的审美维度和发展方向。
三、当下杂技剧场的发展价值及可能
《青春》的审美创意与理念创新,成就了中国杂技剧的形式探索与剧场价值。青年成长题材的时代关注,拓展了当代杂技剧目创作的表现领域与审美空间。综合而言,该剧价值主要表现在杂技创作领域的开拓、艺术主题与现实融合、舞台跨界编创等诸方面。
第一,青春题材对杂技创作领域的拓展。任何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在守住本体特征的同时求新求变是艺术保持活力的关键。新时代杂技的发展仍以杂技技巧为本体,且在题材、形式等方面显示出了更高的探索和驾驭能力。《青春》题材极具现实性、时代性,该剧对青年的关注正是对一个体青春成长记忆的关注,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能从“青春”这一主旨中唤起个人独特的青春体验。同时,它还采用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融合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剧场舞台更具现代感和现代性,进而呈现出更具吸引力的主题叙述方式和更丰富的情感想象,显示出了对现实题材的驾驭能力和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引入跨界艺术进行高度融合为杂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路径。
第二,现代剧场的审美探索与哲理观照。现代杂技节目(剧目)创作,从“显技”过渡到“显技于艺”,从“造型艺术”发展到“审美创意”,通过内在意涵和审美形式建构民族记忆和时代精神。“青春”主题的确定性与“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现代剧场的开放性结构。该剧多次展示的“门”作为重要意象在剧中频繁出现,“开门”的动作意味着面对未知,来回“钻门”有跨越阻碍之意,“旋转的门”与其中的演员带来眩晕感。而这个极具象征的“携带意义的感知”[7]的“门”,作为一个符号承载着抽象化的精神内核,将创作者的情思和哲理传达给观众,呈现一个可供无限体验和想象的丰富世界。剧中借由以“方”和“圆”的形状出现的新道具展示技巧,如第二幕《奔跑吧,以梦为马》中独轮车飞跃七人与跳背上头、方形吊环高空技巧,构成了动态的审美空间,以创意化的形式编创提升了当代中国杂技剧的舞台审美与智性探索。每一个个体“青春”与民族和时代的记忆紧密关联。“另一个名字”既留下悬念又形成敞开的召唤结构,召唤观众深度参与进而与剧场进行“对话”,超越情感性体验和情绪共鸣而进入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思考。
第三,跨界创意与舞台综合的理念创新与主题表达密切关联。艺术跨界、舞台融合是当前剧场呈现的主流趋势。从青春主题的审美创意到剧场效果的完成,《青春》的跨界舞台是创意化的、灵动性的。这一整体意义的呈现有赖于舞台气氛、杂技动作、高水平道具使用及与主题的关联和综合。如第一幕《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在展示晃板技巧的同时,身穿衬衫的少年缓缓伸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喻示着接纳、包容与释然,以具体细节引导观众进行抽象式的舞台体验,提升现代剧场的沉浸感、感染力;第四幕《我们都是主角》中蹦床、跑跳、攀爬等多种技巧体现青春力量和创意舞台。当代杂技与戏剧、舞蹈、音乐、纪实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现代剧场的发展方向,以创意化的跨界编创和审美化的舞台呈现的现代剧场为剧场营销和国内外艺术商演提供了无限可能。
中国杂技剧场是当代杂技艺术自杂技剧发展后的又一探索。《青春》极具当下的青年视野和现实关怀,在舞台综合、跨界审美等纵横维度及价值上的探索、尝试,既是“两创”理论的艺术化呈现,也是当代杂技艺术向前发展的又一路径及可能,它源于中西方文艺的对话和“互鉴”,“马戏/杂技强国的优点整合,共同创造新的剧场形式和优秀作品,推动艺术的发展”[8],显然,以中国杂技剧场为代表的中国剧场艺术走出国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彰显中国审美底蕴和“中国精神”的重要“使者”。
注释:
[1]卞振:《军旅杂技〈天鹅湖〉英国捧大奖》,《杂技与魔术》2009年第2期,第14页。
[2]唐莹:《杂技美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年版,第338页。
[3](美)皮埃尔·约特·德·蒙特豪克斯著,王旭晓等译:《艺术公司:审美管理与形而上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4]张辉:《边界突破!:欧洲新杂艺》,亚欧文化创新中心2017年版,第8页。
[5]蔡昆霖、戴君安、梁蓉:《法国,这玩艺!——音乐、舞蹈&戏剧》,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1页。
[6]郑钲:《“声音即演员”:声音戏剧构作与当代剧场艺术的听觉转向》,《戏剧艺术》2023年第3期,第123页。
[7]赵毅衡:《艺术符号学:艺术形式的意义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8]张辉:《边界突破!:欧洲新杂艺》,亚欧文化创新中心2017年版,扉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董迎春 李丹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