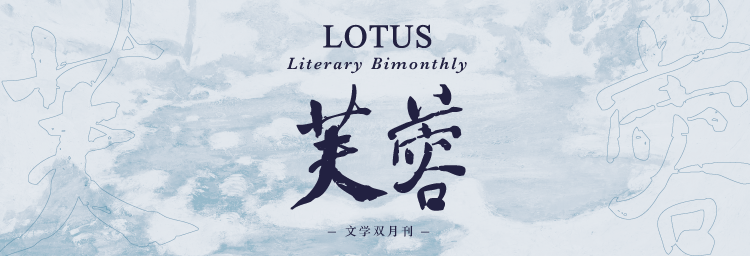

蒙古细
文/格致
我下班就往家赶,不是去接孩子放学,孩子长大了,上了寄宿中学。我本可以下班沿途逛逛小店,看看时装,不买看看也好。有些衣服就不是用来穿的,而是看的。我怕走到瓷器店门口,里面的瓶瓶罐罐个个有本事伸出看不见的小爪子,一圈一圈勾住我魂儿,然后把我拽进去。那些衣服、裙子只会冲着我媚笑,袖子里空空荡荡没有手。但那个哥窑的袖珍玉壶春瓶,在我看到它的一瞬间已经坐在了我的茶桌上,上面被我插了几株野草,好像已经在那里坐很久了。我只得买下它,因为它的魂拽着我的魂已经先到了家,留下我的肉身在店里为这个花瓶的泥胎付钱。不然先到家里的魂找不到安身之所,悬在空中多么可怜啊。晚上它还会出来吓唬我:小花瓶的魂,在夜晚闪着梅子青的荧光,呈一滴水的形状,悬在我家的空中,小嘴一张一合,说让我坐在哪里啊?让我坐在哪里!
现在,我的手里不用牵着一个孩子,也没有一个花瓶水滴状的魂控制着我,但我也得急匆匆赶路,花店、瓷器店、服装店……什么妖魔鬼怪也拦不住我了。
门口的鞋柜,是木匠师傅用细木工板打制的。三层,斜推拉门。三个门关上之后咬得都不够紧,关房门手重了点,某个鞋柜上的门就会哗啦张开大嘴,爆出憋了很久的大笑,然后你就看见了里面牙齿一样的鞋子。
秋天的时候,把夏天的凉鞋包好,放到储藏室里,再把秋天、冬天的鞋放到鞋柜里,以备随时穿用。东北的秋天短啊,哪天一觉醒来,看见窗外白雪铺地,我并不惊讶,只不过是冬天到了。
我有三双棉靴,两双单靴。棕色、黑色、灰色。大都是夏天的时候趁欧亚商场打折时买的。只有一双灰色单靴是在以商品昂贵著称的商场买的,花了大价钱。灰色,高过脚踝十多厘米的短靴,里面是西瓜红色的软皮,鞋跟由灰绿相间的蛇皮状皮革包裹。这是五双皮靴里我最喜欢的,爱不释脚。10月初,柞树叶黄了,枫树叶红了,柳树的叶子还绿着。穿一双稍厚一点的棉袜,穿它正好不冷不热。这双鞋,使我面对整个秋天的阴晴风雨都能气定神闲。
门是轻轻打开的,我害怕听见鞋柜的大笑,我感到它在嘲笑我贫穷。鞋柜在我的控制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面前的鞋柜,三个门都敞开着,像大笑之后,颌骨脱臼无法合上的嘴。原来这个鞋柜在我回来之前就已经把我嘲笑完了,且嘲笑了三次。鞋柜里面空空如也。这不仅是脱臼了,连牙齿也莫名其妙地掉光了。这就叫让人笑掉了大牙。不用低头,就看见那些鞋子躺在地板上。东一只西一只,有的勉强站立着,有的横躺着,每一只上都有破损。有皮毛的鞋子,破损得尤其厉害。
白驹站在那些狼藉的鞋子旁,没有像每天那样跑过来和我拥抱,在门口和我亲热一番。它站在那里,用眼睛看着我,看我对于一地的破鞋子如何反应。我的表情一定是让白驹害怕的,它觉得站在那里很危险,于是掉头跑了。它藏在餐桌下。餐桌垂下来的台布刚好遮住了它,又不影响它从流苏间往外忐忑地窥视。
我在门口蹲下,查看那些鞋子。每一个都被细心地咬坏了,基本不能修复。它们是我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两三双一起买回来的,没花多少钱,但棉靴是我为接下来的冬天准备的。现在它们都坏了,而雪花们正在赶来,这里的冬天没有棉靴是过不去的。就像面对大海没有船。我得再选一个休息日出去买棉鞋。天已经冷了,棉鞋不会打折反而会更贵。
我检查鞋柜的开关,想看看它是怎么打开的。这一蹲下,我有个意外的发现:在鞋柜的里面,居然还有一双皮鞋幸存,完好地坐在那里,没有被动过。心想总算给我留下一双,这样我就不用急匆匆去买鞋了。拿出来一看,却原来是前夫的鞋子,上面一层细灰,鞋带系得板板正正。在我眼里,前夫是有洁癖的,狗毛要是粘在了他的裤子上,他就会大惊失色。
白驹只咬我的鞋,而不咬前夫的,这是为什么?前夫在的时候,对白驹不好,乘我不注意偷偷地打它。白驹从不到他身边去,离他远远的。他俩是互相看不上,谁也不搭理谁。那么,按照常规思维,白驹应该恨前夫讨厌前夫,咬鞋应该咬他的。或者,白驹咬鞋没有爱恨,就是咬着玩,不管谁的鞋以破坏取乐。事实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它只咬我的鞋。而我们的关系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那么结论就是,它喜欢谁就咬谁的鞋。或者,它喜欢我,但是仇恨我的鞋!在它眼里,我是好的,但我的鞋不好。而前夫是坏的,但他的鞋,没做什么坏事,是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窗子,一股甘甜的冷气扑到我的脸上,外面已是白雪的世界。雪花在我睡觉的时候悄悄地来到我的窗外。雪花在我的窗外跳了一夜的舞我却不知不觉。而此时,所有的雪花困倦地躺在地上睡着了,它们累了,一动不动。
进卫生间洗脸。觉得今年的雪来得太早,刚10月中旬,一般要10月下旬下雪。以我的经验,这雪是站不住的,中午就会融化。我用毛巾擦干了脸上的水迹。
在门口我和白驹告别,拍着它的头告诉它,妈妈上班去了,在家等着。我转过身,问题来了:我穿什么鞋上班呢?
灰色单靴是不能穿了,外面都是皑皑白雪,但棉靴一双没剩下,都被咬坏了。这时我发现在门外有一双棉鞋,那是一双旧鞋,当时因鞋柜里放不下,又没舍得扔掉,就放在门外了。意思是谁愿偷就偷去吧。旧鞋子没有人肯偷,这时却救了我的急。退下来的灰色单靴我可不敢放在鞋柜里了。我就剩这一双鞋了,而且是花了上千元买的。放在门外显然也不行。我拎着靴子,站在门口环顾我的居室,得放在哪里才安全呢?我看见了餐厅的酒柜,两米多高,快要顶上天花板了。我踩在餐椅上,把我的皮靴放到了上面,然后我又和白驹告了一次别。把手掌扣在它半圆的头上,说,好好看家,下班就回来,给买好吃的。
我放心地走了。我还有一双鞋,并且是最好的。我的心情还可以。
到中午的时候,地上的雪,在耀眼的阳光下矜持不再,它们变成了水。雪花也是花,不能一直开放。雪花只开放了一宿,就凋落成了水。水是存在的最世俗的形式,而雪花是地上的水的一个关于飞舞的梦境。我的脚在棉鞋里出汗了,看来明天还得穿那双灰色单靴。那几双鞋我并没有特别心疼,三双也没过一千元,只是觉得还得再去买,很耽误时间。我暗暗庆幸那双灰皮鞋躲过劫难,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
上楼前买了几根金锣王。白驹等我一天了,说好的买好吃的。
推开门进屋,哐当一声,最上面的那个鞋柜门猛然张开,像谁给我布置好的恐怖情节,然后露出前夫那双巨大的黑色军靴的后跟。它俩怎么还在那里安然无恙?白驹今天没什么咬的,为什么不咬这双呢?就算再讨厌他,在没的选的情况下,白驹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吗?你忘了他打过你吗?你也有洁癖吗?我换上拖鞋刚走一步,就看见我那双灰色单靴躺在地上,不是在门口,而是在餐桌椅子旁,其中一只已经被咬得惨不忍睹。我大骇,如同遇到了灵异事件。鞋是放到酒柜上的,怎么会在地上?
我来到酒柜旁,抬头看,这个高度白驹是怎么够到的?也只迷惑了一小会儿就找到了答案:白驹先是跳上了凳子,然后又跳上了餐桌,然后在餐桌上站立起来,就够到了酒柜的上面。白驹站起来头到我的嘴的位置。也就是,我怎么把鞋放到酒柜上的,那个过程,白驹站在旁边,都看到了。
我跌坐在餐椅上,沮丧至极。竟然没有想到那些桌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的智商已经应对不了一条才几个月大的小狗了吗?
白驹看我的神情不对,躲到阳台窗帘的后面去了。
每天早上我上班离开,它都很惊慌很难过,并试图跟着我一起走,而早上我已经带它在楼下草地或者江边玩了好一会儿。它也知道我这次开门是不带它的,但它仍然徒劳地跟到门口,然后期期艾艾地看着我离去。每天我回来它都是跳起来和我拥抱(有一次我穿着丝绸衣服,在开门前,在门外我就把衣服脱了下来,穿着衬裙进屋的),并发出像是惊叫的声音,特别像一个人因为激动而语无伦次。那场面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见。那么,白驹是不是以为我每天的离开都是不回来了?而我的回来,都是绝望后的意外惊喜。那么就是我每天的离开都伤害了它。这种伤害每天叠加,到了它无法承受的重量。在我上班不在家的漫长时间里,它都在想一件事:主人为什么走了?我做错了什么?它很听话,讲卫生,从来不乱叫。它检讨自己,发现自己听话懂事,主人还是每天都走了。于是它想怎么才能阻止我每天的离开呢?它开始细心观察,发现我每天都是要穿上鞋子之后才能走。于是它看懂了,我得有鞋子才能离开,如果没有鞋子,我不就没办法走了吗?那么把那些鞋子都破坏掉,我没有了鞋子不就走不了了吗?这还是狗吗?竟然会逻辑思维!
这就是它不咬别人鞋子的原因。它不在意除我之外其他人的来去,只想办法让我留下永远别走。看来我每天和它说的去上班挣钱买好吃的,它根本没懂,或者懂了,但不为所动。它宁愿和我在一块儿饿死,也不愿和我分开一会儿。那么实际上,它一直在那个童年的鞋盒子里没有走出来。长大的只是它的肉身。我的房子,也只是个一百平方米的大鞋盒子。它在里面,不知道回来开门的,会是谁。那么每次它看着我离开,都是生离死别啊。而每天我回来开门进屋,它兴奋得大喊大叫地拥抱我,都是意外获救啊!没想到打开鞋盒子的还是我。打开门的还是我。我每天都回来,准时地回来。重复了好几个月,它怎么还不相信,怎么心里还没有底儿?为什么还要担惊受怕呢?但是,事实证明,它还是不敢相信,童年的伤痕无法自愈,还在疼,还在渗血。还在害怕打开房门的人不是我,打开鞋盒子的人不是凤。
朋友凤从C城来,驱车一百公里,他下车递给我一个鞋盒子,然后转身上车就走。我追着喊:吃完午饭再走哇!他说不吃啦,一面加快脚步,他不给我拒绝这个鞋盒子的时间。我打开那个40号男鞋的鞋盒子,白驹躺在里面,像一只白色的老鼠。我把它抱出来,正看到它的原主人凤转身离去。浑身颤抖的白驹对着凤的背影哼唧了两声(我知道它叫声的意思:你怎么走了,落下东西啦),就再没力气发出声音了。把它放到小区草地上,它站不起来,四条腿没有一条腿不抖。我抱着它转身上楼了。一个月前凤和我说过一次,我拒绝领养,因为我已有了一只狗。今天他突然来了,不由分说把鞋盒子给了我,一分钟不肯停留,转身就跑。
我不知这个螳螂一样的小狗,是什么品种,能长多大。它像是命运给我安排好的,到了某一个时间,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它只有四斤重。我每天都担心它的腿会折断。现在,也就几个月,白驹飞快地长大了。站起来到我的头那么高了。白驹的腿细且长、头细且长、腰细且长。全身流线型,皮下无脂肪,肋骨一根根纤毫毕现。杏核眼,双眼皮,吊眼梢。周身被短毛,白色,只有耳朵和尾部生装饰性长毛。双耳下垂,长毛飘逸,宛如神兽下凡。我曾和凤描述过白驹长大后的样子。凤说白驹是他从狗场要的,是纯种细犬,目前快要灭绝了,狗场老板正在为细犬申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对比网上的图片,对白驹的品种在细犬的基础上,找到了更为精准的分支:蒙古细犬。
我至今不知道朋友凤为什么弃养。他是知道它能长很大并且运动量极大,根本不能在城市存活?那么我这儿也是城市,他这不是把一个一年后的巨大生活难题,在一年前就用一个鞋盒子端给了我吗?这朋友还能要吗?虽然我因为白驹受苦受难,但我还是感谢朋友,没有白驹,我永远看不透世界,永远不知道每走一步都得倍加小心。脚下的路是冰,而身边的人是酒杯。生活的很多层面和人,没有白驹我都不能到达。白驹的长腿和速度,把我带到了一个看世界的新角度,让我把人间的犄角旮旯都看了个清清楚楚。
我抱着白驹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宠物医院,我说了大致情况,那个医生说,它这是病了。我说能吃能喝、能跑能跳、能破坏,这是什么病?大夫说,分离焦虑症。
我问医生,有办法医治这个焦虑症吗?医生说,只有多陪它。我说我除了上班,剩下所有时间,都陪它了。
医生又说,尽可能增加它的运动量,让它多跑动,转移它的注意力。运动还可以产生多巴胺,营养神经,产生愉悦感,让它快乐,于是焦虑就得到缓解。
白驹每天不能恣意跑跳,于是不快乐,就只剩下和我在一起的快乐,这成了它唯一的快乐,而我每天要上班,它每天唯一的快乐都会因我上班而中断。它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它惊恐不安。
陪伴我已做到极限,无法再增加,那么只能从运动下手,让白驹建立起第二个快乐。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格致《蒙古细》)

格致,满族,生于吉林,祖籍沈阳。吉林省作协专业作家。2000年开始写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从容起舞》等四部、散文选集《女人没有故乡》等四部、长篇小说《婚姻流水》、报告文学《乌喇紫线》。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林语堂散文大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格致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