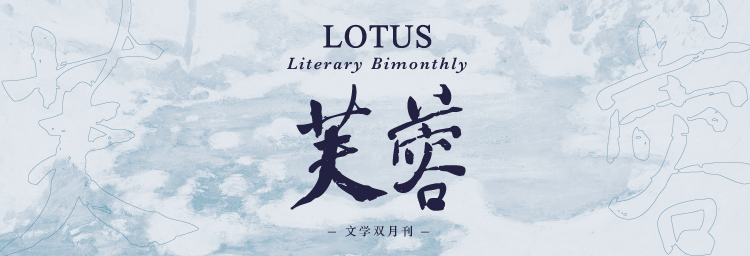

重游(中篇小说)
文/林培源
我们坐在大厅聊天,普通话、潮汕话交替,偶尔夹些粤语,绕着圆桌一轮轮转。吊顶垂挂下无数彩色琉璃,仿若一尾尾锦鲤海底巡游,灯光一打,青黄红蓝,流光四溢。从敞阔的落地窗望出去,靛蓝暮色拢近来,玻璃上即刻显影出一只八角亭的造型——那是汕头老城的标志性建筑,食客足不出户就能倚亭而坐,也算一种雅趣。
饭点已至,周边餐桌陆陆续续坐满了,说话声、谈笑声像从音箱传出,轻轻拍打耳膜。
服务生端来头道菜,坐我左首的椰子旋动玻璃转盘至杨爸跟前,右掌前伸,做了个“请”的动作,一口“潮普”招呼道,剪彩,剪彩。杨爸颔首微笑,用不锈钢勺舀起一勺,另一只手托起白瓷碗,先给身旁的杨妈盛了半碗。
这叫芋头芡实煲,椰子用他口音独特的潮普介绍说,潮汕菜一头一尾要“食甜”,讲究个“甜头甜尾”。
杨妈捧住小碗,细嚼慢品间,捏住汤勺的右手尾指微微翘起。她七十开外的年纪,穿一件鹅黄色的亚麻唐装,领口竖排盘扣,衣身绣有粉色蝴蝶与花瓣;刘海往后梳,弓起又高又亮的发髻,文了两道细长的眉,高颧骨,深眼窝,典型的东南亚华人长相。听到“甜头甜尾”的说法,她心领神会,点了点头。一颦一笑,仿佛从民国电影中走出来的富家太太。
下午两个钟头的讲座过后,我饿得低血糖,苦于没有随身带糖果,忍不住干呕,肠胃像被剪刀铰过,阵阵发痛。芋头芡实煲转到我面前如同救命稻草。一勺落肚,我才缓了过来。芋头的甜在舌尖留驻,鲜百合炖得粉糯,白果略带苦,裹了椰汁的甜在唇齿间滑动。
其他人轮流品尝,纷纷称赞“好食”。
挨着杨妈坐的阿钰问,阿姨,您会讲潮州话吗?
阿钰是陈铭新婚太太,在文旅局工作,落了班专门赶来赴宴。她戴一副厚厚的眼镜,说话时马尾辫在后脑勺摆荡。
杨妈放下勺子,轻声答,我其实是在怡保——马来西亚怡保出生的。
杨凯插话,就是那个很能打的杨紫琼老乡啦,语气透着戏谑,仿佛“杨紫琼”是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
杨妈嗔怪地看了儿子一眼,是啦是啦,怡保不但有杨紫琼,还有知名的河粉。
杨妈的话让我想起翻过的一本介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书。怡保旧称锡都,是霹雳州首府,有声名远播的“旧街场白咖啡”——十几年前我在广州读研究生,学校西门出来有家餐厅,招牌就叫这个。
杨妈自我介绍,我祖上是梅州的,讲客家话,先生才是正宗潮州人。随即又换粤语,但系我识讲少少广东话。
这番无缝切换把众人逗乐了。
柏齐接话,在英国读书时,有个四川同学问我,广东人是不是都讲广东话?
说到这里,柏齐顿了一下,这个问题取决于怎么定义广东话,如果特指粤语,答案就是“否”,如果指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答案就是“yes”。
柏齐说得像个绕口令,杨爸也加入话题中,马来西亚有客家话、潮汕话、福佬话,也有讲广东话的,我哋识讲少少啦。
杨爸声音浑厚,略带沙哑,他突然开口,把众人注意力吸引过去,最后那句粤语透出一股浓浓的潮州口音,略显滑稽,席上气氛更添喜乐了。
我留意到,讲“马来西亚”时,杨爸杨妈都把“亚”发作“哑”的音。
我问坐在右手边的杨凯,杨导,你会讲潮州话吗?
他意味深长看我一眼,拇指食指尖捏在一起,讲一点点。
见我有困惑,他正色道,不过最好不要跟我讲潮州话哈。
杨凯的坦诚让我吃了一惊。我猜想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应该遇到过无数次类似的疑问,说不定早已免疫,所以干脆以直截了当的拒绝来代替解释和澄清。
这时候,椰子凑过来朝我耳语,透露秘密似的,老先生好有来头,之前是东南亚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总。我端详杨爸——鬓角灰白,穿了件圆领的红色休闲唐装,上面缀满鹅黄色花纹;手机插在左胸的衣兜里,说话时,右手手肘支在桌面,半眯着眼,似笑非笑。我将信将疑,无法将眼前这位长相普通的老先生和“唱片公司老总”的身份联系起来。赴宴前,陈铭只提起过杨凯,没说他会带家人来赴宴。杨爸杨妈的出席,为这场聚会添了些家宴的味道。
实际上,聚会全因杨凯而起。他是马来西亚导演,拿过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陈铭说,请杨导来一趟不容易哦,我还帮你准备了书,到时送他。我感激地看了陈铭一眼,佩服他待人接物的周到和细心。他说的书,是我写的一部研究华南作家的专著。眼下,杨凯正在筹拍一部马来西亚华文小说改编的电影,这次来潮汕,就是想四处走走看看,找一找拍电影的灵感。
杨凯体形微胖,像头棕熊,一件灰黑色圆领T恤衫(上面印了东京电影节的logo)套在身上,衬得整个体形更壮硕了;头发自来卷,后脑勺扎了根小辫子,说话时两枚上门牙露出来,我的目光总被他笑眯眯的双眼和厚厚的嘴唇吸引。要不是陈铭事先透露,我会以为杨凯是哪个片场的工作人员,或者临时串场的“茄哩菲”。
我的目光在清瘦的杨爸和胖硕的杨凯之间来回巡视,试图在他们父子身上搜寻一些相似点。整场饭局下来,令我好奇的不是同龄人杨凯,而是坐我正对面的杨爸。他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神情,让你想一探究竟,又觉得相去甚远。陈铭说杨凯是移民三代,意思是,他们家族最早南下是祖父那一辈。那么,杨爸是在哪里出生的?潮汕?马来?我觉得他千里迢遥来到潮汕,一定装了一箩筐的故事。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好奇心一旦被勾起,就如无数条虫往我身上钻。我拿起手机,在浏览器搜索框里输入“马来西亚”“唱片公司”“董事长”“总裁”之类的关键词。页面上蹦出几条链接,我点进其中一条,随即看到杨爸出席某个音乐节的照片。早年的网络照片像素有点模糊,但仍能清楚看到,杨爸满头黑发,面带微笑,对着镜头竖起了右手大拇指,样貌比现在年轻了二十来岁,一身黑衣黑裤的休闲装,像是闯进活动现场的一位衣着朴素的街坊。有趣的是,与他合照的歌手明星个个表情恭敬、谦卑,看起来犹如配角。照片右下角,“大马xx”的水印赫然出现。我猜测,这应该是杨爸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拍下的照片,报道称杨爸为“新马地区流行音乐教父”,是发掘了几代新马华人歌手的伯乐。我在心底惊叹,一些熟悉的旋律在我耳畔萦绕。大学时我的手机铃声,就出自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的代表作。我把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再次落到杨爸的身上。由于隔了好几个座位,我可以假装不经意打量他而不至于被察觉。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林培源的中篇小说《重游》)

林培源,1987年出生,广东澄海人,青年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香港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小说见《花城》《作家》《江南》《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广州文艺》等,曾获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出版有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神童与录音机》等。
来源:《芙蓉》
作者:林培源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