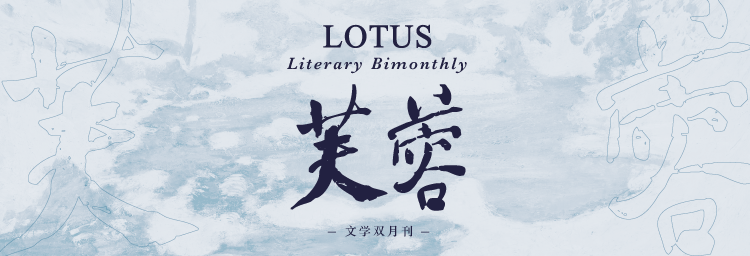

去柳青故里
文/吴佳骏
1.缘起
黄昏后,夜幕降临。我关闭门窗,拉上窗帘,将灯火、月色和树影全都挡在屋外,连同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和窗台遮檐下蛐蛐的鸣叫声。屋内瞬间安静下来。我坐在书桌旁,让四周的书籍筑起的文字、美学和思想之墙将我包围。入夜之后,我需要给自己修筑一座城堡。唯有躲进城堡,我的呼吸才是畅快的,心灵才是自由的。
曾有人对我说,我是属于夜晚的。我觉得他说得颇有道理。在白昼,我总感觉自己是不真实的,我的真实都被生存剥夺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见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游离的,像风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浪涛浮沉,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远处的灯塔。
夜晚就不一样了。我不用听谁的命令和差遣,也不用看谁的脸色和表演,更不用听各种是非和谣言,我纯粹是我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用面向他人说些不明不白、不真不假、不好不坏的废话。我完全可以沉默,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做个午夜的孩子,是我所向往的。
许多哲人都守候在午夜。维特根斯坦、苏珊·桑塔格、洛扎诺夫、齐奥朗、阿伦特、舍斯托夫、本雅明、阿多诺、罗兰·巴特、克尔凯郭尔、巴什拉、普里莫·莱维……好大一个群体,他们如夜空中的星星,熠熠生辉。我一抬头,就能望见他们。望见他们的时候,我是坚实的、有力量的。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虚弱,也清楚自己的平庸。
或许正是因为虚弱和平庸,我特别渴望光。齐奥朗说:“我是一个没有朋友,也没有上帝和恶魔的约伯。”他还说:“只有通过思想和行动扩大你的不幸,你才能从中找到快乐和幽默。”
回顾和省思我自己,我有快乐和幽默吗?很汗颜,我已经多年没有过笑容了。我的笑容早已被他人的嘲笑分割。那么,我幽默吗?我以为我有。不少时候,我都在逗人发笑。我活着的意义,主要就是取悦他人。可是前一阵子,我才发现自己的愚蠢。那些被我的幽默逗笑的人,往往都有一颗哭泣的心。也就是说,我的幽默并未给人带去真正的开怀和轻松。事实证明,我的幽默是失效的,我呈现给他人和世界的,只有荒诞。
于是,我习惯躲进暗夜,采集哲人散发的光芒。
就在那天夜里,我被一束强光照亮。那束光是一个法国人散发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弗朗兹·法农。他在散发这束光的时候已经病危,但他丝毫没有恐惧。他唯一的愿望,是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向人类散发最后一道光。这个倔强的男人做到了,他散发的光酷似一颗启明星,照亮了“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老师打来的,他说最近有家出版社替作家柳青出版了一部佚作《在旷野里》,出版方策划了一个研讨活动,想邀请我参会,会后可到柳青的故乡陕北吴堡县寺沟村走走。我没有犹豫,爽快地答应了。在我心中,李建军老师也是中国文坛的一束光。
我喜欢和信赖那些自带光芒的先生。
在旷野里,在旷野里……我默念着这句话,全身似被一股吸力所牵引。或许,在午夜里待得太久的我,是该到旷野里去瞧瞧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的附录诗歌中说:“我是孤独的;我的周遭溺没在谎言中。生活不是在旷野上漫步。”
的确,生活不是在旷野上漫步,而是去经风历雨,迎接雷霆和闪电。
2.雨途
天微明。我从睡梦中起床,打出租车直奔重庆西站。我要乘坐的开往西安的高铁,将在七点十分出发。我坐进出租车后,一时竟有些恍惚。我感觉自己正在从梦境中出逃,要去一个偏僻的村落。那个村落黄沙漫漫,落日浑圆。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土塬上站着成排的树,树下蹲着几个雕塑似的人,在眺望什么。这个画面反复在我的大脑中闪现,像一个人间隐喻。
车窗外,天色灰蒙,夏日山城的溽热,让人有窒息之感。艾米莉·狄金森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黎明时分充满了露水的味道,像祈祷声那样安静。”我不知道这位美国诗人所感受到的黎明是怎样的黎明。我缺乏艾米莉·狄金森那样的敏锐诗思,我在中国西南山城感受到的黎明是燥湿的、喧腾的,没有丝毫安静可言。街道两边的早点铺熙攘不已,排队买早餐的人神色慌张。他们大多是些上班族,都怕赶不上拥挤的地铁而造成上班迟到。如果那样,他们不但全勤奖拿不到,还有可能被炒鱿鱼。要知道,这些毕业于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他们有的刚做了爸妈,有的正在赡养家中的老人,有的正在分期归还房贷,都需要钱养活自己,故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工作,担心稍有闪失就丢了饭碗。
也许,他们曾是一群热血青年和理想主义者,曾为自己就读于名牌大学而骄傲和自豪,曾幻想以所学知识开创一片新天地。然而,事与愿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头顶的光环和荣耀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存在感。他们逐渐将自己变成了“工具人”。
谁都知道被物化是可悲的,但谁都无法逃脱这种可悲的下场。在生活的海洋里翻卷,只有比黎明醒得更早的人,才可能望见前方稀薄的曙光。
那么,我是比黎明醒得更早的人吗?当然是了。那众多坐在高铁站内的椅子上候车的人都是。他们背包拖箱地揉着惺忪的眼睛,望着显示屏上黄绿相间的钟点,生怕稍不留神,列车就会将他们遗弃。我和他们都需要去远方,尽管彼此的目的地不同,目的也不同。我去远方是因为一个已故的作家,他们去远方是因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请原谅我不能说他们是为了梦——梦是容易幻灭的。我承受不了人的梦幻灭之后的无助和绝望。我也不能使用漂泊这个词,漂泊是无根的,意味着变数和坎坷。我希望从黎明出发的每个人都能在天黑前抵达各自的归宿地。当然,在这群出发的人中,有的原本就是回家。但更多的人,看样子出发后就回不了家,至少短时间内回不了家。我对能够回家的人感到欣慰,对不能回家的人报以同情。
许多年前,我也是一个流浪者。独在异乡,想家回不去。凛冬将至,我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想起白居易写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诗句,不禁潸然泪下。我跟白居易到底没法比,他作此诗时三十三岁,任秘书省校书郎,宦游邯郸,有客舍可栖。而我那时只是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浪子,别说宿客栈,有杯热水喝就不错了。因此,白居易的“思家”是躲在棉被中的缱绻,我的“思家”是坐在寒石上的惆怅,二者有天壤之别。
如今,我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忆及这段往事,心中仍在飘雪。同车厢的其他人皆昏昏欲睡。醒得太早了,是该补个回笼觉。听着身旁之人的鼾声,我也来了睡意。不多一会儿,那个隐喻似的画面又闪现在我的梦中——黄沙弥漫的村落,落日下的土塬,塬上站立的树和树下蹲着的人……
当我被一个小孩的哭声吵醒,列车已驶过四川的苍溪。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骤雨,雨滴砸在车窗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晶亮的水痕。远山云雾缭绕,田野稻穗披绿。放眼望去,能感受到一股来自大自然的诱惑之力。
我再也睡不着,索性掏出柳青的小说《在旷野里》重读,该书第一章节恰好写的也是发生在列车上的场景。一个名叫朱明山的县委书记,带着上级领导的嘱托以及自己的理想走马上任。在列车上,他一边在大脑中规划着治县方略,一边听老百姓扯闲篇。这些质朴、憨厚的农民,在车上看报纸,谈论土地改革和爱国公约,谈论抗美援朝武器捐献和棉花征购……朱明山越听越起劲,以致他也忍不住参与到农民的讨论中来。斯情斯景,让他这位父母官尚未上任,就已经预感到他将要开始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
柳青不愧是柳青,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年仅三十七岁。他在小说开头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就将一个生活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将几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生动。柳青无疑是个文学天赋极高的人,他担得起名家大家的尊称。
窗外的雨仍下个不停,下在苍溪,下在广元,下在朝天,下在汉中,下在洋县,下在西安西,下在西安北,下在我重新读完《在旷野里》的最后一句话:“朱明山不吃饭,就和吴生亮一块儿走了。”
我跟着雨,走出西安高铁站。众生跟着雨,消失在雨中。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吴佳骏的散文《去柳青故里》)

吴佳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芙蓉》《山花》《大家》《作家》《花城》《天涯》《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两百万字,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数十种。著有散文集《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我的乡村我的城》等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重庆文学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吴佳骏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