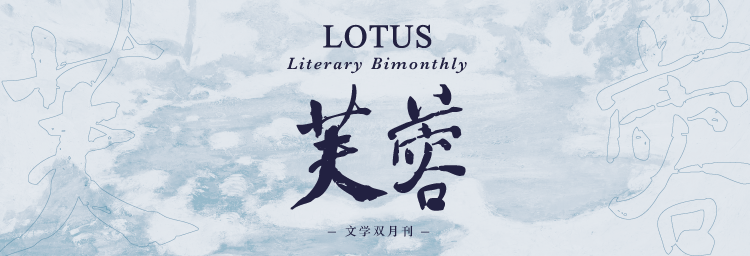

命运来信(中篇小说)
文/西元
老刘是一位战略学教授,今年五十岁,专业技术大校军衔。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座民国时期建筑的三层走廊最里面。如果不开灯的话,整条走廊终年都会很幽暗,唯有水磨石地面泛着灰白色微光。办公室的窗子也是旧式风格,有一人半高,每次擦上半截玻璃都得在窗台摆张木凳,然后小心翼翼踩到上面才行。窗外有一棵大杨树,年龄比老刘还要大上一二十岁。树冠高出建筑一头,像是把楼房搂在怀里似的,到了夏季房间里便进不来多少光线。向远处看去,是一片很大的略带起伏的浓绿色草坪,更远处是一座小山和一面湖水,颇有些颐和园的味道。
楼里少有人说话和走动。坐在一把老旧的木椅子上,望着窗外明亮鲜艳甚至有些刺眼的景色,老刘时常会陷入无我的出神状态,仿佛一切有形之物都消失了,而这把椅子就是茫茫宇宙的中心,历史长河从身边泥沙俱下地奔涌而过。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他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些很根本、很抽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与他的日常工作,与他的职务晋升并无太大关系。
比如说什么是战略?比如说什么是正义战争?还比如说什么是敌人?老刘是在长江边上的一所军队院校上的大学,专业是哲学。其实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便分析过这些问题。年轻时上过一门课,叫军人伦理学,就讲了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不义战争,至今还隐约记得那本书里引用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类的话。多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不少战争。出于职业原因,老刘都比较深入地研究过,也深知战争的血腥与残忍。但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所见所闻,他都坚信,人世间存在着正义战争,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他匆匆浏览过一些小说和电影,被称为“反战”云云,说它们有多么多么深刻。老刘虽然不大懂文学艺术,也不明了其中的高深之处,但对之是颇有些嗤之以鼻的。“反对一切战争”这种说法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的。试想,当异国的军队已经来到了你的土地上,开始屠杀你的同胞,掠夺你的资源,开始篡改你的历史,割断你的血脉,你还要“反对一切战争”吗?你拿什么来“反对一切战争”呢?每思及此,老刘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日本鬼子身上穿的土黄色军服,军服上溅着一块一块血迹。这个画面深深印刻在脑子里,无法磨灭。
那么,何谓战略呢?有时在沉思之中,老刘会突然觉得自己简直是孟浪了三十年。过去,他会认为,战略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只要抓住普遍性的东西,特殊性的种种矛盾便迎刃而解。他还会很自信地认为,一种战略思想,如果用了十个字还不能生动地概括出来,那它一定是不成功的,而且注定不会成功。人过中年,老刘慢慢意识到,人的理性与他们所不得不身处其中的世界之间,其实隔着一条又深又宽的鸿沟。老黑格尔给了人间一把智慧的梯子,使得人们可以从此岸走到彼岸,而且,人们似乎至今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就好比老刘自己。但是,老黑格尔没有告诉世人,梯子下面是怎样的万丈深渊。
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信息技术、无人技术、虚拟技术、生物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让这个世界变得让人不敢相认了。老刘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那时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家里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记得《新闻联播》开头部分有一段火箭发射的视频,老刘那时一直以为火箭喷出的火焰是红色的,直到有了彩色电视机才惊奇地发现那火焰竟是蓝色的。小时候的自己敢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吗?
世界已变得如此,那么未来战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个事情可能很残酷,却是真相,那就是战争永远比人类社会先走一步,所有的新兴技术都注定会很快被用到战争上面。忘了是多久之前,几年前吧,发生过一件事,让老刘印象深刻。那一次,他无意间对同事说了几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当我确定在实力上允许,并且是正义战争的时候,我夺取胜利的意志是不会被改变的。”同事微微一笑,问道:“是这样的吗?物质和意识之间的距离有时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不信,咱们做个小实验。”之后,同事给老刘看了七八段短视频。每个视频的内容都差不多,拍的是某个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被误解、被歧视、被疏远、被欺负,这些场合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不光被异族人孤立,还被自己人排挤。看完了视频,同事笑呵呵地问道:“有什么感觉?”老刘说:“全都在针对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朋友了!”同事又问:“如果你是一名指挥员,或是一名战士,抱着这种孤立无援的心态,你还能说你夺取胜利的意志不会被改变吗?”同事接着说,“更进一步说,现在是我把这些东西给你看,如果把我换成了某种算法呢?大数据的威力可要比我一个肉身之人强大亿万倍!那个时候,凭你个人的智慧,凭你个人的辨别能力还有反击的机会吗?”
总之,这是一个特殊性如洪水一般泛滥的时代,需要解决的精神性问题接踵而来。如何回到普遍性那里去呢?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去呢?这个问题让老刘深深困惑着。
还有,什么是敌人?过去,老刘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下意识地认为这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敌我,敌我,敌人是与我相对的一个概念,对我形成威胁的人或势力都可以称为敌人。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吗?据老刘所知,古往今来的先贤大哲们似乎也没有对此说过什么,这个问题好像被遗忘了。
老刘注意到战争史上的一种现象。某些国家赢得了战争,也就是说战胜了对手,但许多年后,这些国家却垮掉了。而有些国家输掉了战争,但许多年后,它们却令人吃惊地走上了复兴之路,成了全新的国家。如此看来,敌人对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毫无疑问,战争的结局只有输赢,我与敌人的对决只有胜负,除此之外绝无其他结果。老刘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就像他坚信这世上有正义战争一样。这个信念不是来自概念的推导,而是来自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血的经验与教训。但是,仅仅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够了吗?仅仅击败敌人就够了吗?
什么是敌人?这反倒成为让老刘殚精竭虑的问题。该怎么把这个问题追问下去呢?有时,当老刘的思绪精疲力竭时,当办公室的光线昏昧难辨时,他会有种幻觉,一个黑色的影子就站在门外。它披着乌黑的隐形斗篷,面目不清,走路如同鬼魅一样轻飘飘的。它在说什么,但一切都寂静无声,只能靠你自己鼓足勇气去领悟、去理解。它可能会推门而入,也可能会转身离去,而这一切取决于你是否足够勇敢、足够智慧。你的勇气和智慧是一束光,那个黑色的影子最害怕的是这种光,因为光会让它原形毕露。当然,这道光不仅照亮了黑影,也照亮了自己,照亮了这个世界。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西元的中篇小说《命运来信》)

西元,1976年生,籍贯黑龙江巴彦。曾任排长、干事、代理组织科科长、教导员、创作员。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部文学创作员。著有小说集《界碑》《死亡重奏》、长篇小说《苦难山》等。曾获第二届《钟山》文学奖、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等。
来源:《芙蓉》
作者:西元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