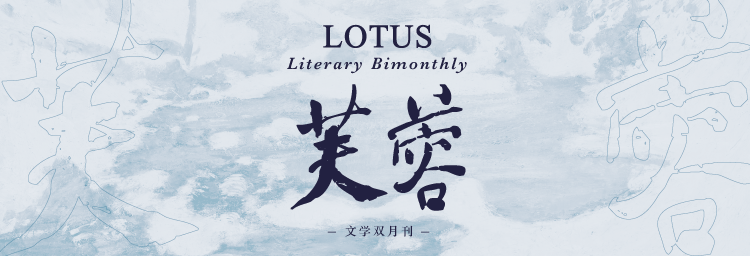

大熊猫(短篇小说)
文/朱辉
时间过去很久了,事情我当然记得,想起来连细节都历历在目,但是我更愿意简略地讲述这段往事,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1985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留校工作。”这是我的简历中必不可少的一句。事实上学校后来改了名,叫河海大学。简而言之,我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留校工作却留在了河海大学,按惯例,先做了几年辅导员。我时常想起的那件事,就发生在我当辅导员期间。
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1985级的水利工程专业,女生很少,每个班两三个而已。全校的新生几百人,女生不超过五十个。我工作是很投入的,跟学生同住一栋宿舍楼,他们六到七人一间,我住顶头一个单间;吃饭也在一个食堂。刚开始时兴致勃勃,连他们上课,我都去,坐在最后一排,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科书就用我四年前用过的。慢慢地就疲沓了,那时我已开始写小说,既然已确定了人生路径,我又何必在这些课程上浪费时间呢?
学生们跟我相处得很好。我只比他们大了三四岁,现在看看照片,才知道自己那时也是稚气未脱,即便想端起老师的架子,也实在不太像。我们不但吃住在一起,体育活动也混在一起,常常我在宿舍里看书,走廊里杂沓的脚步就响过来了,伴着篮球在地上拍打的声音,不等他们敲门,我已经换好衣服鞋子,拉开门,随他们一起去运动场,玩到天黑才收场。
我酷爱篮球,对足球却很畏惧。我没毕业时也随大流试过,很不幸,第一次上场凑数,运球,想模仿普拉蒂尼来个人球分过,不想重心没有掌握好,本该抬脚拨一下球,我却踩实了,球一滚,右脚崴了,顿时疼得龇牙咧嘴,结果是,我瘸着脚在校园里现眼了一学期。从此我远离足球。我带的两个班却有不少迷恋足球的,他们基本身材不算高,但又特别灵活壮实。第一学期,两个班的体育委员都是我指定的,一个特别高,一米八五,篮球打得好;另一个擅长乒乓球,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就做了二班的体委。后来才发现,那个乒乓球高手更喜欢的是足球,两个班的足球热就是他带起来的。因为对足球无甚兴趣,我对这个足球狂热分子并没有太在意,有一次他在走廊里卖弄脚法,一脚踢碎了走廊顶头的一块玻璃,被宿舍管理员告到系里,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听他同学都喊他“罗拉”,很奇怪,因为他只是姓罗,一问才知道,这外号最初叫罗拉尔多,听起来十分威武,可他恰巧长着一对招风耳,对“耳朵”特别反感,谁喊他就要抗议,甚至要上去动手,大家只好无视他的耳朵,简称“罗拉”了。
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简称,连我都叫他“罗拉”了。这罗拉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并不强壮,但在水房里冲澡大家都能看见,他精壮得很,浑身腱子肉。打乒乓球他戴着眼镜,踢足球蹦纵窜跳,当然更要戴着,他聪明得很,用两根橡皮筋接起来,绕到脑后挂着眼镜腿,声称这叫“加强筋”——他读工科才一年多,居然就会用术语了,也是个聪明人。我经常在宿舍里听到走廊里乱哄哄的,足球在地面上发出与篮球不一样的声音,就知道他们又去踢球了;我扔下书,起身看看窗外,总能看见罗拉一路盘着球朝运动场而去。
足球是与众不同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之类,女生也很喜欢玩,羽毛球就被戏称为“情侣运动”;即便是篮球,女生也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男生比赛,她们会在场边喝彩,兼管帮男生看着衣服,这成就了好几对爱情,传为校园佳话。足球就不一样了,也许是因为太粗野,半天进不了一个球也还罢了,突然就会吵起来,面红耳赤、怒发冲冠的也不知道吵个什么,反正女生不感兴趣。从这点看,足球是一项更纯粹的运动,完全没有玫瑰色,与女生无关。可怜整个学校女生也就区区百十个,我怎么能想到,罗拉的足球,还就跟女生挂上关系了呢?
跟罗拉挂上关系的女生,我已记不清她的名字,但忘不了她的绰号:“大熊猫”。大熊猫是可爱的,但这个绰号不可爱,带着恶意,至少透着少年轻浮的味道。
如前所说,我那时已沉迷于文学,自己也开始写小说。往往睡得很晚,中午还要补个午觉。那是一个春日,阳光照在床上暖洋洋的,我睡得很沉,似乎正做着梦,具体什么梦,当时就不记得了。我被吓醒了。宿舍的门砰砰地响了,简直像有人在砸门。我猛然坐起,茫然四顾,不知身在何处。门又响了,伴着焦急的喊声:朱老师!朱老师!
我套上长裤开了门,门外站着三个人,领头的是一班的体育委员,身高一米八五的那个。他身着运动衣,满头大汗,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好了,出——出事了!一看他就是刚从运动场过来,我让他不要急,慢慢说。他喘匀了气,说清楚了。我一听,也傻眼了。真是出大事了!
宿舍门口的场面我不想细说;此后的好几天,我处于惊惧忧心和奔波忙碌之中,此刻我也不想娓娓道来。只说几个片段:
——一班和二班各组一个队,中午去踢比赛。艳阳高照,生龙活虎。场上很激烈,比分一比一,很胶着。罗拉已经进了一个球,斗志昂扬近乎亢奋。一个高球飞来,他飞身冲顶,一班的另一个同学也跃起争抢。他们撞在一起,罗拉技高一筹,他头一晃,卸下球,带起来往对方球门奔去。他盘带几步,慢了下来,捂着腰站住,朝场边举举手,不去管还在地上滚动的球,径自走到场边,站在球场边的蒿草边观战。不一会儿,他人不见了,原来是躺在地上了。他苍白着脸,手伸出蒿草摇着,嘴里说:喊医生!
——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他的同学。我赶到时,罗拉已经被推入了手术室。一个男医生走出来,对我说:他内脏受损,大出血,必须剖腹探查。你们谁签字?幸亏我来医院前已经向学校汇报过,我拿着笔,千钧重,正不敢下笔,人群分开一道缝,副校长过来了,他庞大的身躯令人信赖。他从我手里接过笔,签下了他的名字。走廊里叽叽喳喳地都压低着声音,难熬的半小时。手术室门突然打开了,那个医生双手鲜血,托着一个血糊糊的东西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医生说:肾脏挫裂,只能摘除了,喏,你们看仔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人的肾,像个猪腰子,裂开了。血腥气很重,我一阵反胃,心中茫然。医生又说:他大量失血,需要立即输血。血库里不够,你们立即去想办法。我瞪大眼睛看看他,一班的高个子体委说:血库里还不够?你们是医院啊!医生说:他是RH阴性血,俗称“熊猫血”,稀有!
——校园的各处广播里,传出了征集献血者的号召。我抓瞎之下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一招。广播站反复播送,声音嘹亮。效果是有的,几千人的学校,来了几百人,不能算应者云集,但也浩浩荡荡了。他们排队验血,一小时后,结果陆续出来了。几百人,唯一合格的捐血者是一个女生,她也是熊猫血。
——她是自愿者,是救星。校园里女生如此稀少,我们肯定见过,但我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听说是自动化系的,与我带的两个班一样,也是二年级,因为有些公共课在一起上,罗拉应该跟她在一个课堂里坐过。他伤愈出来后,自然就对上号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叫什么,我现在记不确切了,罗拉现在还记不记得她,我不知道。这女生有个特征:她右颊有一块胎记,半掌大小,几乎占据了她眼角到嘴角的全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缺陷。在捐血以前,我曾听到过有学生私下里称呼她“大熊猫”。这太促狭了。写小说养成了一个毛病,喜欢联想。她的名字里有个字,“莲”,我曾想起了一种植物,“半边莲”。我小时候,叔爷爷生病,有个偏方,要一味药,就是半边莲。父亲带我去田野里找,那是一种野草,花开如莲,只有野菊花大小,它半边开花,另一边缺着。罗拉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后,我找到了她,感谢她,表扬她。即便我暗自为她取了一个文学性的绰号,远胜“大熊猫”,其实也不能当面喊她“半边莲”。她朝我笑笑,立即低下头,侧过脸,轻声说了一句什么,我都没有听清。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朱辉的短篇小说《大熊猫》,本篇系作者回忆录素材之五。)

朱辉,1963年生,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万川归》和中短篇小说集多部,有《朱辉文集》(十卷)出版。曾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汪曾祺文学奖、高晓声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来源:《芙蓉》
作者:朱辉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