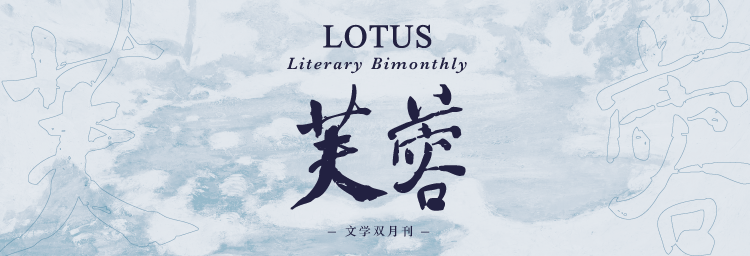

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文/江子
1
夏天某日,到江西省泰和县龙洲村,寻访布衣刘过(字改之)。龙洲村是刘过家乡,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之后他出外求学,求职,求友,求功名,漂泊一生,最终客死昆山。他求功名不得,求职亦不得。然而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他因诗名世,仗诗出游,与他交往的人,有军曹、文士、诗人、侠客、浪子、妓女,甚至宰相、皇帝……他与诗人相互唱和,与山水楼阁相看两不厌,伤春悲秋,愁离恨别,对酒当歌,快意江湖,又在人群中时时不忘藏起自己袖口磨破的部分。如此传奇,如此落拓不羁,他的故乡,应该保留了他不少的记忆才对。他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流浪期间,也多次因母病或怀乡返回家中,常常居住数日再踏上行程。他是给村庄带来声誉的人,村子怎能不精心保存关于他的物证?
然而没有。在泰和,龙洲村是个小村,只有数十户人家。它是村中之村——它与南门村、排田村两个自然村一起组成一个行政村。行政村名南门,因为三个自然村,南门村人口最多,行政村自然以南门为名。可如此一来,龙洲村的存在感就弱。另外,它还是城中之村。它身处泰和县主城区,建筑多为多层簇新楼房,除了部分菜地,已经没有多少村庄的属性了。村与村之间界限模糊,分不清哪里是南门村、排田村和龙洲村,分不清城镇与村庄。没有明确的地理标志和村庄特性,龙洲村靠什么来指认自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会不会有一天,龙洲村这个小小的、面目模糊的村子,会被城市挤占和吞噬?
如此村庄,连保住自己都难,怎么可能保得住八百多年前的村民的记忆。走进龙洲村,发现也许是城中村的原因,村子太新了,楼房是新的,道路是新的,树木是新的,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是新的,整个村庄好像就只有五十岁那么老。就连祠堂也是新的,祠堂钢筋水泥砖混结构,虽然努力拟古,比如飞檐翘角,但明显看得出修建的时间不长。祠堂对联说的是村庄来龙去脉,供奉的是龙洲村开基的祖先,刘过踪影全无。村子里有一座惜字塔,相传是刘过所建,可也是新的,说是原塔损毁,几十年前原址重建,可毫无古意,也没有任何文字证明跟刘过有关。有人取来刘氏族谱,竟是一本铅字印刷品,开本类似《现代汉语词典》,字迹密密麻麻,刘过应该列于其中,但要从这厚厚一本族谱里,找到大约五号字体大小的刘过,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村庄没有为刘过建造的古老牌坊,没有为刘过塑造的石头塑像,没有以刘过命名的休闲广场。刘过死在江苏昆山,这里自然也没有他的墓地。刘过在这里是不重要的——牌坊乃是朝廷重器,为旌表忠臣孝子贞妇,泰和所属的庐陵,自古称为人文渊源之地,曾有三千人考中进士,忠孝节义者众多,牌坊堪称林立,仅泰和一县就有不少,如蜀口洲村祖祠牌坊上书“五经科第”,是张扬该村有二十多名子孙列进士榜,与龙洲村同属澄江镇的杏岭村北明朝五朝元老杨士奇墓,有牌坊上书“与国咸休”。刘过没有功名,也没有因忠孝显赫乡里,他怎么有资格获得牌坊旌表的待遇?同样的道理,他怎么有资格被塑成塑像命名广场?
可牌坊与塑像,并非关乎历史记忆的唯一载体。土地无言,但土地是古老的。这里的土地肯定记得,它的子孙刘过是如何在这里出生、长大,如何满怀希冀地出走与忧心忡忡地回返。同样,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肯定也记得,它是怎样把刘过带走,直至步入最终无家可归的境地。
有没有可能,正是住在流动不息的赣江边,小小的龙洲村因此有了浪迹天涯的心性,刘过的血液里因此就有了羁旅的基因?
可刘过最初离乡的旅迹,并不是从赣江开始的。他的第一次出走,乃是去湖南长沙求学。从泰和龙洲村去长沙最近的线路,并非水路,而应该是陆路,向西南出发,从莲花过萍乡,大约二百公里就到了长沙。
在湖南,这位一脸青涩的庐陵才俊,一身土气的农民后裔,得以养成了他疏狂的性格,他的诗词创作,也因此濡染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2
刘过是吉安(庐陵)人,庐陵文化无疑是他的精神底色。漫观他的一生,他的身上有着他的乡党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等共同的性格特征:激烈、决绝,只认是非不辨利害,同时以士大夫道统为宗,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使命。可他又同时有着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等庐陵才俊不一样的疏狂气质。这种气质,绝非自生,应该与他在长沙的求学有关。
关于刘过的湖南求学,历史记载的笔墨寥寥。偶见刘过中年之后在《与许从道中书》中说起:“某自借湖南之次,默默无闻……方珉隐先生教学于湖也,从游之士无虑数百人,然而获亲且近者,亦不过六七人。”
方珉隐先生即浙江永嘉人戴溪。戴溪是南宋著名学者,少有文名,淳熙五年,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长沙)南岳庙,出任湖南潭州石鼓书院山长。应该是那时候,刘过投身于戴溪名下,成为石鼓书院的一名学子。“从游之士无虑数百人,然而获亲且近者,亦不过六七人”,言下之意,石鼓书院学子数百人,与戴溪最为亲近的学子,也就六七人。刘过无疑是其中之一。
然而刘过的个性与戴溪毫不相关。戴溪参加别头省试第一,说明其出身于官宦之家。所谓别头省试,是宋代为限制官僚、士族子弟应试的特权,规定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时必须加试复试,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参加考试应该另立考场别派考官,即“别头试”,是比科举考试还要严格的一种考试制度。如此出身的士族子弟,多温和沉静、张弛有度,戴溪也毫不例外。戴溪以别头试第一进入南宋官场,深谙危墙不立危邦不入,一生平顺少有坎坷,最终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是典型的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士大夫。他在石鼓书院当山长之时,撰有《石鼓论语答问》一书,阐发《论语》义理,持论平允,朱熹以为近于道。宋史说其“素行平易谨慎,不为新奇可喜之论”。他的故乡永嘉(温州),历史上也几乎不产狂士,孕育于永嘉之地、南宋时期流行的永嘉学派学说风靡全国,也是极其理性的学问,以农商一体、富国强兵为主张,没有丝毫的狂狷成分。
不是得于其师戴溪,刘过的疏狂性格,只能从湘楚文化中找到其源头。湖南古称湘,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三面环山,四水竞流,丘陵起伏,河谷纵横,气候湿热,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植被丰富,水泽广阔,最宜生产渔稻,也生产巫与神话。春秋战国时期,因四面齐、晋、秦等皆为强邻,楚培养了不畏强悍的心性,又加上糅合了中原商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以及汉苗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湘楚之地,自古就养成了以屈原、贾谊和怀素为代表的决绝、自由、标新立异之人文性格,表现在文学,就是以《九章》《离骚》为代表的,以奇诡的想象、夸张的书写为特征的浪漫主义风格。农家出身的少年刘过一到长沙,瞬间被湖湘文化所裹挟,其几近无所依傍的白纸一样的灵魂,被注入决绝、自由、疏狂的湖湘文化因子,几乎就是命中注定的事。
刘过后来在诗词里谈起湖南,不免眉飞色舞,如饮甘泉:
万里湖南,江山历历,皆吾旧游。看飞凫仙子,张帆直上,周郎赤壁,鹦鹉汀洲。吸尽西江,醉中横笛,人在岳阳楼上头。波涛静,泛洞庭青草,重整兰舟。
长沙会府风流,有万户娉婷帘玉钩。恨楚城春晚,岸花樯燕,还将客送,不与人留。且唤阳城,更招元结,摩抚之余歌咏休。心期处,算世间真有,骑鹤扬州。
——《沁园春·万里湖南》
“万里湖南,江山历历,皆吾旧游”“吸尽西江,醉中横笛,人在岳阳楼上头”“波涛静,泛洞庭青草,重整兰舟”“长沙会府风流,有万户娉婷帘玉钩”。在刘过的笔下,湖南于他,是何等风流快活之地,也是何等的情深义重之所!
而在另一首名为《沁园春·观竞渡》的词里,他以更加沉郁的语调写下了对湖湘文化的理解以及对湖南的深情:
画鹢凌风,红旗翻雪,灵鼍震雷。叹沈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哀。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空江上,但烟波渺渺,岁月洄洄。
持杯,西眺徘徊。些千载忠魂来不来。谩争标夺胜,鱼龙喷薄,呼声贾勇,地裂山摧。香黍缠丝,宝符插艾,犹有樽前儿女怀。兴亡事,付浮云一笑,身在天涯。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江子的散文《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江子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