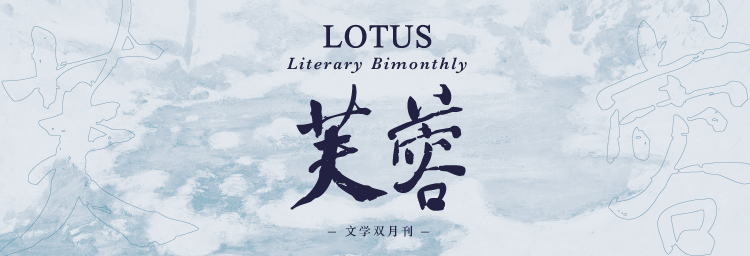

寻隐者不遇
文/詹谷丰
一
贾岛是第一个用诗歌穿越到我身边的古人,他的《寻隐者不遇》让我看到了一个人间烟火之外的隐身之人。
贾岛诗里的隐者,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采药者。少年时代读《寻隐者不遇》,只觉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再读此诗,却觉得隐者身份可疑。一个外人可以轻易拜访的人,即使身居深山草庐,即使入云深处采药,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那个来自俗世的访友,即是他假隐或者暂隐的证人。
“隐者”这个词,我一直以为它有远方和古代的血缘,离我们越远的年代,越能找到隐者的踪迹,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乱世里,隐者以群体的面目出现,他们的风骨,为浇漓的世界树立起一根坚硬的脊梁,他们的风头,无意中盖过了叱咤风云的帝王。
许由,是我心目中清洁精神的源头。当他知道尧帝欲传天下于他的时候,赶紧躲进了箕山。他的拒绝姿态,并没有让尧放弃禅让的想法。第二次,尧降低了要求,请许由做九州长。许由不仅没有接受,而且觉得受了侮辱,他赶紧跑到颍水边,掬水清洗那被污染了的耳朵。
人类五官中的耳朵,在隐士的决绝下被动出场。耳朵不具备眼睛的拒绝功能,它无法像眼睛一样封闭关门,尧的声音,无法选择地进入了许由的耳朵,所以,许由必须借助水的功能,清洗被禅让一事污染了的器官。
巢父的出现,是俗界的意外,也是许由猝不及防的精神挫败。牵着一头牛犊来河边饮水的巢父,问许由何故洗耳,许由用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此事,所以来颍水洗耳的话如实回答了巢父。
数千年之后,我依稀可以猜想,巢父的嘲笑声,一定让许由无地自容。巢父的讽刺,每一句都是当头棒喝: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浮游,用洗耳来沽名钓誉,别让你洗耳的水污了牛犊的口。
两个隐居者的对话,巢父明显占了上风。许由的醍醐灌顶,记载在皇甫谧的《高士传》中: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也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巢父和许由同为隐士,面对巢父的嘲讽和牵犊上流饮之的行为艺术,许由并无辩驳。在一个比自己的隐行更加彻底的人面前,许由的心服当是一个隐士的必然。
所有的文献,均隐去了许由巢父隐居的过程,他们的出世,仅仅是为了拒绝唐尧的禅让。后世的疑惑在于,唐尧的禅让,出于公心,出于天下治理的善良愿望。而且,禅让是一种谦和的继承方式,它与武力、威逼毫无关联,在符合社会伦理的正常交接面前,隐居,反倒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选择。
拒绝禅让,最为极端的例子,当数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是舜的朋友,他亲眼见证了舜的禅让先后在支伯、善卷、石户之农面前碰壁。支伯用我有病,需要治疗,哪里有闲工夫治理天下的理由做了拒绝;善卷则用我立身于宇宙之中,冬天披兽皮,夏天换上葛麻单衣,春天种地,秋天收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自在,我要天下何用来推托;而石户之农,更是用你当天子累弯了腰,从来没有空闲休息,这样的苦差事,竟然加之于我做了嘲讽。北人无择看到了支伯、善卷、石户之农用逃入深山老林和携妻子儿女入海终身不返的决绝姿态,只是他没有想到,痴心不死的舜,又将禅让的目标,对准了他。
在舜的禅让挫折中,北人无择地拒绝,超越了舜的想象,超越了纸上的记载。北人无择地破口大骂,是一个人临死之前的绝望。“你在历山种地自由自在,却要接受尧的禅让。当天子是你心甘情愿的耻辱,也就罢了,又想把这种耻辱加到我的头上,我以见到你感到羞耻。”话刚说完,北人无择纵身一跃,让深不见底的清渊做了人生的句号。
用死亡做禅让的拒绝,北人无择将隐士行为做到了极致。
二
“行若夷齐”这个成语的出现,将隐士的身份和态度推到了遗民的境界。伯夷和叔齐,用“耻食周粟”的行为,为古代汉语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典故。
太史公用《史记》的列传之首,将伯夷、叔齐列为天下第一高洁之士。数千年之后,人们依稀可以循着太史公的目光,抵达遥远的孤竹国,在那里找到伯夷、叔齐兄弟。
在伯夷、叔齐的叙事中,后人都忘记了昆仲之间的另外一个次子。那个未在太史公笔下留下名字的兄弟,是历史的次要角色,是一个被动的王位继承者。
孤竹国君生前,欲立三子叔齐,但是,父死之后,叔齐却不愿继位,他以长子继位的传统为理由,要让与长兄伯夷。而伯夷则以不违父命的理由拒绝。兄弟两人,拒不退让的坚定,导致了他们双双出走。迫不得已之下,“国人立其中子”。
伯夷、叔齐投奔善养老的西伯昌,在周的都城岐下见到了刚刚继位的周武王将父亲周文王的木制灵位置于战车之上,准备东进讨伐纣王的一幕。伯夷、叔齐认为父死不葬,非孝,以臣弑君,非仁,于是勒马劝谏。伯夷、叔齐的劝谏和指责,并没有阻挡武王的步伐和胜利。周武王以成功者的名义建立周朝荣登大朔之后,愤怒的伯夷、叔齐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为生。
伯夷、叔齐以山野里的薇代替周粟,只是为了延续生命,他们推位让国的行为,本质上是坚守仁、孝的价值观,不事二朝。“耻食周粟”这个成语,开创了以遗民身份隐居的先河。当价值观重于生命的时候,隐居深山,采薇而食,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日常行为的主动选择和精神标杆。
伯夷、叔齐的首阳山,是“义无反顾”这个成语的起源地和墓地。兄弟俩用悲壮的歌声,记录了他们不与周朝合作的决心: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词中的绝命意味,其实是伯夷、叔齐命运的最终走向。他们预测到了死亡,却没有看到他们唯一食物的本质:薇的属性。
鲁迅先生用虚构的小说《采薇》为首阳山里的伯夷、叔齐开列了一个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这些用薇菜组成的果腹之物,用一个美丽的“薇”字蒙蔽了后人的双眼,让我们产生了美食的幻觉。这些野生的草类,其实是两个拒绝事二姓的前朝遗民维持生命的唯一食物,我能够想象得到那些远离了油盐的野菜的苦涩、粗糙和难以下咽。
伯夷、叔齐的饿毙,源于旁人的恶意提醒。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录了这个悲剧,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历史没有记下这个无意中致伯夷、叔齐死命的妇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匿名的妇人显然不是大字不识的山野村姑,她目光炯炯,看到了草木背后的政治属性。拾人牙慧的后人,将妇人的观点做了延伸:“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鲁迅先生,将伯夷、叔齐的绝命歌声,翻译成了现代汉语言的白话: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行若夷齐”这个成语,将尧舜时代的隐居,推到了一个最难的境界。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世界之后,天地山水乃至人类呼吸的空气,都已经彻底改姓易帜,从这个意义上说,“耻食周粟”式的隐居,已经无法进行,只有停止呼吸,才是隐居的唯一选择。
我对伯夷、叔齐的兴趣,源于“耻食周粟”这个典故,但真正使我深入探究“行若夷齐”“推位让国”背后的精神内涵,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居,那些事迹超越了伯夷、叔齐的隐士,更值得后人讴歌赞颂。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詹谷丰的散文《寻隐者不遇》)

詹谷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书生的骨头》《骨头的姿势》《一幢祠堂的重量》。曾获《作品》小说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山东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等多个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及长篇人物传记十部。
来源:《芙蓉》
作者:詹谷丰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