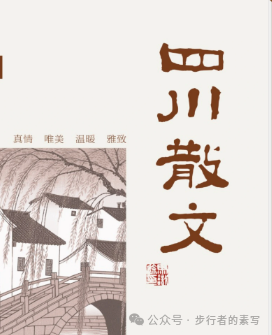
我是极度不愿打开话匣子的人,因为一不小心,说了心里的秘密,或者说出了别人的秘密,都是会让人难堪的糗事。
仲夏,一个人去生产队瓜地里偷西瓜,夜黑得让人提心吊胆,钻进瓜地旁边的玉米地。鸦雀无声的四野,一路连滚带爬地靠近瓜垄,明知道看瓜的人不在,还是叽里咕噜摸上一个大的瓜抬腿就跑。在路边砸开瓜皮,结果是个生瓜蛋子;初秋时节去果园爬上高大的李子树,把还没有熟的李子塞满口袋,然后被果园的狼狗撵到树上不敢下来。直到看果园的老刘头喊走了狗,才心怀忐忑地溜下来。然后一边跑,还一边骂该死的“刘瓜蛋子”不早点出来。脸红心跳中从未想过这种行为是偷窃,在小伙伴中洋洋得意地把污点变成炫耀的人生谈资。明明自己是个瓜娃子,硬要装成老熟的成功者,或许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失败。
“刘瓜蛋子”是因为他一直都是光头,头发长了,也不用去理发店,就跑到我姥爷家,姥爷一个刮刀就解决他满头的烦恼丝,几下子就干净利落了。不像我们小时候理发,妈妈用剪子剪几下子,短了就行。老刘头的详细名字,我是真不知道,估计整个村子里也很少有人知道。小时候没问过,长大了他就已经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刘头,是他要去镇里的敬老院了。老刘头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属于孤寡老人。生产队为了减轻负担,也是希望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去敬老院养老。他拄着一个木棒子,蓝布衣裤,身上背着一个帆布包。看到我的时候,习惯性想从包里拿点好东西,可是翻了半天,摇摇头。他经常来我姥爷家,按照辈分,我要喊他一声爷。或许这一声尊称,让他喜欢上了我这个淘小子。每次都会给我带点好吃的瓜果。我也愿意围着他,听他和姥爷天南海北的讲故事。常来姥爷家的还有生产队东羊圈的羊倌博老五,这也是个孤寡老人,我知道他们凑到一起并不是光聊天,而且还是要一起耍钱。耍钱的人,从来没有把钱当成钱,而是当成了命。他们要赌别人的身家性命。而最后赌掉了自己的身家,这是所有赌徒身上唯一的特质。
我的姥爷是个“蒙古大夫”,他可不是蒙古族。姥爷一生嗜赌如命,推牌九、赌骰子、打麻将、看纸牌,在我眼里只要是赌的东西,就没有他不会的。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姥爷成了医生大夫,而且家里的医书、器具是整套的。我有时候没书看,就跑到姥爷家,翻他的药书,也看不懂。只听妈妈说,姥爷治妇科很灵。被他救治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他常年在外行医,背一个褡裢,腰上缠着一个绳镖。医者仁心,而在我的姥爷身上,体现的却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听姥姥说,他赌输了会经常骂人。不过我知道,他没有动手打过人。他对我的舅舅和姨妈都很好。而且在我的记忆里,姥爷从未因为我们经常跑来他家玩耍,气恼过。甚至打扰了他的午觉,姥爷也从未生过气。至于姥爷会不会武术,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这个老头拽得很。他很多年都在研读奇门八卦,麻衣神相。他给我们姐弟四个都相过面,算过卦。他说我八方进财,注定半生颠簸,中年安居,基本无差错。有这么神奇的姥爷,你们估计都会羡慕我。可是我真不羡慕我的姥爷,一辈子的好日子,都给了风餐露宿,或许也正是暗示着我,要把他没走完的路,再走下去。看人这种技术活,很多人都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经常会在某些活动中看到有人手摇蒲扇,迈着方步。一脸虔诚地凑近美女身边,一会说看手相,一会端详面相,如果他会摸骨,估计早就上下其手地测量人家的身躯。
直到姥爷去世,我也没想明白,这些东西哪里来的。线装的医书,一本一本地撕碎,就在坟头烧了。一捆银针也都丢到了火里。我悄悄从祭奠的现场捡回来的银针,也的确是银的。我妈说,死人的东西不能留,结果姥爷的医术,就没有传下来,银针也被再次去上坟的舅舅拿去烧了。舅舅们学不会医书更不会医术,也就什么都没有留下。姥爷姓曲,当然我妈妈也姓曲,以至于我差点把著名诗人曲近老师,认成了娘亲人。因为这个姓氏太少了。“外甥是姥家的狗,吃完就走”,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把好吃的东西送给姥姥,因为分享是我们的幸福。史籍《姓纂》中记载:“大庭氏居曲阜,后有阜氏,曲阜氏。”细想起来近代曲姓的名人并不多,恍惚只记得曲波,也是因为《林海雪原》这部长篇小说。
提到我妈,就不能不说我的姥姥,我姥姥姓桑,这又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史籍《姓氏考略》记载:“神农娶承桑氏,亦作桑水氏,其后有桑姓。”“《姓氏》及《万姓统谱》记载:出自少昊的穷桑氏,子孙以桑为姓”在我的记忆里,姥姥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能的巧匠。姥姥是个小脚,她说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裹脚,受了很多的罪。所以我大姨和我妈就很幸福。没有遭上裹脚的疼痛。姥姥一辈子,精于布艺。在她的指尖,花鸟鱼虫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绣花枕头、被褥、桌布、窗帘,四季鞋袜,有布的地方就会出现姥姥的手艺。姥姥惦念着她的每一个晚辈,在我女儿出生前,姥姥就已经给准备了绣花枕头,虎头鞋和虎头帽。并不是因为我属虎,而是老令,新生的孩子穿虎头鞋,带虎头帽震祟辟邪。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到姥姥家吃饭,姥姥做的每样食品,我都想法让妈妈学会了,姥姥烙的饼,金黄酥脆;姥姥蒸的馒头,松软又鲜又香。姥姥的慈爱,是无法记录的一本账,直到她在生辰当天老去,都让我这个被姥爷说成狗的外孙,念念不忘。我经常从姥姥的烟叵罗中,拿出她的烟袋锅和烟丝,长长的烟杆和金黄的烟袋锅,因为小胳膊短点起来很费劲,因为怕没点着,猛吸一口,被烟呛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以这样的代价,成为我人生中抽的第一口烟。
那一阵的咳嗽声,从脑海里引出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他是我的爷爷,是我生命中最爱的老头之一。他姓王,我也姓王。至于是琅琊王,还是晋王,我是说不清楚。因为家谱在破四旧的时候被烧毁了。后面的祖辈们,只能说出来老家是从山东搬过来的,而且言之凿凿是大槐树下迁移出来的人家。爷爷排行第十,我最小的爷爷排行十几,我是没问清楚过,不过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姑奶。我从小就喜欢爷爷,却很少靠近他。他有气管炎,话说了就会喘不上来气。不过这个毛病没有遗传给我们,却传到我姑姑的大儿子,我大表哥身上。在爷爷昏黄的脸上,我看到岁月的波澜和他唯唯诺诺老实本分的影子,却看不到他为了延续生命,小心翼翼地带着小儿子,半夜逃离老家,一路闯入大兴安岭的坚强和勇敢。爷爷是个木匠,在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已经干不动太重的活计。生产队的木匠肯定是香饽饽,除了公家的任务,谁家都会有盖房子,修门窗,修理个镐把,叉子把,锹把,打个桌子,做两个板凳。木匠是个手艺人,靠手艺吃饭。当年能够落户,也是因为爷爷的手艺。
后来从父亲的口中得知,爷俩逃荒的原因,竟然是家人的迫害。一个同宗的叔辈,为了显示自己的积极和有原则,在夜里偷了公家木材,扛到了我家屋后。父亲发现后,告诉了爷爷,爷爷考量半晌,连夜带着父亲逃离了老家,让我对老家的牵挂,瞬间降到了谷底。我没有见过奶奶,她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是难产,甚至可能是因为生下了我的叔叔,导致大出血去世的。因为父亲当时正在上学。所以他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而在若干年的黑龙江的邮局,竟然遇到同名同姓,同月同日同出生地的人。而且陪同的人竟然是当年爷爷的邻居。导致父亲的晚年,经常念念不忘地让我们给他找兄弟。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我是非常相信是真的,也通过朋友多方面核对注册信息。尽管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门亲戚在这个世间。即便我几次回去,看望过亲人,但是对那个叫台安的地方,兴趣全无。
台安在辽宁鞍山市的辖区,张作霖和张学良是我的老乡。当代作家晨哥是我的乡亲,当年我在鞍山文联和他有过短暂的交流。我也知道他已经回台安去了,或许回去才能让他继续书写他的《神曲》,也是他距离《人民文学》奖最近的一次。说到鞍山,就不能不提我的打工经历,在鞍山阳光酒店学徒,我丢了老姑父一台自行车。那时候也没啥钱,我也没有意识赔付,都是母亲在事后做得弥补。以至于老姑,心里可能都埋怨我不懂事,那时候他们还在谈恋爱。不过我的八姨奶和八姨爷两位老人对我是真得好,只有在叔叔姑姑他们身上,我才能感受到血脉的亲近。人这一辈子,穷富都是会有亲情的眷顾。当然,鞍山还有刘兰芳的评书,陈晓旭的林黛玉,还有鞍钢的高炉,都曾经点燃我的文字和梦想。
直到我结婚以后,和爱人一起专门去了趟千山,那个木鱼石传说的地方。我没见过奶奶,只是从父亲的口中听来的一支半语。奶奶姓马,《姓谱》一书中记载说,“马”姓的发源地是扶风。马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汉族马姓最初发祥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河北省邯郸市一带。奶奶排行老五。也就是说我有八个姨奶,还有七个舅爷。近年,八姨奶和八姨爷都去世了。每次想起他们,我都忍不住的心痛,奶奶去世早,好在有生之年,我在台安见到了六姨奶、和小姑,从小在黑龙江讷河九姨奶身边长大,至今我和小老叔的关系依然很好。亲戚多了,能记住辈分和远近,也算是我心安之处。
鞍山是我人生中真正离开家乡的第一站,天津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驿站。从接触诗人罗广才开始,我在天津才算正式有了一个写诗的朋友。那时候他在广告公司,我在艺术团上班。因为离得近,通过网络结识以后,就成了我在天津的狐朋狗友,隔三差五就在一起胡吃海塞。广才确实有才气,也有狗的脾气。嬉笑怒骂间,我们就成了最亲近的人。我时常去他的家,看望老娘和峤峤,峤峤还在上小学。我们经常会因为剩下的一瓶啤酒,抢着喝,当然我也抢不过他。他会耍赖,他会说最后一瓶酒归他。我想这没有影响我把他当个兄弟。有一次我在外面出差,他迫不及待地在电话里给我朗诵一首诗,我听着很半天才缓过气来。弱弱地说了一句还不错。这就是他后来传播很广泛的《给父亲烧纸》。我们经常一同拜会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和国学家沙驼。沙驼是个玩家,写诗、写字,而且还喜爱收藏。为一张邮票,当年被打碎了满口的牙齿。沙驼离休后受著名诗人鲁藜之邀,担任天津昆仑诗社顾问兼任《昆仑诗选》和《昆仑诗丛》两刊主编,从1989至1999年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他自掏腰包,独自一人共编辑出版六十期《昆仑诗选》。在他阳光、幽默的生活态度感召下,让我们更加热爱诗歌,也催生后来的《华语诗人》《天津诗人》。沙驼老说话的风趣幽默,为我今后的人生擦了多少亮色,他欢快的语言和对书法的苛刻,都让人在敬仰中渐渐懂得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道理。听说我结婚了,沙驼兴奋地给写了一幅“琴瑟相和”,还信誓旦旦对他的保姆说最后一幅。原来老爷子的字很管钱。我们都笑呵呵的,估计保姆心里挺难受。
说到华语诗人,就不能不能不说著名诗人牛汉。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牛汉,诗人王竞成与牛汉老人很熟悉。我想做刊物,就想委托他找一位老人家给题写刊名。我们约好了在北京鲁院碰头,我和江帆从天津出发,到了鲁院先看望诗人宋晓杰,然后汇合诗人杨拓,一起去牛汉老人家。不巧的牛汉老师刚刚摔了跤,断了肋骨,一直在静养。牛汉先生坐在椅子上,也依然显得那么高大。消瘦面颊上,被岁月的风刀铭刻下了沧桑。先我们而到的诗人李木马、李小洛一行看我们人太多,她们就离去了。我听着他们叙旧,也不好提写刊名的事。刚好有人带来了牛汉老师的集子,请老先生务必签个名,宋晓杰也趁机提出了我要写刊名的事,老爷子一口答应,并同意担任顾问。也是了却了我专门跑一趟的心愿。后来晓杰姐把这段经历写进了《鲁院日记》,今天在辽宁文学网还能查到。
说到题写刊名,就要提到诗坛很著名的另外一个老人家阿红。我是通过《情诗》主编见闻,拿到了阿红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在我出差沈阳的时候,去拜访老人。阿红本名王占彪,是我的本家,也是鸭绿江文学院的创始人,《当代诗歌》的创始人。我见过的第一本文学函授教材就是鸭绿江文学院的。我的文友胡连海,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在阿红家里,老人给我讲了很多文坛往事,让我更惊讶的是老人思路非常清晰,他听说我办民刊,就提议让我编辑中国诗书画报,他来担顾问,并且负责帮我走上正轨。可惜那时候,我真对书画一窍不通。老爷子也把我当成忘年交,每次都会送我大量写好的字。长时间的对话交流,我慢慢了解了老人传奇的一生。因此也写下了我人生第一个非正式对话作品《常青藤》,发表在《北方文学》2015年11期。被著名诗人艾青称赞“阿红,诗歌的舵手”
诗歌改变了我的人生,也获得了爱情和家庭。
落户成都以后,经常和著名诗人孙贻荪老师在一起喝茶。孙贻荪是老兵,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崛起的诗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参加过成渝铁路建设的老革命,老铁路。也是因为他的推荐,我才有机会来到现在工作单位《星星》诗刊杂志社,从诗人转变成诗歌编辑。
“修成渝铁路有多苦?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剿匪一边筑路。”“修路缺木材,很多老人将自己的寿材都捐了。”……说起建设成渝铁路的故事,孙贻荪仿佛回到了多年前,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时候的人心多齐,为了幸福的生活,不仅捐献财务,甚至捐献了生命。每一块枕木下都有当年的解放军兵流下的血汗。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举行了通车典礼。孙贻荪被特批领到了“摄影记者证”。他拿着相机,在主席台上拍下了这一幕幕历史的画面。然后会后,一纸调令,孙贻荪直接被派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直到战争结束,他作为战地记者,书写了大量血与火的篇章。直到战争结束,他回到了四川由一名战士,脱去军装,成为铁路战线的一份子。
某一年《星星》诗刊在原始森林举行笔会,主办方特请流沙河先生赐字。流沙河先生走上主席台挥毫。搁下笔后,招手喊孙贻荪先生:“老孙,我送你几个字”。流沙河先生一挥而就:荪香草也。举着墨迹未干的字对孙贻荪说,这是我对你诗的评价。孙贻荪从自贡工务段退休以后,客居成都。如今九十多岁高龄,却依然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孙老一辈子写诗,退休后原单位中铁二局、中铁八局,写了大量的纪实文学,最近还成了大型电视连续剧《一路向前》的文学顾问。2021年获中宣部表彰,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我很早就路过延安,后来机缘巧合两次去延安学习开会。在延安鲁艺的宣传栏上,我们看到了刘新民的名字,他就是我们星星的创始人之一白航。来到《星星》诗刊以后,我陆续见到了张新泉、杨牧、刘滨、鄢家发,孙建军、杨青这些原单位转退的老人,也送走了白航、流沙河,蓝疆这些退休多年的老前辈。见证了梁平、靳晓静、萧融的退休,也见证了干海兵、熊焱、王琳、马琳、杨献平的转岗。更见证了敬丹樱、任皓、童剑、黄慧孜、罗倩的入职。同时见证了星二代们出生,成长、高考,走进婚姻的殿堂。星星还是那颗星星,而站在星光下的人,依然坚守着朝着星星的箭头。
为了不说话,我基本戒掉频繁的酒局,小心翼翼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最后活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作为星星的一份子,我们见证了白航老师的九十岁寿宴,本来今年还打算在石天河老师的百岁寿宴上,好好为老人家做一场诗歌朗诵会。可惜老人未能等到星星诗文库的出版,也没能让星星的晚辈见证星星人的最高寿。人总是要怀旧,只有旧的才能在心海里泛起波浪,甚至泛起足够荒唐手足无措的梦游之事。偶尔还能遇见张新泉老师,他对后辈的关爱,甚至有些偏爱,他会给晚辈们点赞,也会指出我们在编校过程中的缺憾。偶遇到刘滨老师,他洪亮的声音,总会我精神一震。杨牧先生也总脸含微笑,孙建军老师也时常问我一些星星的发展情况。每一个曾经在星星工作的人,都把星星当成了自己的老家。家有一老,真得是一宝。
和这些比我老的人在一起,能聆听他们的人生智慧。对于我,从初出茅庐,到颠簸流离半生来说是最好的财富。如果说人生是一团麻,他们告诉我的就是怎么清理和理顺自己的人生态度。活着,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四川散文》2024年)
来源:“步行者的素写”微信公众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