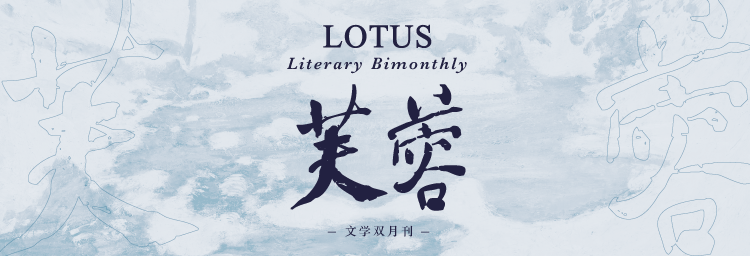

竹鸡殇
文/张雄文
油菜花在屋前稻田铺开金黄,与四野无边苍碧相映,勾出一幅重彩水墨画时,村子静美得常令我沉入痴呆,像古小说中被倩女勾去魂魄的男子。蓦地,“滴水,快——”“滴水,快——”屋后大株山一串鸟音骤起,一连就是数十声,急促、尖厉、悦耳,节奏铿锵鲜明外,最后一个音节还格外加重,发着拉长的颤音。这鸟音,将村子辽阔的安谧瞬间击碎,也将我从痴呆中唤醒,却又迅速沦陷另一种沉醉里。
童年乡居的日子,我时常与这不同于鸡鸣雀噪的鸟音猝然而遇,感觉与村子一样孤寂的心被这声音缓缓融化,犹如跌落舌尖的棉花糖。
家乡湖南冷水江一带方言称竹子为“丢子”,这种常在竹林、山地、灌木和草丛出没,学名“竹鸡”的鸟,便被村里人唤为“丢鸡”。它们的叫声,有时也被孩童们学舌为“丢鸡,快——”“丢鸡,快——”。
早先,我觉得“丢鸡快”的拟声颇神似。遥望大株山苍翠深处,我常默然想,它们或许是在急急呼唤同伴动作快点吧?后来渐渐懂事,又接触了些书本知识,才知“滴水快”的拟声更合理,也更有内涵。竹鸡叫唤后,一般都会下雨,即“滴水”。北宋文学家张舜民的《打麦》诗写道:“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竹鸡一叫,乌云沉沉卷积,大雨将至,说的即是竹鸡这一特点。与张舜民同时代诗人梅尧臣的《竹鸡》诗云:“泥滑滑,苦竹冈。雨潇潇,马上郎。马蹄凌兢雨又急。此鸟为君应断肠。”“泥滑滑”是竹鸡的又一俗称,也是因模拟叫声而得名,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竹鸡,南人呼为泥滑滑,因其声也。”待在“苦竹冈”的此鸟一催促,天空便“雨潇潇”“雨又急”,说的也是“滴水”。另一位宋人刘宰则在其《开禧纪事二首·其一》诗中说:“泥滑滑,仆姑姑,唤晴唤雨无时无。”描摹的还是竹鸡在声声呼唤下雨。儿时的我对竹鸡叫唤后是否有雨兴趣不大,湘中山区春夏之际原本多雨,屋场、村道、田埂上总是湿漉漉、滑溜溜的,踮着脚尖小心翼翼走过,往往仍是一身泥水。这雨是否果真为竹鸡的神通所致,我也从未想过去考究,沉迷的是其鸣叫本身。
日子一长,我知道了竹鸡的叫声分公母,母者是“嘀、嘀”短声,低沉而单调,并不为我所喜,公者才是令我愉悦的“滴水快”。接连数十声的“滴水快”也并不雷同,先是急促响亮,像缯帛撕裂于旷野;而后渐渐低沉,每声的时间也逐渐拉长,仿佛音质雄浑、雍容沉着的歌手;到最后,竹鸡如乐队指挥家手势有力地收尾,鸣声戛然而止,绝无拖沓,唯有空山与村庄四野似乎依旧飘荡着悠远的回响。
我迷恋竹鸡的鸣声,却从未见过它们的真容,哪怕掠过眼前的身影也没有。山野茫茫,草木浓碧,它们“只在此山中,草深不知处”。好几回,我独自上山,悄然穿行林木间,拨开荆棘灌木,循声而觅,竹鸡的鸣叫总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骤然中止,像断弦的琴瑟。一次,在后山坡麦地里,我拨开浓密的麦秆,专注扯着猪草。这是村里小伙伴们未曾想到的一大片自留地,隐伏着绿茸茸鲜嫩嫩的鹅肠草等。我正为很快就能扯满一篮,完成母亲给我今天的任务而兴奋时,两米开外的麦地突然哗啦作响,随即一只大鸟扑棱棱而起,在麦子上方画一道弧线,又降落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再无踪迹与声响。它的出现倏忽,令我几乎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而消失与沉寂也格外迅疾,似乎刚才一切只是虚幻的梦境。但咫尺之间,我真切看清了它的模样:比家里的鸡略小,一身五彩炫目的羽毛,艳如彩霞,拖着长长的尾巴,边飞边“咯咯咯”地叫。这是我与身形硕大的野禽近距离接触不多的几次之一,有着莫大的欣喜与遗憾。不过,它的身影与叫声,让我马上断定它不是竹鸡,而是野鸡。
野鸡我曾远远见过。那时尚未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说法,乡间日子又多半清苦,便有了打鸟人。我家背靠大山,常有农家汉子扛了鸟铳从门前过身,铳杆上倒挂着三两只鸟雀。一次,我正在屋场上自个儿玩“四角板”,蓦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一只大鸟从屋后林木间慌里慌张蹿出,钻入屋场下水沟里的草丛,奔跑、挣扎一阵,没了声响。须臾,一个陌生汉子提着鸟铳气喘吁吁跑了过来,问我看见野鸡没有。我才知刚才并未看清的大鸟是平常难得一见的野鸡,心里颇不悦,便摇着头。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枪法的自信,汉子并未当真,而是四处看了看,又顺坡爬到屋场下,细细搜寻起来。不久,他在辣蓼草深处捡了野鸡,不满地回望我一眼,扬长而去。我撒了谎,连细看一番野鸡的机会都没了,只远远见到挂在铳杆上的野鸡沉甸甸的,尾巴老长,几乎挨着了地面,像我沉甸甸的心。
为了一睹竹鸡真容,我专程上了一趟二十里外的城里,用积攒许久的零花钱买了个望远镜。回来后顾不上歇口气,兴冲冲跑到屋后山里,趴在“滴水快”时常鸣奏的草丛,等待竹鸡现身。约莫半个钟头后,左边山坡响起了令人陶醉的“滴水快”,我急忙举起望远镜观看。但镜头中除了蓊郁的松树、灌木与草丛,一根竹鸡毛也未见到。只有“滴水快”一声紧接一声,像琴弦上急促滑落的音符,似乎有意向我挑衅。正怅然间,镜头里出现了一只老鹰,急速滑翔而下。“滴水快”的鸣唱也瞬间中断,一只比老鹰小的灰褐色禽鸟从灌木丛猛然蹿出,拼命起跳扑腾,试图逃出魔掌。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老鹰又一个稳准狠的俯冲,利爪一把扣住了禽鸟,犀利鹰嘴顺势朝它的喉咙一咬。禽鸟一声惨叫,再没了声息。随后,老鹰单爪提着猎物,翅膀翩然一展,飞往了镜头外的某个山头。我知道,一场兴奋的饕餮大餐即将开始。
此刻,四周陷入死寂,再没有往昔鸟雀欢快地鸣唱,更没有其他“滴水快”声音的应和。除了志得意满的老鹰,山间一切似乎都沉浸在被屠杀的惊恐与哀伤里,其中也包括心情沉重的我。我的望远镜倍数不高,事发突然,距离又有些远,并没有看清楚惨遭毒手的禽鸟,无法确认它是否为竹鸡,但我想它一定就是竹鸡。
此前,我在课外书中读过一则关于竹鸡被老鹰屠戮的寓言故事。野兔和竹鸡一同生活在某个山头,平时互相瞧不上。某天,一只猎狗闯进山林,发现了野兔,兴奋撒腿追逐起来。野兔急急窜逃,躲伏在了丛林深处。猎狗不依不饶,从野兔身上散发的独特气味找到了线索,一步步逼过来。危难之际,立在不远处灌木顶端的竹鸡却幸灾乐祸,嘲讽野兔:“你总夸你是飞毛腿,但从现在的形势看,你的腿连竹竿都不如。”竹鸡嘲笑野兔时,全然不知噩运正从天而降——一只老鹰锐利的鹰眼早盯上了它,一个俯冲,将它掠去做了点心。我不喜欢这则寓言,不知作者何故抹黑精灵般的竹鸡。竹鸡一定不会这般猥琐和愚蠢,而是相反,否则鸣唱不会如此悦耳。但我从中知晓了竹鸡并非总是想象中的自在与惬意,身边布满了危险。这次就惊心动魄目睹了一回。
此后,我始终未能真切一睹竹鸡芳颜,只能长久沉迷在它独具魅力的歌喉里。某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在镇上供销社看到一幅售卖的年画——徐悲鸿的《竹鸡图》,央求父亲买了回来。《竹鸡图》与竹鸡无关,一片竹林下立着一只傲然的雄鸡而已。画面构图简约,重点刻画鸡冠与尾巴,冠红如火,尾黑似漆,在粗与细、红与黑的对比中呈现一种平安和谐的气氛。父亲很满意,说我到底读了几年书,眼光不错,“鸡”谐音“吉”,寄寓“吉祥如意”,“竹”则谐音“祝”,寄寓“长青平安”,二者结合,便是表达过年“祝福平安大吉”的美好愿望。我后来才知,徐悲鸿构画前确有此意,说:“竹用以象征正直,鸡能报晓,所谓‘雄鸡一声天下白’。合起来在中国老套说做‘竹报平安’。”其实,我执意买年画,并未想这么深奥,只是觉得“竹”与“鸡”的构图,能抚慰未曾见过竹鸡的我而已。如果《竹鸡图》有吉祥之意,那竹鸡也必定如此,我为父亲的诠释开心了许久。这幅年画也和竹鸡“滴水快”的鸣唱一道,藏在我心底许多年。
16岁以后,我上高中,念大学,参加工作,都在城里,离老家愈来愈远,后来还长饮湘江水,定居湘东一座城市。母亲和弟妹们也跟着在煤矿上班的父亲农转非,迁居靠城的矿山,老家房子几近废弃,我便再也不曾听过竹鸡的鸣叫。但它的鸣声,像一首儿时读过的诗章,偶尔会从记忆深处被悠悠勾出,依旧清新悦耳,令我久久咀嚼,回味不已。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张雄文的散文《竹鸡殇》)

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湖南散文学会副会长,株洲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出版《名将粟裕珍闻录》《潮卷南海》《燕啄红土地》等书四百余万字。曾获冰心散文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四川散文奖、第六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第三届湘江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张雄文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