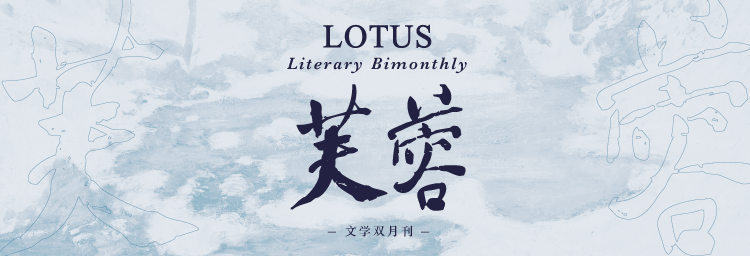

画蛇记
文/胡竹峰
故乡的物事,隔得再远,精神上却觉得亲近。偶尔也有例外,譬如蛇,总是来得疏阔,不经意想起也会迅速丢弃一旁,不让它盘踞心头太久。万物皆有性灵,《淮南子》有灵蛇之珠故事,春秋时,随国君主随侯出游途中,见一蛇受伤,断为两截,用药物为其接续。蛇痊愈后,游入江中,衔来明珠,送给随侯。蒲松龄的蛇人故事读得熟,弄蛇者与两条青蛇之间超然物种的情谊,只敢在纸页向往,没有现实的亲随。
老家村野有蛇,银环蛇、眼镜蛇、蟒蛇、蝮蛇、菜花蛇。还有一种叫竹叶青的毒蛇,颜色碧绿,颇具攻击性。河潭或稻田常有泥蛇,风一般游过,悄无声息。春四月插秧时常常遇见它,胆小的避开,胆大的径自直取七寸,抓起来遥遥掷向远方。还有一种叫尖吻蝮的蛇,乡民称五步龙,又叫它七步倒、百步倒,被其咬到,五步或七步最多百步即倒地毙命。据说过去进深山,人总要随身带一刀,倘或被尖吻蝮咬到,咬指断指,咬肉剜肉,绝不容缓。让人想起壮士断腕的决然与勇气。
某老居士告诉我,有一回听法师讲经,一青色花斑大蛇也伏在大殿前门侧,形状细长。众人失色却步,上人莞尔一笑,说这条蛇是来亲近三宝听法。蛇果然从前门爬行到殿内,未曾惊怖旁人。从大殿左侧爬至右侧,绕佛像一圈状,然后伏在法座前聆听说法。这是蛇的向善,万物有灵有善,众生皆存佛性。
蛇身形柔软,在地上爬行时仿佛游走一般,悄无声息。它大概是阴气很重的东西,村野乡居时,无数次在山里遇见,兜头迎面感觉一股冷风,盛夏酷热亦然。蛇身更阴冷,着手软凉,不敢久触。蛇好在坟陵出没,老人说那是先人之灵,大吉之相。乡下葬俗发现搁厝棺木周围有蛇,认为美穴,是活龙地。
每到秋天,山上平坦的地方,常常看到蛇皮,有些碎成块,风吹着四散,有些却整节空心,鳞片毕肖。撞见过蛇蜕皮,紧紧附在木头、树根或石头上扩张颈部,用尽气力,忍痛将旧皮一点点从头至尾蜕去,其状甚苦。老家说人吃苦事,好比喻脱了层皮以示艰辛。
蛇平日在洞中、穴里、树上安眠,夜间开始活动,游走觅食不休。乡下人夏天走夜路,常常手执竹木,清扫路边草丛,免得被蛇咬了,是谓打草惊蛇。
八岁那年被短尾蝮咬过一次,脚肿到腿跟,一个月不能走路。乡下无蛇药,以蜈蚣浸菜籽油涂抹患处方才祛毒。短尾蝮,头略呈三角形,有颊窝,头背有对称的大鳞,褐色或灰色,杂有黑斑,其状极懒疲,昼伏夜出,老家叫土巴蛇、土公蛇。常常有农人被它咬伤,乡民见了总是痛下杀手,除之大快,然后厌弃地远远扔进夹垄。
古人雅称蛇升卿,《抱朴子》说,山中有种大蛇头戴冠帻,名字叫升卿,相遇时称其名字,大吉。纵疑心那是眼镜蛇,葛洪是读书人,所以才有头戴冠帻的比喻,乡民则称饭铲头。
据说蛇有神力,报复心强。朋友告诉我,当年他们一伙年轻人在海滩上玩,有同伴打死两条大蛇。回家路上发现有蛇挡在小路上,惶恐中又打死了几条,结果更多的蛇在挡路,像乱草一样,一绺绺封住路径。
童年的时候,有蛇活吞过山脚人家的大狗。事后去看,只见稻田从中分开的一条蛇迹,一路向山林里,压坏的稻子歪在一旁。隔得远远地看那片稻田,依旧感觉森森阴气扑面而来。那条蛇是山蟒,后来又出现了几次,没有侵害人畜。好多年过去,踪迹全无,想必去了深山老林,家乡传说它修炼成龙,早已升天了。
在秋浦河边见过蟒,江南地气肥沃,蛇粗壮如老树,吐着芯子,懒洋洋横过马路。不多时入得丛林,但感觉草木纷纷避让有爆豆声又如大雨忽至。一车人骇然大惧,脸有土色,半日方才安下心来。
老家蛇极多,乌梢最为常见,体长者七尺有余,但生性温驯,从无伤人之心,即便被咬到亦无碍。常在农田、河沟附近,有时也在屋舍旁出没,行动迅速。小孩子初见略略觉得悚然,大人们常常捉来炖汤,说是治疗恶毒生疮。乡野湿气重,瘴气雾气伤人,旧年村民上山下河,腿脚易生疔疮。
有一年去蓬莱,海上有蛇岛,隔水眺望,哪敢上前。怕入了旧小说中的情景:走得几步,忽听草中簌簌有声,跟着眼前黄影闪动,七八条黄中间黑的毒蛇窜了出来……转身便走,只跨出一步,眼前又有七八条蛇挡路,全身血也似红,长舌吞吐,咝咝发声。这些蛇都是头作三角,显具剧毒……只见树上、草上、路上,东一条,西一条,全是毒蛇。
明万历中,刘元卿《贤奕编》观物篇,说有蛇名叫高听,常闯入巨蜂房中,尽收其毒。然后趴伏道路旁草丛,用蜂毒刺来人。刺完以后,尾随那人到他的住宅近处,爬到树顶上窃听。家中有哭声,知道人已经死了,悠然自得离开,否则心里窝火,重新集毒刺人。
传奇里蛇变化为人的故事颇多,白娘子与许仙行状差不多家喻户晓。人人爱那白娘子,人人羡慕许郎中,人人迁怒法海多事。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说,也有人变过蛇。沧州城一泼皮,为人凶横,做羞愧事,投河自尽了。因为生前侍母还算尽孝,冥间官员检阅档案,得受一个蛇身投为人间了。
长妈妈说给鲁迅听的蛇故事,祖父讲古也和我谈过,细节不同而已。从前一个读书人,夜里正习字读书,窗前有美人露齿一笑。他很高兴,让美人进屋了。几个月后,一道士见到读书人,说他眉目都是阴气,像被妖吸走了元神,恐怕性命不久。读书人慌忙跪到地上求救命,道士画出一道神符,让他贴在门口。当天夜里,美女来时,化为一条大蛇,道士恰逢赶到,挥刀下去断了蛇身,取下蛇胆自行吞服了。从此书生发愤用功,大考得中,外放为官了。
我并不喜欢那读书人,觉得他着了道士的计算,是个孱头,更为美女蛇遇人不淑、无故惨死抱不平。此后每到天黑,常常留意窗口,期盼会有一条蛇化作美女粲然一笑,可惜直到离开乡下也没能见到。后来倒是见过很多蛇,它们丝毫不标致,并非美女蛇,兴许是来不及穿戴人皮吧,还存了青面獠牙的头脸。
祖父讲古,大概脱胎于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许逊斩蛇故事。那年江东蛇祸,蛇粗大如树身,无人敢除。许逊啸命风雷,指呼神兵,以慑服之使不得动。然后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向蛇的脑门,几个弟子也引剑挥之而上。此后一方安宁。
柳宗元说永州之野有异蛇,通身黑质上有白色花纹,剧毒无比,草木碰到亦干枯而死;那蛇咬了人,没有解救的办法。世间并无草木触之尽死的蛇。柳宗元文章我向来喜爱,这一句故作惊人之语,却不以为然,士人作文通病如此。庄子寓言,说部传奇,神游八极尽享物化之美,读来飘飘欲仙。写碑写史还是要考究一些物理,不能太多矜张作态。
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究竟物理。隋以前两汉魏晋诸多文章下笔沉着,华实兼具,态度安详。此后,唐风鼓荡,文章也多了奔腾、多了躁进。几百年后,才有公安派、竟陵派、性灵派的革新,尽管又落入新的窠臼。作文难免窠臼,文章家当如狡兔,何止三窟,像跃入大海的游鱼,像飞进山林的雀鸟。下笔有世道人心,用意固然佳妙,然不能强文所难。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才是自然之性。先秦诸子与六朝人物,文章即为文章,或言志,或抒情,或说道,后人却多以此做手段,为进阶,为争宠,为稻粱,一个是天意一个是机心,机心再高,终不及天意万一。勉为文辞,越发局促,无益,也无趣,也无味也。不如在心里撒把文章的种子,等待发芽,任它自生自灭。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胡竹峰的散文《画蛇记》)

胡竹峰,1984年生,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雪下了一夜》《空杯集》《墨团花册》《中国文章》《茶饭引》《惜字亭下》《黑老虎集》《南游记》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茅盾新人奖、雪豹文学奖、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奎虚图书奖、刘勰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来源:《芙蓉》
作者:胡竹峰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