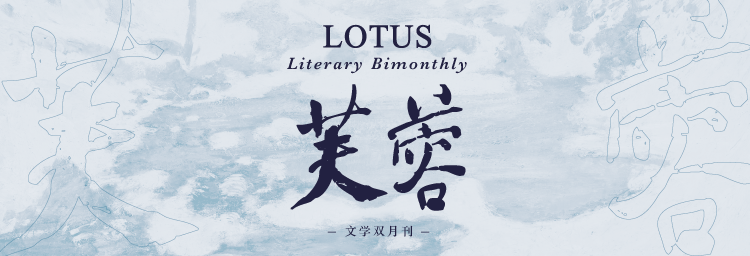

菩提树(中篇小说)
文/郭雪波
出生,就是为了歌唱。
荒野上的蝈蝈儿,一生如此。
涉过养畜牧河,上了南岸,坐在土坎儿上,哈尔姑一边回头看缓缓流淌的河水,一边揪一撮草揩净脚上的泥沙。心里说,入夏了河水真暖和,回来时洗个澡吧。
套上布袜子,用麻绳扎好裤脚,再穿上儿子弃穿的一双旧旅游鞋,哈尔姑就朝着河上游的嘎海山出发了。她要去那里,逮一只蝈蝈儿。
腰上别着一把镰刀,胳膊上挎着一个柳条筐,六十岁的老村妇哈尔姑尽管显得有些老态,但看上去还算硬朗、结实。黧黑的脸上皱纹如刀刻,如沙漠上刮过一道飓风留下的凿痕,眉毛依然浓黑,鼻梁刚挺,干裂的嘴唇紧抿着,显示出内心的坚定。
她的老伴儿巴斯虎正在院子里收拾鸡窝篱笆,一听她上嘎海山逮蝈蝈儿,嚷起来,疯啦?现在野外哪里还有蝈蝈儿?不想想自己都六十花甲了,还想逮蝈蝈儿玩儿,烧的吧?
没有烧,不是我。你看看吧!
哈尔姑把一张皱皱巴巴的黄字条递给老头子巴斯虎看。
上边只有一行扭扭歪歪的字:真想听到一声嘎海山的蝈蝈儿叫啊!
这是银沙湾赛车手巴图穿越塔敏查干荒漠深处,带回来给我的——是那个大哥。哈尔姑默默说。
巴斯虎一时愕然,无声。半晌后说,要不我陪你去吧!
不用,家里堆着干不完的活儿,你去嘎哈(干啥)?添乱!
哈尔姑回绝老头子,就这样独自出发去嘎海山,逮蝈蝈儿了。
嘎海山离这里有十公里,没有通路,要经过全是农田或者荒野之地,狼狐出没虫蛇盘咬,很不好走。这些倒是难不倒哈尔姑,一辈子生活在这一带什么没有经历过,只是担心嘎海山上现在还有蝈蝈儿吗?
走过一片盐碱滩的时候,有两个珠占村的人在那里种水稻,向他们询问时二人哈哈大笑,大脑袋摇得如拨浪鼓说,那物儿,早就没了,快二十年了吧!自打用了化肥农药以后,荒野上那物儿就绝种喽!
其中一人往池田里撒着化肥尿素,眼睛乜斜着,奇怪地盯视哈尔姑,问她,你打听蝈蝈儿干啥?想逮着玩儿?嘎嘎嘎——
不,不,随便问问,随便问问,我是要去采药材的,不是抓蝈蝈儿。哈尔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正是抓蝈蝈儿的,都六十岁了,玩儿小孩子把戏,说出来的确让人笑话,会令人觉得老不正经。
水田里的尿素味儿很冲,哈尔姑赶紧掩着鼻子离开那里,心想这种味道别说蝈蝈儿,人都会被熏过去。城里的人现在肯定都练成了金刚不坏身子骨,卖给他们吃着这样的化肥大米,他们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嘛嘛香。
哈尔姑扎紧腰带,手里握着镰刀,继续向前行。前边不远就进入嘎海山区域,那里荆棘丛生,野兽出没,需要当心。一片山洼地上,一溜儿摆放着几十个蜂箱,有一男一女放蜂人头上戴着白纱遮网斗笠帽,正在忙活。野外还是遇见这样的两口子养蜂人让人放心,不会让村民生疑。几年前有两个男性养蜂人诱拐走了珠占村一个漂亮丫头,两年后那丫头挺着大肚子蓬头垢面回来,据说两个养蜂人因诱拐良家妇女达七八个之多,被公安机关逮住判了刑。
即便是男女两口子,哈尔姑还是躲开他们走,更不敢招惹那些在头上飞来飞去的蜜蜂。那两口子也知趣,头也不抬地忙活着,根本不搭理过路人,因为也出现过不三不四的村里青年人骚扰袭击养蜂人,发生过一起命案。
终于走到嘎海山脚下了,一上午整整走了三四个小时,她气喘吁吁。
选一块凸出的小岩石坐下后,她抬头仰视嘎海山。
这山其实不高,也就海拔六七百米,有三座形状相同的山体相连,静静地矗立在养畜牧河南岸,像是三位沉默的老人,威严而肃穆。山上边没有树林和高大乔木,四处皆是突兀的青黑岩石,其间只生长着些稀疏的杂草,矮灌荆棘丛,零散开着一些小花,有蓝莹莹的鸽子花、淡紫色牵牛花,偶尔还可见红灯笼似的萨日朗花,装点着这座光秃秃的嘎海山。哈尔姑一边掂量着山,一边慢吞吞地把挂在裤脚和衣衫上的刺儿球一一摘干净,再把松开的裤脚麻绳重新扎紧了些,以防山上常有的小蛇钻进来。此时,她不禁回想起小时候跟随大哥爬这座嘎海山游玩的情形来。小时每到阴历五月五就高兴,那会儿尚不知这一天汉语叫端午节,他们只叫tabensarin-xinintaben,即五月五,这一天他们早起先到养畜牧河边洗脸庞,然后兜儿里揣着鸡蛋和炒米去爬嘎海山游玩,从山上采撷野艾蒿挂耳边,带回家来挂在门楣、窗棂驱邪避灾。那年五月五大哥小学六年级,她才入学一年,她便跟随大哥去爬嘎海山,没有从河南岸路上走而是一路沿着河道溯流而上,一路欢喜嬉戏,大哥还捡到一只失散的小鸭雏送给她玩,还用香蒿、艾草编了花环套在她的头上,笑呵呵说我的黑丫妹妹是天下最漂亮的女孩儿!
想到此,哈尔姑差点扑哧笑出声来,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歇够了,哈尔姑准备爬山,她竖耳谛听,搜索那宝贵的绿肚子蝈蝈儿叫声。四处寂静,万籁俱寂,头上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脚下是杂驳的土地、鼓凸的岩石,别说蝈蝈儿叫,连个鸟儿啼的声音都没有,荒凉的山野让她感到很孤寂,生出无端的恐惧来。记得就那次五月五来爬嘎海山时,天气已经很炎热,本来入六月夏季才出现的蝈蝈儿提前出现,满山的酸不溜草、沙巴嘎蒿,还有红柳条子上聒噪着无数的蝈蝈儿群,一片喧哗,悦耳动听,那简直像是听一场荒野交响曲。那时候山坡和山脚下,草木真是旺盛啊,不像现在,山野大自然真的是无可奈何地衰败了。
正当哈尔姑站在那里踌躇时,冷不丁,从山上一座大岩石后边闪出一个人来。她吓了一跳,一见是珠占村的护林员嘎达老光棍儿,肩膀头上挂着三四个空荡荡的铁夹子,手里拎着一只血呼哧啦的瞎眼地鼠子。
咦?这不是东村的哈尔姑大婶儿吗,这么大热天的,您老跑来爬嘎海山——嘎哈呀?
那个啥,家里的牛胃里有火,想逮几只马蛇子喂喂,败败火——
逮马蛇子,你得上村北的塔敏查干沙坨子呀,这硬邦邦光是石粒子的山上哪有马蛇子牙?不对!嘎达光棍儿奇怪地盯住老太太,询问道,不对吧老婶子,你有啥秘密瞒着我吧?难道你知道了嘎海山金猪洞的开启秘密啦?
金猪洞?开启秘密?啊哈哈!哈尔姑失声大笑起来。
傻小子呀,那只是个传说,古老的传说,哪儿跟哪儿啊?哈尔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嘎海之意为猪,自古传说嘎海山有个金猪洞。
说的也是,那只是个传说!可怜的嘎海山,现在除了啃树根、草根的瞎眼地鼠子,没有别的玩意儿喽!光棍儿嘎达转身走开,嘴里哼哼着,啊哈呦,我是光荣的人民护林员,保卫祖国北疆生态屏障——
光荣的护林员嘎达光棍儿,豪迈地唱着歌儿下山去了,肩头的铁夹子叮当碰响,手拎的地鼠子滴着淋淋鲜血。
大侄子,问下哈,哈尔姑迟疑了一下,怯怯地从嘎达光棍儿身后问一句,这嘎海山上,还有蝈蝈儿叫吗?
蝈蝈儿?那是个稀罕物,跟金猪洞的金猪一样,那只是个传说!嘎嘎嘎——
听了老光棍儿的回答,哈尔姑心里一凉,又颓然坐回那块岩石上。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郭雪波的中篇小说《菩提树》)

郭雪波,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狼孩》《银狐》《青旗嘎达梅林》《蒙古里亚》《诺门罕之锤》《摇篮旁的额吉》等,中短篇小说集《大漠魂》《狼与狐》等十余部,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首奖、第十九届香港“十大好书”奖、德国之声文学大奖优秀作品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郭雪波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