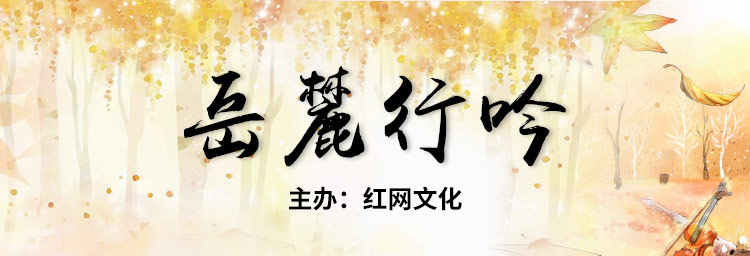

岳麓山的无尽藏
——谢宗玉《千年弦歌》的时间观
文/李颖
“已将全部的自己都给了岳麓山”,这是谢宗玉完成《千年弦歌》一书后的感慨。三年光阴,他把自己种在了岳麓山。他踏遍了岳麓山的角角落落,抚摸了这里的山岚晨雾,也勘测着岳麓山的精神高度。他目光所及,是层林尽染,也是北宋《梦溪笔谈》记载的柴薪危机。他于莽莽苍苍的岳麓山间远眺,与杜甫望见的或许是同一片江水,却永远无法共享诗人登临时的那缕夕照。在每一寸的光影挪移间,时间暴露出它最残酷也最迷人的本质——所有存在皆为瞬间,所有的瞬间永远存在。杜甫离开潭州时的岸花飞舞、韩愈行经时的江帆、柳宗元贬谪时的晨雾,那些看似消逝的时刻从未真正湮灭。
岳麓山海拔不过三百来米,在湖南来说,也不算巍峨,但在谢宗玉笔下却变得无比辽阔,足以照亮世人幽微的精神隧道。谢宗玉笔下,岳麓山不仅存在于空间坐标中,更是由无数消逝的“此刻”层叠而成。在时间不可逆的流动中,我们如何打捞那些被草木掩埋的历史回响?这是谢宗玉文中的终极追问,或者说,他一直在写作中找寻一条通道,并发出了指向未来的深刻叩问:在凝固史料与僵化诠释的困境中,我们该如何重新触及深埋于岁月尘埃中的情感印记,并激活其当代价值?
于是,二十八万字的《千年弦歌》,成了他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它分作四个篇章:《道法源脉》《人物风骨》《诗话流芳》《江山胜迹》,谢宗玉以其辽阔的历史视野与深沉的文哲思索,引领我们触摸麓山肌理中沉淀的文明脉动,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壮游,也揭示这座山独特的“时间智慧”。
这绝非寻常游记,远不是一部简单的山水志,在谢宗玉笔下,岳麓山挺拔醒目,却不拒人千里;它怀抱古刹书院,让它们在各自角落发光而互不相扰;它是城市的地标,又不会过于庞大而难以亲近。这座若即若离的山峦,被谢宗玉精微地切入了三重身份:儒释道三教交织共生的哲学熔炉,风起云涌之近代史的精神坐标,更是一座亟待深度唤醒的情感记忆宝库——那些曾被作者扼腕提及的风花雪月、潭州悲歌、微澜鹤影……构成了一部被时光掩埋的非文字史书。
这个文本,让我读出躲在文章后面那个谢宗玉:他是一个羞涩潜藏的人,也是一个磊落勇敢的人。他沉静如深潭,笔下却奔涌着孤勇的暗流。那份常伴书生的内敛与羞赧,并未掩盖他叩问千古的胆识。
关于岳麓山的文明思考,谢宗玉认为其深层困境在于:尽管麓山拥有丰富的历史层积,其文明阐释却常陷入一种“凝固的、僵死的、单一的”状态。历代麓山书籍多停留于资料汇编的平面整理,对三教合流等核心议题的探讨常囿于陈说而缺乏“纵深思想研究”与“阐发新意的文章”。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多想一步、多说点新的?好像某个历史观点一旦被认定了,就成了不能改的铁律,谁要是想探讨点新东西,就会被看作是对前辈和专家的“不敬”甚至“背叛”。这种静态史观,构成了对文明生命力的窒息性禁锢。
谢宗玉最具洞见的,莫过于时间智慧,在于他发现了岳麓山特有的“时间包容性”。《千年弦歌》中,谢宗玉对儒释道三家在麓山关系史的梳理,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叙述,在这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道家“身化自然”的超越,佛家“修心见性”的终极关怀,并非壁垒森严。西晋慧光明寺点燃佛法之火,十五世纪云麓宫最终扎根山巅,直至北宋岳麓书院以儒学之姿巍然矗立,它们并存在岳麓山上,又“互忍互让,和睦相处”“取长补短,互相进益”。他看到,这座山没有过于强烈的“主人意识”。它不像五岳那样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不像某些名山那样被单一宗教独占。这种开放性,使得不同文明能够在这里平等对话。谢宗玉看到的,不仅是空间上的共存,更是一座山在时间长河中展现的辽阔胸襟。
或许,惟其如此,才使麓山成为了时间的容器,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元素的碰撞、调试与融合的珍贵场域。谢宗玉没有用艰深的学术语言,而是以平实的笔触,让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在岳麓山上行走的僧侣、道士和儒生,如何用他们的日常实践,书写了一部独特的文明交流史。
在书写中,情感维度成为解读岳麓山文明的钥匙。他感慨:“南方多雨,草木葳蕤,很多曾经发生的事很快就被那一山四季青翠给掩埋了。”那被茂盛植被掩埋的,岂止是事件?更是杜甫登临的欣喜、韩愈过境的失落、柳宗元贬谪中的深切依恋、辛弃疾壮怀难酬的郁勃愤懑……这些丰富的情感印记,构成了一部未被充分解读的麓山。作者认为,岳麓山积累的众多诗文绝非尘封故纸,而是可被创造性活化的宝藏。“萤辉古砌延僧炬,鸦噪残碑诵露章”,在百度无生平的作者萧衍守的诗句里,流萤残碑、废墟寒鸦等衰败意象,经谢宗玉的情感想象,被点化为对道乡先生直谏风骨的深情缅怀与精神守护。
“来长沙散心的元稹,终究放不下朝堂往事,一番呼酒买醉后,又怅然而归,算是辜负了这一江碧绿与一山青翠。”这是《元稹:风花雪月觅轻愁》的结尾处。千载后重读《晚宴湘亭》,元稹的醉眼穿透时空,他立在盛唐与中唐的交界处,身前是李杜的万丈光芒,身后是李商隐的深情绵邈。新乐府的革新锐气,艳情诗的缠绵悱恻,悼亡诗的锥心刺骨,在他笔端奇异交融。他与白居易之间的情谊,“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历史终将“元白”并称,却让更懂人间疾苦的白居易赢得身后清名。在这里,谢宗玉没有进行道德评判,因为他如此纯粹,有着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情境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乃至于他看人看物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对错”或“价值”。元稹或许辜负了岳麓山,但他让麓山的时间短暂停留在湘亭夜宴的那一刻,谢宗玉喟叹:“天地光阴,长醉不醒”。元稹将此刻无限拉长,这或许正是谢宗玉最纯粹的时间观。时间不是一条河流,每一个此刻,都是一个饱满的宇宙,都同时承载着过去、孕育着未来,它就是永恒的当下。而谢宗玉,正以一颗悲悯纯净的心,去倾听那些来自时间长河深处的漫漶回响。
“诗话流芳”辑中,《江天暮雪的打开方式》里,那种时间叠加打动人心的力量尤其特别。作为潇湘八景中唯一地处长沙的风景,“江天暮雪”如此打开:天幕低垂,江流凝滞,漫天大雪模糊了天地的界限,消融了人与世界的隔阂,也悄然消融了时间的壁垒。
江天暮雪,不再是古画册里渺远的场景,在谢宗玉笔下,长沙的雪仿佛落在了不同时代的屋檐上。六朝的古寺飞檐、唐朝的殿宇楼台、元代的渔舟、明朝的钓竿,在同一场大雪中相遇。他自己仿佛成了那个披蓑戴笠的古人,他怀念的,是橘子洲还是荒岛时的样子——“看暮色降临,天、山、江、雪、洲、城所营造的氛围是如何迷人心魂”,也直面它如今游人如织的热闹——“提起它,脑海里只有茂盛的植物、接踵的人流”。作者捕捉到那份天地混沌间,灵魂被雪洗去浮尘的孤寂与超然。在这个时间截面里,不只是失意的寒凉,还有勘破世相后清冽的澄明;也不仅仅是独钓的孤绝,更有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自由。
他在写柳宗元,写马致远,亦是在写那个与世界既远又近的自己。他被俗务裹挟,又不甘将一颗心全然捧给这个红尘;他超拔物外,又想要妥帖地照拂身边每个人。他冷静地分析柳宗元那“孤舟蓑笠翁”承载的坚韧,和马致远“钓鱼人一蓑归去”背后的洒脱转身;而他回想起荒岛赏雪时陌生人之间那份默契的温暖——“共情暖意,暗生周边”,笔触又变得格外温柔。史家的眼光、诗人的心跳,让文本愈发动人。他笔下的“江天暮雪”,因而超越了地理景观,升腾为一种承载千古文人精神密码与文化乡愁的诗意象征。当文字在纸页上渐渐隐去,唯有那漫天飞舞的暮雪,跨越千年,恒久飘落在每个读者心灵的江天之间。
每一次对麓山的重访与重读,谢宗玉都将其视为一场充满敬意的再创造,一次为传统注入当下活力的尝试。从历史深处打捞起那些被遗忘的欣喜、失落、依恋与愤懑,并非仅仅为了还原过往,而是为了让这些丰沛的情感能量汇入当代精神的河流。让杜甫的欣喜、辛弃疾的愤懑能在今人心中激起回响,让寒鸦诵章的想象能点燃公民参与的热忱,那么,岳麓山的层峦叠翠便不再仅是眼前的风景,它一定是指向未来的。譬如,麓山积累的众多诗文绝非尘封故纸,而是可被创造性“活化”的宝藏。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提出,将其“挑选一些出来,勒石于游道旁”,那么,在数字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活化”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借助AR增强现实技术,游客步入山中,可在手机屏幕中目睹虚拟重现的“麓山寺僧人雨夜下山,举着熊熊火炬”迎接道乡先生的震撼场景;通过精心设计的声景装置,在特定遗迹处,仿若能听到“寒鸦在残缺的道乡碑上起起落落,呜哇乱啼”。
这座山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谢宗玉的这次写作,是人类在时间深渊前点燃的微小而璀璨的火焰——它或许无法照亮整个长夜,却足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此刻,足以证明我们曾经在场,并试图抚摸岳麓山的无尽藏。他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仿佛能听到山风中传来的千年弦歌,而那正是时间本身的低语。
无人会,登临意。《千年弦歌》,为登临者提供了重新触摸历史体温的可能。它让每个走向岳麓山的人,都能与时光对谈,那么,我们或可共酿一穿跨越古今的精神醇酒,在麓山的辉光下,在时间的截面上,于春秋流转中永恒对饮。

谢宗玉,散文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代表作有《遍地药香》《时光的盛宴》《贼日子》《与子书》《涂满阳光的村事》等。
来源:红网
作者:李颖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