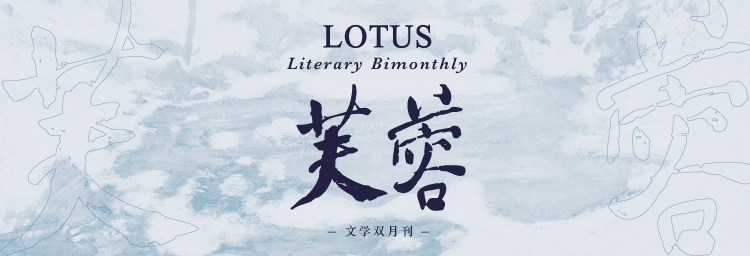

野外麋鹿考察手记(非虚构)
文/沈念
天色藏青,我跑进了一片静谧的湖洲之上。晨雾浓稠,如乳液般在枝丫间流淌。腐殖土松软,在脚下发出咔吱咔吱的声响。我站在树下,树冠像一头垂落的黑密长发,树干上有一道闪电状的焦痕。
麋鹿的宽蹄坚硬地叩击地面的声响,像一把利剑刺破雾空,又如同定音鼓般笃定有力。它从酒红色的帷幕后面走出来,角叉上栖满去年冬天的苔衣。我们之间隔着十几步远的距离,它啮咬着的牙齿之间,像是在嚼碎那块褐色的闪电树皮。
我伸出手想去摸一摸麋鹿右耳后那绺被荆棘钩乱的毛,还不等靠近,它突然奔跑起来,蹄尖踢起的水珠悬在半空,折射出冰凌般的晶光。我呼喊着它:“嘿!喂!等等我。”但它连头也没回。我追了上去,风灌进鼻腔,带着湖洲上潮湿的铁锈味。大雾如同幕布般被拉开,湖洲慢慢向后退成一匹硕大的绿绸,芦苇、树林、草叶在震颤的大地上剧烈地摇摆起来。
我的呼吸也变得紧迫,喉管感到阵阵灼烧。我看见湖洲上错位的季节——麋鹿的脊背时而覆满白霜,时而蒸腾着盛夏的热气。它的脚蹄踩踏水洼,那些如泼墨般的水沫,溅到我脸上,化作一串黑翅鹬的啼鸣。
这真是一场漫无边际的奔跑。我们都越跑越快,像两条疾驰的平行线,某个瞬间我们似乎要冲破雾的尽头。半空中悬着蜂蜜色的月亮,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化。蜂蜜落在麋鹿的眼睛上,变成了它们的眼泪。我踢着脚叫喊着。我很紧张地闭着眼睛,害怕睁眼就看不到它们了。
麋鹿,快跑啰!
麋鹿,回来喽!
喊声是从大地深处传来的。我奔跑的梦也是被这遥远却亲切的乡音惊醒的。我从睡袋的拉链缝隙处看到头顶的树冠,就是梦中那棵长着闪电标记的树。我从漫长的奔跑里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第一章 青铜王冠
时间:2016年2月
地点:湖南省华容注滋口三角洲滩涂
坐标:东经112°48′,北纬29°36′
一
早春的洞庭湖还未完全褪去冬日的寒衣。清晨的湖洲笼罩在薄纱般的雾气中,苇草随风低伏,露出几簇新绿的嫩尖。
洞庭湖,这个被誉为“八百里洞庭”的广阔水域,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是无数生灵的家园。湖岸线蜿蜒曲折,湖洲星罗棋布,芦苇丛生,形成了一片片天然的生态湿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群特殊的居民,誉满全球的兽类明星——麋鹿,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之后,又在湖洲出现了。
麋鹿的再现并不是梦境。它的消失,似乎只是一曲生命旋律的一次长短音的间断。
我踩着湿漉漉的泥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老杨身后。年过半百的他,头上竟然白发簇拥,胸前挎着贝戈士俄式望远镜,腰间别着水壶,步伐却轻快得很。望远镜是一位俄罗斯的湿地研究专家赠送的。这款有出色的日夜两用功能的望远镜,帮他在野外拥有了第二双眼睛。
我来湖区走访,遇到过很多老杨这样的本地人,他们从光着脚丫子起,就在湖洲上跑。白天夜里,生活中梦境里,湖洲再辽阔,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幅活地图。
“再往东走二里地,就是麋鹿群的栖息地。”他回头冲我咧嘴一笑,皱纹里嵌着泥星子。
“你这么确定?”我问道。
“这群家伙精得很,得踩着露水过去,不然惊了它们,跑到角落湾里躲起来,连影子都瞧不见,又要把脚杆子跑断。”他径直朝前走去,留下一个健壮的背影。他说得对,在湖洲上往哪里走都是方向,一旦走错,来回折腾让人跑断腿。找到一个好向导,也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好的交通工具。
到洞庭湖区找麋鹿,老杨是不二人选。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本地渔民,年轻时是个打鸟高手,也因过度捕捞被抓到处罚过,但后来成了保护区脚最勤、心最忠实的巡护员。我零星听过他和麋鹿结缘的故事,昨晚刚张嘴要他亲口讲一讲详细的经历,但隔着睡袋,听到的是疲惫的他打着呼噜的声音。他已经有半个月没回家了。前不久,东洞庭湖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刚搞完水鸟调查,又马不停蹄地组织精兵强将做了一次野生动物调查。这次网格式的调查兵分三路,包抄东洞庭湖保护区水域与薹草地、苇地,重点调查麋鹿活动频繁的注滋河口、天鹅凼、团洲外滩、白湖、红旗湖,我获知消息太晚没能赶上趟,甚是遗憾。几天前,当我找到老杨,说明寻访麋鹿的来意,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跟在他身后,听着胶靴踩着路面砂石发出的脆响,思绪却飘向此前做的“麋鹿功课”——
麋鹿,中国特有的鹿科动物,这些脸像马、角像鹿、蹄子像牛、尾巴像驴的家伙,远古时期以亿计量,却因栖息地丧失与猎杀濒临灭绝。
国内各个历史时期出土的麋鹿化石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我国境内北至辽宁康平,南至广东新会及海南岛,西起山西襄汾,东至东部沿海及台湾地区,都有麋鹿生活过的印迹。
麋鹿的逃亡是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1890年北京永定河发大水,逃散的麋鹿没能逃生,却成为受灾群众的果腹之物。1898年英国十一世贝德福德公爵花重金把十八头麋鹿带去了乌邦寺庄园。那是伦敦郊外的一座著名古园林建筑,1547年英王爱德华六世将这片土地赐封给大臣约翰·罗素,后来成了贝德福德公爵的采邑。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麋鹿被一抢而空,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但贝德福德公爵豢养的十八头鹿自由生息、开枝散叶,一百多年后,数千头麋鹿后裔的足迹分布到了二十多个国家。
乌邦寺庄园挽救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也延续了它在时间里的生命。全世界的麋鹿,就都成了贝德福德带走的十八头麋鹿的后裔。阅读这些资料,我内心刮起一阵风暴,对麋鹿的这段历史有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我问过老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法国传教士与中国麋鹿的故事,更是令人生发很多感慨。
那位法国传教士名叫阿尔芒·大卫。他是1865年秋天来到的中国,有一天在北京的户外郊游时,意外发现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几头“怪兽”。他其实并不认识这种奇怪样貌的动物,但原本是博物学家的他很敏感,隐约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宝贝”。于是他花钱买通守卒,制作了两头麋鹿标本寄回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不久收到了馆长的回信,确认这是从未发现的新种。于是,中国古代的灵兽,有了现代博物学上的第一次命名:鹿科,麋鹿属,达氏种,原产地中国,后来拉丁种名又称大卫鹿。
麋鹿走向世界,竟是缘于这样的一次被发现和被命名。在那个灾荒和战乱时期,也许并无人想到,这群“皇家兽”很快就要在中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而过了一百年后,麋鹿又还能回到它真正的故乡。向中国捐赠麋鹿时,乌邦寺庄园主的后裔塔斯托克侯爵在信中写下:“我的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灭亡的命运……历史不会忘记经历上百年漫长岁月后,又致力把这种著名动物送回故乡的人。”从1985年8月起,中国两年内从英国引进三批七十九头麋鹿,放养在南海子麋鹿苑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过了三十多年,国内以圈养、野生放养、半散养的模式,繁殖出一支占世界总数五分之四的麋鹿种群,数量达到五千多头。
这次来洞庭湖寻访麋鹿,有老杨当向导,当然是件开心的事。在老杨的心里,虽然这片湖洲上的麋鹿是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场大洪水从湖北逃生于此,但他坚信在遥远的古代,麋鹿就在洞庭湖上自由地生活过。他希望它们在这片辽阔的洲滩草甸上重建族群,因为洞庭湖才是麋鹿真正的乐园。这也是老杨这些年毫无怨言地担当巡护员工作的初衷。
昨晚我们是根据老杨手机上的地图定位选择夜宿地的,到了湖洲上,精确的导航和丰富的经验变得格外重要。我在旷野上做了一个追逐麋鹿的梦,睁开眼,看到的是一棵与梦中并不一样的树。枝叶疏落,老气横秋,长在一块小高地上。“它们都在那边。”老杨忽然蹲下身,示意我伏低。
接过他递来的望远镜,我透过一片苇草的缝隙,看到开阔的洲滩上,晨光穿透雾气,草地上像镀了一层金箔,十几头麋鹿正低头啃食薹草。基本上是成年鹿,体长近两米,肩高一米七八左右,毛色灰褐,肩背隆起如驼峰,宽大的蹄子踩在淤泥里,随意地挪动着。麋鹿喜欢在湿地沼泽草滩上奔跑,性格温驯,以植物为食,拒绝山地和平原,仿佛为这洲滩而生。
风卷起一阵寒意,我裹紧冲锋衣,呵出淡淡的白气,眼镜片也随即蒙上一层水雾,模糊了远处芦苇荡的轮廓。交配期未到,麋鹿的结群比较松散,像游荡的闲人。老杨说,马上进入换毛期了,有的颜色偏浅,那是还“穿”着冬毛。但我看到有的鹿身上——深褐色皮毛间闪烁着星点淡棕色,那是新生的绒毛从旧毛丛里探出的头,宛如古铜器上剥落的绿锈下透出的赤金。
我慢慢挪动望远镜,哇的一声差点惊叫起来,一头高大俊美的雄鹿出现在眼前。最引人注目的是鹿角,角叉上挂着项链配饰似的水藻,角尖向后弯曲,整体繁复如古树根系,宛如一顶青铜王冠。
老杨轻轻地按了按我的肩头,说:“那是鹿王,小心惊扰了它。”
鹿角是雄鹿俊美、庄严的标志,通常是在冬尽春来时脱落。古人把麋鹿脱角当作吉祥之象,意味着新的一年万物生机勃发。历代皇室才能饲养麋鹿,这几乎成了皇权的象征,被视为“承天受命,以行王狩”。老杨告诉我,去年从北京来保护区实习的一个博士写了篇很古怪的文章,专门从典籍历史里找与麋鹿有关的东西。
“那些古文把我看得云里雾里,但一想有那么久的历史,不就是证明这是中国独有的吗?”他边说边把文章转发给我。
我最早是在古典名著《封神演义》中读到麋鹿的,元始天尊赠予徒弟姜子牙的坐骑,就是一头可以上天入地的雄性麋鹿,角如玄铁,蹄生紫烟,那个威风可了不得。我快速浏览博士的文章。那篇文章钻研的功夫很深,开篇就是引用典籍中的文字:“商王狩猎,获鹿五十。鹿血祭天,鹿骨占卜。”接着详细述说麋鹿的变迁:周朝以后,鹿成了“仙兽”,周穆王“八骏”中的“鹿耳”,实为麋鹿与蒙古马的混种……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沈念的非虚构作品《野外麋鹿考察手记》)

沈念,湖南华容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灯火夜驰》《八分之一冰山》《歧园》、散文集《大湖消息》《世间以深为海》《长路与短句》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高晓声文学奖、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沈念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