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衰人自画
一、首
我的怒发要冲冠
却被帽子压得服服帖帖
我的额头再高再亮
也不得不在帽檐下低三下四
我的目光如奥运会的火炬
到头来因为看得太多而昏花
我的鼻子像烟囱帮灶王爷
遮盖灰烬,却不能随他的烟上升
我的嘴巴被改装成喇叭
在大街上鸣放,却被讲话捂得严严实实
二、身
我的双肩曾勇挑重担
却被僵硬的扁担压折了骨头
我的胸脯挺得像机关枪
打完后落到心里的是一堆空弹壳
我的肚子是一条河的下游
多少船淹没于不咸不淡的水
我的腰上曾挂着三尺龙泉
如今被自己用一根带子束紧
我的膝盖下从来都只有沙子
这样好,哪怕跪下也不会硌得生疼
我的脚承担我全部的重
却总是被我自己的鞋子囚禁
◎飞蛾死于扑火吗?
冲破飞蛾的重重包围
我冲进小楼成一统
我关紧门户
势要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我一打开灯
成千上万只飞蛾
就企图投奔光明
它们的翅膀剧烈地拍响
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我的灯没有发火
没有去诱惑、捕获
或烧死任何一只
它们全都自己撞死在
灯罩上、玻璃上
伙伴们的身体上
◎东门外
被车轮拥抱后又抛弃的尘埃
奔赴到路灯的裙底下
俯伏下来
像大鸟羽翼下的一群幼雏
一棵白杨的膝盖越是受过伤
越不会弯曲
被初夏微醺的风抚摸着
每一片叶子都在抽筋
另一棵,在灯光的重重围困中
挺起了胸膛,伸手把弯月
取下来,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暖溪
——灵感源于福建省闽清县塔庄镇秀洋村
我这来自大山的皱纹
是众人的眼泪
从一个村
流到另一个村
我用六月的舌头
去舔螃蟹的洞穴
我用涟漪的唇
去吻芋头的根
雨滴敲响我的耳鼓
给不安分的蛙鸣伴奏
月光乱弹我的心弦
把歌声强行灌入倒伏的稻子
让玉米在我的小曲里濯足
让荷叶在我的掌心里跳舞
让我怀中的小虾小鱼
都被你们的画笔钓走
只要那被大山遗弃的石头
滚下来,留下来
在这比刀更狭窄的河床
与我相互取暖
◎冬日的老丝瓜
怀抱着饱满的种子
在冷风里盲目地晃动
像一面卷紧的战旗
一座被敲破的铁钟
亟待月光的尖喙
啄断盛夏的肋骨
取出你怀中的种子
种入黑白不分的大地
◎地铁口的摩托车大军
生计的弦被拉得太紧
生命的弓弯得几乎要崩断
这些箭被狠心地射出去
任何一支
都无法飞出自己的射程范围
这支射中孔方兄的心窝
那支射中垃圾桶的脚踝
还有一支失落在
城外土馒头的后背
铁马升上天空
会把偶遇的飞燕
踏成一摊肉泥
那从地下回来的幽灵
已经在薪水的牢狱里熬得太久
地铁口如火山口
谁会做片刻的停留
◎我是你悬崖上的马
两眼被蒙着斗牛的红布
两肋贴满肥实的秋天
踏破高速路上飞扬的尘土
我向你布满病毒的悬崖狂奔
你的笑容像千年灵芝挂于峭壁
你的裙摆像蝴蝶翅膀敛于峰巅
我的缰绳已经勒断
而马的前蹄已经失落
唯一的阻力来自空气的流动
唯一的救星是谷底的草叶
你悬崖的下巴始终高抬着
等待另一匹马的嘶鸣和白沫
◎农夫与手机
农夫的手机一受冻
就开始冬眠
农夫把这胸藏芯片的蛇
放到贴身口袋里
用体温暖醒了它
它吐出字码的舌头
咧开影像的牙齿
把农夫的时间的血肉
咬了个稀巴烂
◎我的伊甸园被摘除了
今天,我的伊甸园
被从大地上摘除了
那曾经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河流
变成了鲜血的涓涓小溪
柳叶刀逼退苍老的闪电
从松弛的滕蔓上割下我的伊甸园
只留下空荡荡的竹架子
像风中的蜡烛头
守着菜畦的残年
当蟒蛇缓缓爬过田野
我的庄稼迅速衰败
西伯利亚的风不用吹
伊甸园的热带植物都在枯萎
病榻的呻吟从天上传来
连最远方的金牛星都感到了疼痛
大地没有变得轻松
反而更加沉重
◎南锣鼓巷的早晨
最细的雨滴最可能击穿
我华美的伞盖
太阳躲在乌云身后
悄然变回公鸡
已经站上了屋顶
还觉得不过瘾
以为它的嗓子
是明代洪武年间的钟
能震破小巷的胆子
使我受伤的脚步更加缓慢
更难逃脱瘟疫的追捕
昨夜的狂欢已经被冲入下水道
又变成馊味一股股泛上来
几乎要拧掉仿古的鼻子和门面
几乎要逼停宿醉未醒
却赶着上班的轮子
◎竹
无论他们把我横排还是竖放
我都兀自直直向上
他们可以摸着我的胡子叫我小鬼
我会低垂着叶子
俯瞰阿猫阿狗从我脚边走过
无论大地有多大
我的根椐地只需要立一根锥子
每一节都是膝盖和脖子
哪怕被削、被砍
也绝不弯曲
◎火炉在火里
烧得通红的铁块相互碰撞
从这一块踏到另一块
我的赤脚底部吃吃作响
但我在重温咱俩的每一步时
觉得阵阵寒冷
只因为你的火炉已经降温
那时经过火神庙的祈祷后
一整片爱的幽篁就已经被烧毁
◎人与狗
主人与主人相安无事
狗还是会相互撕咬
因为这个主人扔出骨头
与那个主人没有关系
而所有的狗都可以去抢
◎时代诗学
没有鲜花
从春天的铁板上迸射出来
他们用落叶
装饰他们的窗户和门面
细枝末节被他们撸光之后
我的树干将以光秃的姿态
进入这装修的时代
抵御那来自西伯利亚的风
如果你不能把我
从新时代解救出去
就不要靠近
这已经被乌鸦攻陷的林子
连喜鹊都加入了乌鸦的合唱
你走过时,就不要发声了吧
◎幼童照镜子
镜子把我吞了
又把我吐出
我想自己走进去
却被玻璃挡住
我想用手指去戳他的鼻子
却戳到了自己的手指
我想去摘一朵他的笑容
却始终够不着他的脸
镜子的后面
是否还有一个我
我伸手到后面摸了一把
却摸到了自己的后背
我前进他也前进
我后退他也后退
我转身离开
他是否留在里面
◎风箱自白
你推我,我就给你吹
你拉我,我就送你一阵风
在你的推、拉之间
我帮你扇动了多少火
把多少生米煮成了熟饭
把多少骨头炖得稀巴烂
而我始终空着我自己
而且从不主动生————气
(原载于《欧洲诗刊》)


北塔,原名徐伟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系世界诗人大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石头诗选》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作品曾被译成英文、德文、蒙古文等近20种外文,曾出访40余国。曾在国内外多次获诗歌创作奖和诗歌翻译奖。欧洲新移民作家协会诗学顾问、《欧洲诗刊》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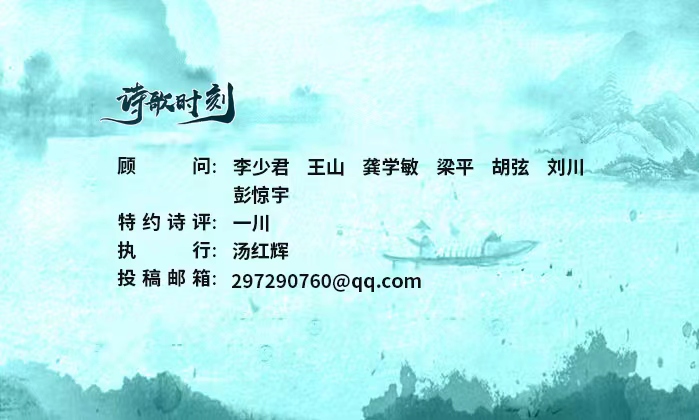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北塔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