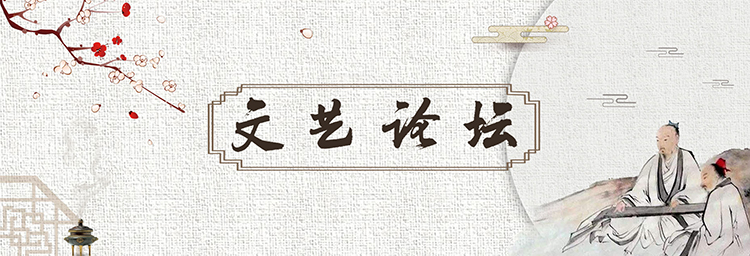

中国当代侦探小说的先锋叙事
——评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文/管季
摘 要:《回响》是一部探究人性的侦探小说,也是侦探小说中的“异类”。它没有博眼球的精彩故事,却采用了更贴近先锋文学的表达方式,借鉴迷宫叙事手法,使情节形成两个循环的圆形迷宫。在心理描写方面,采用深度精神分析叙事形式,着重揭示人物的潜意识与精神缺陷,刻画了人物内心的贪婪欲望。作者东西还描写了一个家庭所影射出来的包含心理纵深的社会,与传统外部社会相比,这样的描写全景式地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精神顽疾,为作品注入了现代性。东西主动靠近了人类存在的绝望,拾起了卡夫卡留下的精神“包袱”,用“众人皆恶”展示了传统伦理的失效,也用“疚爱”探查了人性自省的尺度,为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开辟了先锋化和现代化的可能性。《回响》登上茅盾文学奖领奖台,也标志着侦探、悬疑、科幻等类型小说,已经不单单是娱乐大众的手段,而是有着无限的文学潜力,能够把主流文学的技巧和精神散播开来,真正实现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回响》;东西;侦探小说;叙事伦理;文学现代性
初读东西的《回响》不免失望——平淡的生活,毫无悬念的案件,对当代婚姻家庭伦理的探究,构成了一个极为“日常”的故事。这个故事作为侦探小说而言,其精彩程度和悬念揭晓的技术难度都不尽如人意。没有杀人狂,没有恐怖氛围,没有凸显人物极端的智慧,也没有警匪搏斗的紧张过程。这似乎导致了作品的尴尬处境:尽管登上了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却在主流小说中显得过于“通俗”,在侦探小说中又显得过于“普通”。在五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排名最后,多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种境遇与当年的《暗算》类似,麦家也因此成为很难归类的作家。无论是东西还是麦家,在下笔创作侦探小说之前,应该都考虑过读者接受度的问题,然而他们主观上忽略了这个问题,或者不如说,在侦探小说中,他们属于汪政所说的“艺术派”,借用侦探推理小说类型化叙事方式,而其创作意图却在小说艺术本体和社会、人性探究上[1],与本格派这种纯粹的技术派形成了对比。
这就带来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在艺术革新层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已经开始扭转读者的印象。在反复细读之后,《回响》的余韵才渐渐显现,它对刺激情节的放弃,在以情节为推动的侦探类型叙事中,是一种难得的创新。这既是一部登上主流文坛领奖台的侦探小说,也是侦探小说越来越艺术化的集大成之作。在叙事层面,《回响》已经突破了读者对于侦探小说的刻板印象,从日常中延展出去,进入深邃的人性中,通过深度精神分析叙事展现了先锋作品特质,并通过现代性的伦理叙事,让人性恶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尺度中。相对于传统侦探小说作品以猎奇、惊悚吸引眼球的策略,《回响》的叙事伦理则显示出一种文学性和日常性的回归,以现代性的内核来打破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展现出中国当代侦探小说越来越丰富的可能性。
一、延展的迷宫叙事
迷宫叙事通常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并由马原、余华、格非等先锋小说家率先在当代中国实践。而先锋叙事作为纯文学技巧巅峰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它不仅在叙事结构上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也将现代性的荒诞植入作品中,展现人类潜意识中的非理性和孤独感,借由幻想、梦境、呓语、谎言、记忆缺失、错乱的时间等要素,形成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格非在《迷舟》《大年》《褐色鸟群》等小说中就曾进行“叙述空缺”的尝试,在格非的小说“迷宫”之中,“迷宫”的塑形当然在于关键情节的有意缺失以及作家始终拒绝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上[2];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则直接让读者跳入他的叙事圈套;余华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也描述了少年的幻想,他对于自身的臆想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幻想和现实产生了错位。先锋文学大规模尝试迷宫叙事,的确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种奇观,却也带来了某种担忧:当时批评家津津乐道的“形式”“语言”“叙述”正是先锋文学打天下时的惯用措辞。现在看, 这种阐释方法在为先锋小说打开一个生存空间的同时, 也为之设置了一个封闭的美学陷阱。[3]先锋小说借由虚构来狂欢,却无法很好地从现实中汲取养分,连格非本人都认为先锋作家之所以采用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叙述手法,都是为了掩饰自身知识的匮乏。
这种猜想无疑是十分犀利的。在我们认真地去辨别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现象和转向时,先锋文学要往何处去,总能成为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而在关注侦探小说时,也能够发现一种现象——侦探小说和先锋小说有着天然的结合度,悬疑是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迷宫叙事本身就是悬疑,而侦探小说的故事性和对细节极致的掌控,都弥合了先锋小说的虚构性,填补了所谓的“美学陷阱”。即使先锋从1980年代末的神坛坠落,却依旧在影响当代的文学创作,并逐渐成为当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策略资源。
就《回响》而言,它的叙事结构就是迷宫式的,且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回响”。其实《回响》的故事结构本应是线性的,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简单,它描述的是一个叫夏冰清的第三者,由于向情人徐山川逼婚而被买凶杀害的故事。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冉咚咚充当了“侦探”这个角色,从夏冰清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发掘线索,推进情节。如果用字母替代犯罪链条中的各个人物,那么整个犯罪过程呈现出层层外包的特点,最终形成A(主导者徐山川)—B(买凶者徐海涛)—C(被雇用者吴文超)—D(外包刘青)—E(实施者易春阳)的犯罪链条。而冉咚咚实际的破案过程却充满波折,按照A—C—B—C—D—E—A的顺序推进,冉咚咚在A(徐山川)和C(吴文超)之间反复碰壁,最终这个破案过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形结构。虽然早就知道凶手是徐山川,但苦于没有证据,于是绕了一个大圈,才最终找到徐犯罪的录音证据。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悬疑揭晓过程,是通过不断地审讯和对质完成的,由几个嫌疑人分别诉说自己和夏冰清的结识经过,并由冉咚咚从口供中找出破绽。这种“密室审讯”类叙事属于侦探悬疑小说的惯用模式,除了能集中提供破案线索、清楚描述故事情节之外,也为后续的反转提供了铺垫——显然,毫无疑问,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说谎了。尽管犯罪线索较为简单,但东西也用了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描写这个案件,那就是冉咚咚自己的家庭纠纷。在这个平行的叙述线索中,冉咚咚因为查案而顺便查到了丈夫慕达夫在宾馆开房,出于职业惯性,开始探查丈夫的行为破绽和内心深处的隐秘想法。她反复论证丈夫出轨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出轨对象,丈夫也上演了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的闹剧。作者并未揭示最终结果如何,但冉咚咚后来也明白,丈夫出轨不过是一个假设,她内心真正渴望的就是用这个假设来达到减轻自己精神出轨负疚感的目的,而事情真相本身并不重要。当冉咚咚离婚后迅速投入同事邵天伟怀抱,再与慕达夫见面时,慕达夫才帮助她看清自己的内心。
于是,这个故事的叙述结构就变成了两个循环的圆形迷宫。在第一个迷宫中,五个嫌疑人(此外还有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从隐瞒真相到后来互相揭发、互相推卸,让案件陷入循环;而第二个迷宫是冉咚咚自己内心的迷宫,由精神出轨开始,到围绕着丈夫的出轨事件打转,终点又回到自己内心的欲望。如果不是丈夫看出冉咚咚内心的答案,她大概也走不出这个迷宫,正如这个罪犯E——实施者易春阳,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于是案件很有可能陷入不能破解的死结。录音证据虽然能证明杀人动机,但是层层外包之后,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徐山川实施了犯罪,在现实的案件庭审中,较为常见的情况是审讯口供会被推翻,所以五个犯罪者的结局也留下了一个悬念。
更为吊诡的是,以口供来连接的事实线,也很有可能充斥着虚假的细节,每个人的口供都介于真实和虚假之间,他们隐瞒了什么,连作者也不得而知,甚至连冉咚咚本人都患有精神疾病,偶尔会虚构出现实不存在的人物。这也正是先锋小说常用的不确定叙述手法。东西用这些隐藏的细节将这个事件的真相变得更加迷离。他展现了人性宽广、复杂的内容,正如慕达夫所说:“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4]迷宫的意义大抵在此,如果说先锋小说的审美陷阱构筑在虚无缥缈的高空,那么东西让它沉到了地上,他描写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身上的虚构,是他们大脑中的虚构。人性,借由心灵的密室,延伸至情感的旷野。
二、深度精神分析叙事
博尔赫斯曾经指出,侦探小说如果不想成为一本难以卒读的书,那么也应该成为心理小说。[5]《回响》是一部心理小说,但又不完全是心理小说。东西在后记中直言:小说下笔如此之难,是因为他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6]将心理小说和推理小说结合的例子其实不少,在侦探小说的分类中,就有心理派的划分。传统的心理派作品会借由不同的案例展示犯罪心理,这些案例通常是较为极端的,而《回响》最难得的是将日常融入犯罪,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像是罪犯,而是身边的普通人,案件本身也平平无奇,甚至在十多年前的杂志和网站上一找,会出现无数个夏冰清傍大款的故事。杀人者起初也并非蓄意,甚至都没有详细的谋划,不过就是借由一层层外包,将摆脱夏冰清这个任务交代了下去。至于在哪个环节被理解成了“杀人”,这里也是有悬念的。录音中,徐海涛对徐山川说:“我找过人了,他们说做掉得两百万。”[7]这里的“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徐海涛要钱的幌子,在拿到钱后,徐海涛才将50万拿给吴文超,指使他完成任务。而吴文超身为夏冰清的好友,仅仅只是想让她移民,并不想伤她性命。徐海涛委托吴文超时,也说:“除了不杀她,什么办法都可以用……”[8]而正是因为“杀”字这个暗示,触发了吴文超内心的隐秘“回响”。如果说吴文超完全没有动过杀心,那是不可能的,他抗拒不了50万的巨额现金,但又因为自己内心出现过“杀”字而感到“不舒服”,最后才觉察徐海涛的险恶用意——除了杀掉夏冰清,似乎没有别的永远摆脱她的方法。
到这里,徐山川、徐海涛和吴文超三个人实际上都已动过杀心。但吴文超还是因为内心的怜悯,花10万找来了刘青,企图引诱夏冰清移民,而移民又需要一大笔钱,夏冰清只能找徐山川要钱,这又触发了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阴暗和伪善,包括极细致的心理过程都暴露出来:徐海涛吞了150万和吴文超吞了40万的贪念,企图甩掉杀人责任的掩饰,夏冰清对徐山川的威胁,以及刘青继续雇用易春阳的侥幸心理,证明了“全员皆恶人”。当然,东西叙事的高超之处就在于,除了录音是绝对的证据之外,所有人的口供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也就存在这么两种可能:第一,徐海涛本不想杀掉夏冰清,但是他必须用杀她的借口让徐山川给钱,徐山川本也不想杀她,但知道200万能搞定麻烦之后,也起了杀心,后续各人的交代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尽管一开始谁都不想杀害夏冰清,她还是阴差阳错被杀掉了;第二,徐海涛和徐山川一开始就明确要杀夏冰清,而吴文超、刘青则都在说谎。他们明确买凶,并在口供中掩饰了自己的目的。
无论出于哪种可能性,作品对于人物心理的解剖,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前者可能更倾向于一个偶然的命运悲剧,充满荒诞感,而后一种可能性则揭示出人性最深层的恶,甚至是不自知的恶。正如冉咚咚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出轨,吴文超、刘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过杀人的心。他们说谎,是因为这样能减轻内疚感——事实是吴文超和刘青自己都没有内疚感,刘青因为内疚而来自首,不是因为夏冰清的死,而是因为女友卜之兰为了这件事逐渐憔悴;吴文超尽管由于阴差阳错害死了夏冰清,最后想的还是从徐海涛那里拿回尾款。人性的每一个贪婪、阴暗、懦弱的角落都被写透了。亲密好友随时背刺,给人以希望的伙伴其实毫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侄子坑叔叔,情人之间随时准备为金钱和前途反目,夫妻间则毫无信任可言——案情最后最大的反转来自沈小迎提供的录音,而沈小迎的女儿,压根不是徐山川亲生的。虽然应了“一报还一报”这个古老的诅咒,但作品要表现的显然还是真相与谎言、善与恶、信任与背叛、贪婪与欲望之间的复杂张力。
更让人深思的是,这些人在侦探小说的范畴内,并不属于典型人物。他们不是变态杀人狂、高智商犯罪者或者复仇者,也不属于边缘人群,如妓女、罪犯、流浪汉、儿童、黑老大或者其他特殊从业者,简而言之,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也不可能相信他们有犯罪可能性的“好”人、“体面”人。因此,这样的深度精神分析叙事反而具有强大的可信度,正是普通人的人生才更具有普遍性,普通人的想法才能代表这个真实世界大多数人的想法。而普通人身上善与恶并存的主题,虽然被许多经典反复书写,却在东西这里被写出了更加悲凉的意味。在小说的众多同谋者中,其他人也许是伪善的、分裂的,唯独凶手易春阳本人是纯粹的。他接受了刘青的钱,却不单单为了钱去杀人,他的想法是“他那么尊重我。他给我借火,帮我点烟,夸我诗歌写得好,付我一大笔钱,长这么大谁对我这么好过?就连我爹妈都没对我这么好过”。[9]他被刘青感动了,刘青交代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无论这个任务是不是违背人性。而由于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对“任务”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偏执,所以整个犯罪链中,只有他义无反顾地真正动手了。他甚至还砍下了夏冰清的手,送给了他想象中的完美恋人。
南帆曾说过,对于侦探小说而言,人物内心的缺失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缺陷[10],而东西在脱离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框架后,显然走得足够远。小说中的深度精神分析比之当代最优秀的先锋小说而言,也毫不逊色。小说中数次提到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如村民看到有警察来找刘青和卜之兰之后,就开始对他们避之不及:集体无意识,既是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内心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精神,又是人类原始意识的回响。[11]显然,东西已经将心理解构实验当成了他的功课,其中有沙赫特的理论:任何一种情绪的产生都由外部环境刺激,[12]还有伯特·海灵格说的:清白者往往是较危险的人,因为清白者心怀极度愤怒,会在关系中做出严重的破坏性行为。[13]还有对冉咚咚心理的一段精彩分析:她通过否认、压抑、置换、投射、反向形成、过度补偿、抵消、认同、升华启动了自我防御机制。[14]这些心理学专业术语,不仅仅是为了深入探究人性,也展现了侦探小说融入纯文学的可能性,打通了先锋和通俗的壁垒。人物内心的缺失被极大程度弥补,而且这种弥补不仅仅是面对罪犯或侦探的内心而言,也广泛辐射到了与案件不相干的每个人身上。
三、现代性全景叙事
这种广泛辐射的社会全景式写作,构成了东西小说的另一种先锋特色。当我们谈到现代性时,一般会联想到先锋小说的深邃和荒诞,却很难联想到“社会全景”式写作,这里的社会,是由一个家庭所影射出来的包含心理纵深的社会,而非巴尔扎克式的外部全景社会。巴尔扎克和卡夫卡本就是现代性硬币的两面——没有巴尔扎克对社会的正面硬攻,也不会有卡夫卡“头朝下”的出逃。东西说过,卡夫卡的写作心态有利于作品构思,巴尔扎克的写作心态有利于小说的推进。[15]这两位都成了他写作《回响》时的精神动力。反观《回响》的叙事结构,确实采用了现代派的迷宫叙事和精神分析,但唯独在描述社会这个层面,东西扎扎实实沉到了现实中。
而现实的社会,毋庸置疑就是现代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金钱至上、尔虞我诈已经不是一种虚构,小到心理医生、高校学术圈,大到工人阶级、农村乌托邦,都被东西解构了。各种社会恶象连接上演:没有背景的普通女孩,被强奸后只能选择做“小三”;有多个情人的大老板与妻子各自出轨,相安无事;主持正义的警察自己患有强迫症,时常焦虑甚至产生幻觉;高校教授为了晋升,抛弃专业操守,填报擦边课题;作家借艺术发泄欲望,渴望“一夜情”;老师剽窃他人的观点,出轨于崇拜他的学生;出身农民家庭的普通工人为了一万块杀人;买凶者逃到农村隐居,过乌托邦生活……各个阶层的生活被浓缩在这个普通案件中,这就是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它反映了现代人迷惘的精神状态和无限下沉的道德底线,反映了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之后的挣扎,以及“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式批判。整个社会都是焦虑的,犯罪是一面镜子,连接着社会和历史的种种要素,人们得以反观自身最深不可测的欲望。正因为犯罪本身的现实性和神秘性,一些批评家深信犯罪小说构建了现代性的神话体验。这个神话说的是,生活在一个由更新和解体、进步与破坏、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对立力量所统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犯罪小说所具有的评价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要素的能力,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样态,而是这种艺术门类产生的必然结果。[16]
读者对于侦探小说的痴迷也在于此,他们追求的也许并不是精巧的谜题或者“烧脑”的破案过程,而是现代性构筑出来的神话。这种神话与古典神话的根本区别在于,古典神话无限强调人的力量,将神性和人性融合为一体,寻找人类的上限;但现代性的神话则将人性无限解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性的下限。这个下限隐藏得越深、代表正义的警探与之周旋得越久,那么这个故事就越是会被神化,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信徒。侦探高手也理应具有神的品质,他(她)必须大公无私、智慧过人,且善于勘破人性,排除一切干扰——但是东西明显将这种神的品质解构了。冉咚咚不仅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普通警察,且与杀人犯易春阳患有同一种疾病——她有妄想症,会虚构不存在的人;她也非道德偶像,在得知丈夫可能出轨贝贞后,报复性地与贝贞的丈夫有过亲密接触。一个研究别人精神世界的人,自己却有精神疾病,而一个道德审判者,自己也差点走入歧途,差点成为被审判者——相比神话,这样的描述显然更符合现实,它既是一种对外部世界进行解构的现实,也是全景式的心理现实。这种现实同样延展到读者当下的心理现实——小说中的“小三”被杀案件已经见怪不怪,无法让读者感到新鲜,可见这个时代的下限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借冉咚咚反观当下现实,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包括判案者。
这是东西对于传统侦探小说深度的推进,也是东西对于现代性的传承与解构。面对社会,东西一向都不吝于给出自己的批判和思考。他的创作大多是寓言式的,如《耳光响亮》中的去父(失踪)与去子(流产)寓言了整个“后文革”时代人们的徒劳和无所依靠;《后悔录》中莫须有的强奸罪,也一样寓言了时代的荒诞禁忌。他和所有现代派小说家都具有同一种野心,想站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肩上看看这个世界的形状和结构,以及被隐匿起来的真相。他的小说既不像典型的先锋小说,也不像现实主义小说,他总在通往真相的路上反复徘徊,连描写一个大学教师,也要谈论一下社会的顽疾,引用一下鲁迅的名言,并且发出了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楚门的世界”的呼喊:“我是不是演员?这所大学是不是摄影棚?”[17]慕达夫作为唯一有可能洞穿真相的知识分子,却陷入了无尽的迷惘与挣扎,这也暗示了作者实际上一直在思考这个社会的出路。
正如李洱所说,东西的写作兼具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首先,是他的抽象和具象的结合。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代里面最具卡夫卡气质的作家,带有很强烈的抽象主义风格,他的抽象是通过非常具象的、非常情节化的故事来表现抽象,这个能力在中国当代作家里面是罕见的。其次,东西做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所有心理学的分析都是现代的;而现实主义,应该写的是现在的生活,人物的出生、成长、受教育、死亡,一个行动的过程,所以表现各种行动的小说往往属于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奇数是现实主义的,而偶数是现代主义的,非常巧妙。”[18]东西的作品主题往往隐藏得非常深,看似平淡不惊的故事情节下,其实融合了他对于整个时代的思考与质疑,并且向下探究,还可以发掘到更深处。就如慕达夫对于时代现状的悲鸣和对于世界真实性的质疑一样,他自己终究还是成了一个不真实的人。他揭穿了冉咚咚精神出轨的伪装,同时对她说:“直到今天我都没背叛你。”[19]他可能是真诚的,但如果他认为冉咚咚对邵天伟的喜欢叫背叛,凭什么他认为自己对贝贞的欣赏和幻想就不是背叛呢?而小说中始终没有揭露,慕达夫开房究竟是干什么去了,小说里面每个人物的每句话都变得不可信,整个叙述成了一种对真实的解构。可见,东西对于人性的发掘并未仅仅停留于表面。人性太复杂,睁眼看世界的人,往往看不清自己的内心,徒劳和无意义感体现在每个人身上。
《回响》是越读越让人惊叹的。初看,它不过描写了一个简单的凶案;再看,它是一个悲哀的人性莫比乌斯环;再细看,它居然是一种全景式写作,不仅写透了现实的虚幻和徒劳,写透了人性的龃龉,也利用侦探小说的互动,穿越了作品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写透了读者的内心。一千个人会对作品有一千种理解,最后,作品利用一个混沌的“爱”字收拢了一切。这个结论本身也是分裂的:“疚爱”的力量尽管如此强大,却基于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更多情况下,大部分人也许永远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错。正如办案过程中,如果不是冉咚咚拿出了带血的假内裤,徐山川不可能承认自己强奸了夏冰清;如果不是冉咚咚找来徐海涛深爱的女友,徐海涛也不可能招认;如果不是冉咚咚发现吴文超缺爱,利用了他的母亲,吴文超也不会被捕;如果不是冉咚咚住在村里让刘青被村民孤立,刘青也不可能自首;如果不是冉咚咚用诗歌和谢浅草叩开易春阳的内心,易春阳也不会指认出断掌所在;如果不是冉咚咚利用徐山川女儿的DNA鉴定报告,沈小迎也不会为了自保出卖徐山川。其中任何一个链条断掉,这个案子就会陷入停滞,因为当事人没有内疚,他们的内疚是外力激发出来的,并不是他们主动意识到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反讽——爱也许是可信的,不可信的是人自己。
四、侦探小说现代化的尝试
要清楚东西的《回响》将中国当代侦探小说推进到了何种程度,就要先弄清当下侦探小说的现状与动向。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和科幻题材一样,长期处于被主流文学压制和轻视的地位。尽管有中国古典狭义公案小说在前,但这些作品基本是论证传统封建伦理或发出一些民间朴素的正义之声。晚清民国阶段的侦探作品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法治精神,杂糅着传统忠孝、豪情等多方面元素,呈现出过渡阶段的思想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反特小说属于革命伦理叙事,而这种“国家安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明显以现实功利目的取代艺术的创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探小说的艺术成就。[20]新时期之后再度繁荣的中国侦探小说,公安题材维系了人民伦理叙事,西方侦探小说影响下的玄学侦探小说则发展了个体伦理叙事。新世纪之后的侦探小说更为多元,叙事伦理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麦家这样无法归类的主流作家,也有网络作家将侦探与推理、悬疑、科幻、玄幻、古典传说等类型小说叙事结合的探索。产生了如蔡骏、那多这样借古代传说和原始文化来书写地狱惩罚、生死轮回、阴阳交错、灵魂附体、巫术蛊术的作家,其创作属于“知识悬疑”类型,是典型的丹·布朗式的思维。[21]也有雷米这样以现实案件和犯罪过程为出发点,以破案为目的,向福尔摩斯式侦探小说靠拢的作家,其《心理罪》系列也属于心理派的优秀实践。还有紫金陈这类网络作家,以《坏小孩》《谋官》等作品,延续了东野圭吾式的写作,将人性融入悬疑中;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蜘蛛的《罪全书》、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作品等,都已成为侦探小说阅读榜上的常客。然而这些作品基本还处在通俗文学的框架和尺度之内,在叙事伦理层面而言,并没有超越古典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的范围,以“谁干的”为谜面,以“为什么”为谜底,最终指向对正义和法制的思考。
显然,侦探小说叙事伦理变迁表征着中国大众文艺的文化伦理特征,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问题,也亟待更新和进步。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朦胧诗到先锋小说,现代派文学仅仅只是围绕着技术层面进行模仿,却不为读者真正理解和接受。先锋并不代表着现代化,真正现代化的文学是面对这个现代化社会的双面反馈:一面是批判,一面是逃避;一面是解构,一面是重建。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在于他将人性解构,由他人之恶反观自身之恶,指出人皆吃人的乱象;莫言小说的现代性在于他将历史解构,从教科书中叛逃,重建了一个想象的时代;而《回响》也加快了侦探小说现代化的进度,东西把整个世界解构了,一切都是虚构的,无论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还是从人脑中想出来的。这同时也是主观上对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个世界中有着最神秘的某种原则:从微小的情感纠纷到一个杀人的念头,不过就是一念之差,恶念会被放大,一层层放大之后,最终由一个善意的动机来完成恶的行为。
这种宏观的隐喻,比之传统侦探小说所描述的微观层面的、为了犯罪而犯罪的描写,要显得柔和、隐蔽得多。一个疯疯癫癫喊着要报复全人类的杀人犯,或者一个高智商越狱逃犯,不会比一个现实中的普通农民工更具有现代性,后者的绝望才是真绝望,后者的恶才是普遍的恶,后者的爱才是尘埃中生长出来的爱。先锋小说用尽全力实践的文体结构革命,也不会比细致描摹当下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具有现代性。与其说现代性是一种文体革新,不如说现代性是一种精神限度——这种精神限度首先是卡夫卡带来的,他呈现了一个“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并“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22]这里的他们指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的写作者,也泛指绝大多数普通人。大众往往都是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学也因此抛弃了沉重的负担。在新媒体的发力下,侦探题材以另一种方式风靡起来,《唐人街探案》《消失的子弹》《追凶者也》《隐秘的角落》《嫌疑人X的献身》《解救吾先生》《白日焰火》《我是证人》《心迷宫》等众多国产影视剧和翻拍片层出不穷,侦探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大众关注的更多是其中惊险刺激智斗的部分,而不是探究其剧本的文学性,即人性的苦难与尊严。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不仅要在通俗化、商业化的诱惑中艰难前行,还要拾起久违的高贵的尊严,直面人类存在的不幸。
在这一点上,《回响》显然主动靠近了人类存在的绝望,拾起了满载冲突的精神包袱。这种尝试无疑是可贵的,东西用“众人皆恶”展示传统伦理的失效,也用“疚爱”探查了人性自省的尺度,为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创造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指向“先锋”,也指向“现实”,更指向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侦探小说不仅承担着拯救道德秩序的使命,也对整个现代化城市空间进行描摹,并与之对话。巴赫金在对复调小说和小说杂语的讨论中,曾着重指出虚构小说以不同形式手法引入社会杂语并由此激发对话和思考的能力。犯罪小说通过罪行环节的故事建构,对犯罪地点、涉案人物、犯罪动机的艺术再现,实际上为各种激进观念提供了展示空间,引发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23]各种犯罪也许各有理由,但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唯一的共同理由就是钱。金钱腐蚀了一切,让一个被强奸的女孩沦为了有钱人的情人,让原本守法的普通人燃起了贪念,也让真正穷困潦倒的人看到了尊严和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是虚幻的,这也正是现代性的绝望。小说中写道,易春阳曾给家里汇了一千元钱,“说到一千元时,易父自豪地竖起一根手指,好像那根手指就是现金”。[24]富人的两百万和穷人的一千元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对话空间。这是现代性和原始欲望的对话,是阶级与阶级的对话,是城市与农村的对话,也是一个饱受生活摧残的贫穷者与良心之间的对话。贫穷把人变成了兽,人性在降格的同时也渴望被尊重,重新站立起来。这座现代化的城市,不仅仅是斗兽场,也记载了人性的浮沉。
侦探小说与先锋叙事结合,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它不仅标志着侦探小说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承继了主流文学的艺术性,也标志着侦探、悬疑、科幻等类型小说已经不单单是娱乐大众的手段,而是有着无限的文学潜力,能够把主流文学的技巧和精神散播开来,真正实现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深度融合。除此之外,它也预示着先锋小说开辟另一条广阔的大众之路的可能性。正如陈晓明所总结的那样,在年青一代作家已经对既有的文学经验以及当下做新的文本试验都不太感兴趣的时候,反而是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阿来等上一代作家,在历史意识、现实感以及文本结构和叙述方面不断越界,寻求把中国文化传统经验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经验混为一体的方法,他们“骨子里是先锋派”,而先锋就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变革的超越,更是一种更新的创造力[25]。先锋没有隐匿,更不会消失,只会伴随着新的文学形式传承下去。大众对于侦探题材文化产品的热情经久不衰,本身也说明了先锋叙事与侦探小说结合的广阔发展空间。东西在侦探小说本土化、侦探小说先锋化的尝试中,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1]汪政:《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论纲》,《艺术广角》2007年第3期。
[2]周显波:《格非小说叙事的时间寓言与哲学》,《文艺论坛》2020年第5期。
[3]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4][6][7][8][9][11][12][13][14][15][17][19]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5页、第348页、第340页、第219页、第319页、第299页、第155页、第266页、第341页、第349页、第181页、第345页、第317页。
[5](阿根廷)博尔赫斯著,陈泉、徐少军等译:《文稿拾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89页。
[10]南帆:《〈回响〉:多维的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
[16]John Tompson:Fiction, Crime and Empire: Clues to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69.
[18]本刊编辑部:《东西长篇小说〈回响〉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20]胡和平:《试谈中国侦探小说》,《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6期。
[21]朱全定、汤哲声:《当代中国悬疑小说论——以蔡骏、那多的悬疑小说为中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22]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6页。
[23]段枫:《犯罪小说的叙事内核及其伦理考量》,《国外文学》2016年第2期。
[25]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再思考》,《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
*本文系2020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GD20YZW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管季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