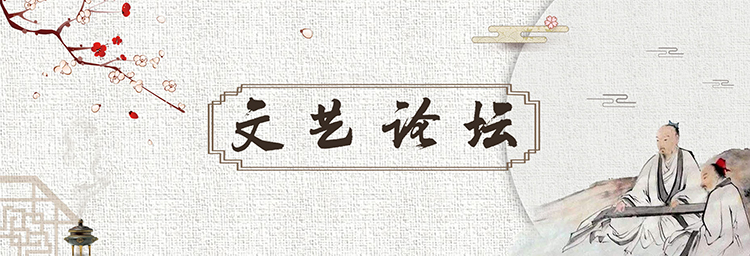

“雅”与“俗”的互动:论李宏伟、王十月的跨界写作
文/蒋洪利
摘 要:作为跨界者,李宏伟和王十月的创作为科幻文学注入了许多新质。“纯文学”思考方式下的“未来现实主义”写作使他们的作品饱含人文性,文本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他们对科技发展的隐忧;他们的写作在关切科技与人的辩证关系时,其思考方式往往是哲学式的;与此同时,李宏伟、王十月还将“先锋”文学形式融入科幻小说中,从而在形式上创新了科幻文学的形貌。然而,当他们无限拉近了科学幻想的时间点,在“近地端”畅谈“未来现实主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科幻文学本身的魅力,产生了不适反应。首先,他们的科幻小说较为缺乏科技感。其次,他们将笔力过多地用于观念的传达以及哲理的阐释上,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因而,这种“雅”与“俗”的互动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开掘。
关键词:李宏伟;王十月;未来现实主义;跨界写作
在众多的文学类型中,科幻文学凭借其内蕴的科学理性、瑰丽想象成为文学长河中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与此同时,它也凭借自身书写的丰富性、异质性成为一门演绎“跨界”的艺术。它“囊括太空宇宙、宏观微观、万物生灵等万象题材,汇聚人工智能、自动化、物联网、脑联网、VR 增强和虚拟现实、区块链、社交媒体等前沿阵地,联结科学、小说、影视、游戏、音乐等领域,文理打通,时尚碰撞,大胆预言想象新科技和文化”①,恍若未来世界的试验场。如果说科幻文学的跨界性质为其带来了艺术丰腴度与文学表现的内部张力的话,那么跨界作家的加入则为这一文学类型增添了许多异质和变化的可能性。
1990年代以来,作家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一方面,专业的文学创作者有的开始下海经商,有的转型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另一方面,非专业文学创作者也转型进入专业的文学创作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跨界业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②在王朔、韩寒、郭敬明、张嘉佳等人的跨界进入导演、编剧行业之后,李宏伟、王十月则从诗歌、小说的“纯文学”创作跨界到“科幻文学”(类型文学)的创作领域中。虽然与王朔、韩寒等人的跨界相比,李宏伟、王十月的跨界步伐显得小了很多,但科幻文学自身的跨界属性则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当“跨界”遇到“跨界”,作为类型的科幻文学也很难不产生新的表现形式与价值主题。
一、“未来现实主义”下的科技隐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习惯用“科幻小说”的概念统称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夏笳等人的写作,然而,当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所指意时,往往遮蔽了科幻小说内部的诸多异质性因素。在具体的科幻写作实践中,科幻小说因其描写侧重点以及展开描写的方式可以分为“硬科幻”和“软科幻”两种。所谓“硬科幻”便是那些尊重科学精神,推崇科学理性,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基点展开叙事的科幻作品。相对而言,“软科幻”则指那些“在科幻背景下描写社会人文,以表现人与人关系为主,题材集中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内容,重在情节发展叙述”③的科幻作品。而根据文本的立足点是重“科”还是重“幻”,又可将科幻文学分为高概念科幻、未来学科幻与隐喻派科幻三种。④其中,“先幻后科”的科幻文学作品属于高概念科幻,即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先预设某一概念,然后再以科学术语夯实。因而此类科幻文学的形成依据的是创作者的头脑与非凡的想象力而非现实的科学技术。与之相对,“先科后幻”的科幻文学作品则属于未来学科幻。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创作者沿着现有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路向展开想象,探寻科技发展的未来将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相较,隐喻派科幻仿佛自成一派,它不注重对科学概念的解释以及对未来科技的想象,而是意图在未来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探讨现实社会问题。此外,如果按照科幻文学对未来时间设定的长短划分,科幻文学可以分为近景想象型、中景想象型和远景想象型。按照叙事内容离现实的远近,“近景想象大致是50年左右的事情,而中景想象大致是50年至300年,而远景想象则大致是300年及以后”⑤。因此,近景想象型的科幻小说的“未来想象深深地植根于当代想象中”,中景想象型的科幻小说所关注的往往“是人类命运与人类生命的问题”,而远景想象型的科幻小说则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科幻小说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某一文学作品很难被严格地划归到某一类型之下。科幻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与含混性使其往往成为多种类型交织的混合品。具体到李宏伟、王十月的科幻小说写作,王十月曾以“未来现实主义”概括其写作特质。⑥所谓“未来现实主义”,其实质便是以未来想象的方式关涉当下科技发展的可能性与潜在危机,换句话说,它是以科幻想象的方式介入未来社会的发展,写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科技必将带来的现实”⑦。如果按照此前所列出的分类标准来看,“未来现实主义”式的科幻写作当属于中、近景想象型的隐喻派科幻。
在《如果末日无期》中,王十月将五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的故事连缀成了他对未来现实思考的寓言诗,其中浸润着他对科技发展的审视与隐忧。王十月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在面对科技发展时,他是忧患派的——他赞成科技要发展,“如果不发展,我们还在山洞里面住着,但在大方面乐观的同时,更多的是忧患”⑧。因而在科幻文学创作中,王十月更多的是在表现科技高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困境以及对这一困境的思考。《莫比乌斯时间带》中,今我为了寻找进入○世界的入口,在“量子吧”遇到了我在未来。经我在未来之口,今我了解到WA病毒——该病毒其实是拉奥教授为了实现自己的科研理想制造出来的恐慌——曾试图摧毁物联网,为了清除该病毒,拉奥教授决定建立“蜂巢思维矩阵”。进入这一矩阵中的人将丧失个人的自我意识,而融合成的“超级大脑”强大到能随时捕捉人类的意识从而控制人类的思维。当这样的矩阵越来越多后,“人类最有智慧的大脑”,有可能“成为政客们的科技奴隶,而且是没有自我意识的科技奴隶”⑨。如果这样的境况出现,那么,作为个体的人将不复存在,自由自在的个体思维也将不复存在。《胜利日》里的人因未来信息爆炸不得不在大脑里植入纳米芯片以处理海量信息。反对者认为“实现人机互联是反人类的,和计算机结合的人类不是真正的人类”。“于是他们设计出了一种病毒Garbage,Garbage病毒迅速在信息网络中传播,自我复制垃圾信息,他们试图瘫痪信息网络,逼迫人类回归纯粹的人。”⑩内森则设计出MC程序以等量的速度清除反对者制造出的垃圾信息。作为清道夫的安德鲁意外发现MC程序里存在一个禁区——它能够感染并入侵公民大脑,使受感染者只能接受指定信息。这也就是意味受感染者所了解的世界是程序设计者按照某种意图塑造出来的,所谓的真实其实是虚假。当这种程序病毒扩散到整个人类世界后,人类将丧失自我。而当这一程序被独裁者掌握时,人类就会变成独裁者操控世界的工具。《如果末日无期》里罗伯特教授通过纳米技术实现了“永生”,然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父亲与女友死亡的命运。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永生,永生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虽然在故事的设定中,谁能获得永生是由大数据说了算,然而站在大数据背后的可能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抑或是金融巨鳄。他们把持着实现永生的权力。这也就是说,永生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甚至还将成为他们统治民众的新的暴力机器。王十月凭借其对科技发展的认知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审视,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技变革将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以一件他认为最合适的“衣服”重新“装扮”了科技革命的“样貌”。
与王十月一样,诗人出身的李宏伟也热衷于思考科技进步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的问题。《暗经验》中的张力在储备处阅读了五年经典文学作品来培养自身的审美力,以求能够进入到暗经验局工作。而所谓的“暗经验”其实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潜意识,它是人们在长期的阅读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文学的本能反应与本能认知,是处于经验之下的更具决定性力量的一种能量。暗经验局存在的意义便是通过局内员工的暗经验来匡正、规约人的创作,使其在适当的范围内发展,也使其具有时代意义。为了解决创作的分配与互动的问题,暗经验局下设的翻检、筛查、设定、擦拭四个处,对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出版进行全面的指导。在一定意义上,李宏伟的《暗经验》与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梦宫》存在某种互文性,在《梦宫》中,“阿尔·克莱姆在睡眠梦境管理局工作,主要是收集、分类、分析成千上万的梦境,以便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帮助国家和君主免于灾难”。张力所在的暗经验局则将文学创作者的思考与文学创作方式规约到意识形态所允许的准则内,对于不符合暗经验局要求的作品一律不允许写作、发表。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后,作家的创作活力将被无情的斩杀,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将如《命运与抗争》一样,成为歌颂国王丰功伟绩的干瘪之作。在《国王与抒情诗》中,作者以更加深沉的心境、更加锋利的目光再次审视了科技与文学的关系。在2050年,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宇文往户意外死亡。宇文往户的好友黎普雷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往户身死的秘密——原来宇文往户获奖已被预知,他是在别人的“操控”下完成了获奖作品的写作,而这一切的设计者则是帝国文化的国王。国王通过意识共同体影响了宇文往户的灵魂,提示了他所要形成的文学经验以及具体的文学写作。国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取消语言的抒情性,使个体的抒情消失,让人们走上一条可以被预见、被规定的语言使用方式的道路。当人们都用可预判的语言来说话的时候,那么人类就实现了另一种方式的永生。然而这种永生的实现是以丧失抒情的个体性、言语表达的自由性为代价的。应该说,李宏伟思考的具体命题是科技发展给语言的文学性带来的困境,而语言的文学性背后藏着的则是人的主体性以及关于人的定义的问题,就此而言,李宏伟所思考的命题与王十月所关注的话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二、哲学命题的科幻式思考
作为跨界写作者,王十月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的写作是未来现实主义式的。科幻只是给他的现实主义思考提供了一套极为合适的“衣服”。无独有偶,李宏伟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所书写的是个人体验后的现实世界。可以说,科幻为他们提供了一面可以反观现实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作者想要描述的也并非未来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之事,而只是想在作品中陈述一种可能的现实,这现实,基于他对这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基于他所知的一些差不多是绝密的,而又众所周知却无人相信的科技成果,以表达自己对科技社会现实困境的思考”。而在他们“纯文学”的写作经历以及广泛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他们的思考在关切“人”本身的同时,其思考方式往往是哲学式的。
《如果末日无期》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每一章都有各自侧重的主题。每一个主题背后,分别凝结着王十月对科技伦理的认识与反思、对人性与人类文明的审视与希冀。在《子世界》中,王十月试图探寻真实与虚无的辩证关系。子世界的张今我发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他们可能是只是一条计算机的信息代码。而在他们的世界之上的元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掌握着这个世界的法则。当今我认识到这一点时,他感到十分痛苦。怪烟客却安慰他说:“虚实可以是外在的,属物;也可是内在的是,属灵。如果我们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么,虚也是实,我们不会感受到生命是一串代码……反过来,元世界的人类,就算他们是真实的存在,如果内心感到的是虚无,那么,他所在的世界,也依然是虚无的。”在这一哲学辩证关系中,个人感受成为裁判真实与虚无的准则。只要你对你所及都能准确地感应并能够找到生存的意义,即便你真是一条代码,那么你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具体论辩过程中,王十月也将庄子的传统哲学融入其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元世界、子世界、○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世界呢?在作者看来,追寻这一命题并无意义,只要自己能够感受到个体的实在、寻找到作为个体的生存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于他而言便是真。
真实与虚无的哲学思辨外,王十月在《莫比乌斯时间带》中反驳了刘慈欣的科幻哲学认知。刘慈欣的科幻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而非个体的人,所以当他以“假如人类文明只剩你我她了,你必须以吃掉她为代价才能保存人类文明,你吃吗”为题发问时,江晓原选择不吃,刘慈欣选择吃。这也就是说,在刘慈欣那里,人物形象主要以两种方式呈现于众:一是以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二是一个环境或一个世界作为文学形象出现。而在王十月这里,个体的价值始终高于整体的价值。在故事中,当张今我为了寻找进入○世界的交错口时,在“量子吧”遇到了我在未来。我在未来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张今我写下《退之的故事》。这是因为在未来,司徒退之因看了张今我的小说,在面对拉奥教授的“阿瑞斯计划”时,选择假意加入,待消灭了WA病毒后摧毁了“蜂巢思维矩阵”。然而当外星人进攻地球后,人类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人类文明行将毁灭。为了保存人类文明,我在未来希望张今我能够改变故事的结局以保存“蜂巢思维矩阵”,但张今我并没有修改此前的结局。因为“他坚信,如果人类连思维的自由都失去了,这个物种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如果末日无期》中,王十月则从另一个侧面思考了人权自由与科技伦理的问题。罗伯特教授因为专注于以东方神秘主义学说寻找人类的永生之路而被纳入永生人的行列。然而成为永生人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与城实,就只能按照永生人的规则行事,臣服于整体意志。于是,罗伯特教授不得不在挣扎与痛苦中迎接父亲与女友的死亡,他也在为儿子寻找永生机会的过程中违反条例,被判处终生监禁。可以说,罗伯特在获得永生的过程中失去的不仅是精神的自由还有身体的自由。而罗伯特教授的悲惨遭遇也提醒人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永生的。唯有在财富、权力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的人才能获得永生,而这种权力的获得也使得他们成为权力的分配者,换句话说,永生即为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在王十月看来,科技发展虽然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困境,但很多时候,这种困境的产生更多的来源于人类本身。在《胜利日》中,安德鲁沉浸在一个名叫大主宰的游戏中。作为清道夫的安德鲁发现了内森的阴谋,联合皮特制造了the truth程序成功解除了危机。作为拯救者的安德鲁因此被推举为元首。然而掌握自己杀害女友朱恩秘密的皮特成为安德鲁的心头大患,于是他通过秘密手段释放了内森,并在内森的帮助下重新设计了MC+程序以求小范围地控制他人的思维。内森的存在对安德鲁来说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排除隐患,安德鲁用毒药杀死了内森,并在他遗留的设定程序里找到了皮特。于是他按下启动键将皮特变成了白痴。至此,他终于成为了大主宰。然而当他想要变出山花烂漫的世界时,世界却充满了蛇虫鼠蚁。原来大主宰的世界是人性的映照,邪恶的内心只能映照出荒凉、残暴,满是混乱的世界。安德鲁唯有清理干净自己的灵魂才能获得解放。在这个故事里,内森、皮特、朱恩都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获得最终胜利的安德鲁所印证的也只是“胜利者一无所有”的谶语。科技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这其中的关键并不是科技而是人,唯有人类先净化己身才能真正地掌控好科技的红利,否则,人类只能在科技的狂潮中走向死亡。
如果说王十月是站在哲学的角度思考人与科技的辩证关系,是一种外部透视的话。那么,李宏伟思考的则是科技、文学与人的关系,属于一种内部透视。《暗经验》中,张力为了适应暗经验局的工作,逐渐丧失了自身的审美能力,身体逐渐变白、逐渐变透明。“白”“透明”在这里成为一种隐喻。身体越白说明对现有的文学写作与评价规则越认同,也意味着越发丧失自身的独特性与个人审美。于是,对规则越认同,身体变白得越快,地位也就越高。身体的完全透明也就意味着个体对规则的完全信服与融入,个体成为规则的代言人。而在这种规则的盛行下,原先有个性、有创造力的文学写作者将会被埋没,被同化的作者也将如萧峰一样彻底失去文学创作的能力。《国王与抒情诗》中,国王想要取消语言的抒情性,抒情性的取消也就是语言“歧义”的取消。毕竟“语言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方案’,阻碍了人类的交融与统一,一旦语言的‘歧义’消失,通过意识的交流,人类将重新‘一体化’,进而实现群体性的‘永生’”。与之相反,宇文往户则要保存语言的抒情性,为此他坚持创作“抒情诗”。在抒情诗中,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物种、一个民族,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就此而言,李宏伟借国王与宇文往户的对立所要探讨的是个体性与整体性、一体化与差别化的问题。当个体之间的差别在语言层面完全被取消之后,人类真的能够实现“永生”吗?可能并不能。《国王与抒情诗》的结尾处作者虽然并没有直接给出黎普雷的选择,但以《暗经验》中作者所占据的价值尺度来看,他其实并不认同一维化的语言可以成为人类实现“永生”的金钥匙。当个体性、差异性被取消之后,人类也将失去蓬勃的创作能力,人类文明很有可能会消散在一潭死水之中。
总的来说,与其他科幻作家相比,从“纯文学”领域跨界而来的李宏伟、王十月在文本中增置了许多哲学观念的表达。无论是王十月在科幻小说中对巫楚文化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入,还是李宏伟在科幻写作中对“纯文学”的穿插、哲学观念的直接表达,它们都丰富了科幻小说的人文内涵与文学韵味,从而在雅与俗的互动中提升了科幻文学的表现力,提供了开拓科幻文学的可能性。
三、跨界写作的可能性
不得不承认,主流文学作家的跨界为科幻小说增添了许多新质。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人文性与哲学思辨性的强化之外,形式上的创新也成了主流作家创新科幻文学的一种路径。在《如果末日无期》中,王十月融入了元小说的元素,让创作者张今我进入文本与故事主体产生对话,从而进行了一场形式上的先锋实验。而在《国王与抒情诗》里,李宏伟除了将抒情诗直接插入到小说的叙事文本,使之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外,在谋篇布局上,李宏伟也颇具新意。“本事”一章作为文本的主体,讲述发生在国王、宇文往户、黎普雷之间的故事。“提纲”一章在形式上恍若抒情散文诗,抑或是意识流主导下的呢喃。在内容上,它应算得上是“本事”的注脚,昭示着在抒情性取消之后人类未来的书写方式与表达方式。而“附录”一章中的几个小故事虽游离于主线之外,但又为主线故事而服务,召唤着有关未来的可能性。李宏伟、王十月对科幻小说所进行的“先锋”文学形式在创新科幻文学整体风貌的同时,也为科幻小说赋予了更多个人化的特色。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内,科幻文学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不为主流所接纳。其主要原因是,主流文学认为科幻文学只流于对未来虚幻世界的臆想,缺乏现实立足点以及文学所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然而李宏伟、王十月的“未来现实主义”式的文学创作将科幻的视点拉回到“近地端”,他们所描写的并非离现实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在不久后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未来。应该说,《如果末日无期》《暗经验》《国王与抒情诗》等篇章所“呈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共享了一个支点,同时又与现实世界构成了锐角或钝角关系”。他们将科幻拉回到对科技未来批判性思考的维度,从而使得文本所要展现的不是未来的科技图腾,也不是在未来科技加持下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向。他们所关心的是科技变革之下的人的主体性、个体自由等问题,此外,“他们在纸上进行的社会实验告诉读者,健康社会制度的缺失会让技术带来毁灭性的社会灾难,人类文明的偏狭发育将会把人带入黑暗的深渊,如果没有一个能承认和保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社会运行机制,如果社会没有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和保护普通个体的共识,历代人文主义者所努力构建和追求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能会在这样的技术浩劫中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人将变成毫无还手之力的极权主义者的仆人和奴隶。在他们看来,需要约束和警惕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李宏伟、王十月的科幻文学写作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基调,满溢着对社会现实以及科技变革之下的人的关切。他们的写作无意于概念的建构、未来科幻图景的绚烂展演,他们将科幻当作一种表达他们人文理想与人性关怀的理想容器,从而肆意放飞想象的翅膀,进行着多种多样的科幻实验。
当作家无限拉近了科学幻想的时间点,虽然能在“近地端”畅谈“未来现实主义”,但这种过近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科幻文学本身的魅力,从而使得李宏伟、王十月的科幻文学作品显得创新性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科技感的缺乏上。在《如果末日无期》中,除了元世界、子世界、○世界的设定还颇具新意外,其他几章中的故事背景都显得较为老套。例如,《我心永恒》中扫地机器人的“人化”,《莫比乌斯时间带》中的“蜂巢思维矩阵”,《胜利日》中的MC病毒以及《如果末日无期》中的永生机器人技术。这些未来设定在其他科幻文学作品中已经广泛提及,甚至其他作品中对这些技术的展现更为绚烂多姿。再如,《国王与抒情诗》中作为“帝国文化”统治机器的意识共同体、移动灵魂与意识共同体,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下的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未来科技的“现实化”使得主流作家的科幻作品很难在未来想象中占据优势,从而使得科幻文学徒有其形而不具其神,因而很难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此而言,主流文学作家要想在跨界实验中实现跨越与突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科学幻想的创新。对于主流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大多出身于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不仅科学知识相对匮乏,也缺乏一些对科学原理以及前沿科学动态的关注,然而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捕捉大多来自对其他科幻文学、科普作品的阅读,所以很难真正进入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中。因此,对于像李宏伟、王十月这样的跨界作家来说,要想创新自身的科幻文学创作,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零开始,深入了解科学知识、学习科学原理,持续关注当下的前沿科技以及未来科技的发展动态。唯此,他们才能真正地将科幻文学纳为己用,创作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科幻文学作品。
当主流作家跨界科幻进行“未来现实主义”式的哲思时,他们将笔力过多地用于观念的传达以及哲理的阐释,反而忽略了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最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读罢《如果末日无期》,读者很容易在时空的跨界中绕晕在人物不同身份的转换中,然而掩卷细思,除了能记住几个主人公的名字外,很难总结出某一人物的典型特征。不仅王十月是这样,李宏伟在《暗经验》《国王与抒情诗》等作品中也没能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他们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中,人物仿佛变成了串联故事情节、推进故事发展的工具。其实对中国科幻文学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是其短板。主流作家的进入本应能带来新鲜空气,为科幻文学塑造典型人物提供新动力。然而李宏伟、王十月在进入科幻文学领域后,为了凸显其价值关怀放弃了他们本来最具优势的人物塑造,从而降低了其科幻文学写作应有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忽视人物形象塑造的弊病也存在其他跨界作家身上。所以,要想创新科幻文学的新面貌,这些作家有必要重新思考科幻文学的写作方式,注重在展现面对科技发展的人文哲思的同时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科幻文学曾作为严肃文学用以探讨民族国家的未来,然而到了当代,在新的学科体制之下,科幻文学被划分到通俗文学的领域,成为与“纯文学”领域之外的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坛也鲜有“纯文学”作家跨界从事类型文学写作的。从话语权力的场域关系来看,“纯文学”对科幻文学长期存有一种偏见与傲慢,这使得科幻文学好像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李宏伟、王十月的跨界写作却提供了“纯文学”与科幻文学交相融合的一种可能性,即使目前这种雅与俗的互动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着锐意探索精神的文学实验者将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
注释:
①③凌逾:《赛博与实存的跨界太极——论王十月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②电视节目中的“跨界表演”既是跨界的文化表征,也是跨界热潮的有力证据。电视节目中的跨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节目内部存有跨界的元素,如《爸爸去哪儿》《极限挑战》《挑战者联盟》《我们来了》等;一是节目本身即是跨界表演,如《跨界歌王》《跨界喜剧王》《喜剧总动员》《十二道锋味》《舞林大会》等。
④郑军:《科幻文学的三大类型》,https://net.blogchina.com/blog/article/821975173。
⑤王峰:《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三种时间想象与当代社会焦虑》,《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⑥虽然王十月并未以“未来现实主义”指称李宏伟的科幻文学写作,但从李宏伟科幻创作所展现出来的特点来看,“未来现实主义”也可以用来标识他近期的科幻文学作品。
⑦⑨⑩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8页。
⑧王十月、杨袭: 《对话王十月: 我写的是万年孤独》,《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9月7日。
⑪王鹏程:《生活与存在的精致寓言——读李宏伟的〈暗经验〉》,《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1期。
⑫唐媛媛:《一部“软硬兼济”的科幻作品——论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⑬参见岳雯,陈凯,周明全,张维阳,汪雨萌,王晶晶:《“先锋”一种:科幻与现实》,《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⑭刘诗宇:《文学或科学 生存与毁灭————评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文艺论坛》2020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0AZW015)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的‘启蒙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0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蒋洪利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