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抵达极限之境的击打力
——凸凹诗歌评析
文/陈啊妮
在反复阅读凸凹的诗歌后,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他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吗?简单化地将一个著名诗人归类,恐怕是不太严谨的,但他诗歌厚重而硬朗的在场感和抵达感,那种击打人心的力度,又一再加持我的这一印象。凸凹是做到了用真心和生命写诗的,我设想,如果他不写诗,也可能会借助其他文字体裁去抒发他的情绪和情感的(事实上他也是著名小说家),但恰好“发现”了诗歌,瞬间他和诗歌语言的对视和唇语,两者皆被照亮,乃至点燃。他的每一首诗,让我感觉都不是一时兴起写就的,哪怕是很平凡如“牙膏皮”那件事,如此生活中的小件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悲喜与辛酸,它就像平常的一张废纸,上面却留有他惊颤式体验的文字。抑或我们可以从诗歌的抒情性方面来讨论,可以说凸凹的诗,不是纯粹的叙述体,更不是浅显的抒情体,他的诗是流动的,跳动的,但流动的不是水花,跳动的也不是火焰。外象沉静的内部,是激越和焦黄,这是我们能体味到的,即他用生命体验生命,用呼吸体验呼吸,用心跳体验心跳。由此,可以下结论的是:他是真写诗,写真诗,他的诗没有丝毫的跟风造作之嫌,也不是图消遣,或发泄,而是有一种历史责任感,时代鼓点的催使,或语言之魔附着于身的灵光乍现和诸多机缘巧合的投射,总之,他的诗彰显时代,拒绝颓废,内质沉实,情感丰盈。
我阅读了凸凹自1986年以来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总体观感,他的情绪一如既往的沉静,绝少因激奋而产生嘶哑式的破音,他诗歌的语言叙述方式,不拘一格,乃至他的“变化”也不是呈线性规律的,你会发现也有不同风格间的横跳,但又不是徘徊式的,他始终在追求“抵达”一种“极限之境”,即用最少的字,最佳的节律感,最能呈现表达空间的构筑。
所以,我们从凸凹大量的诗歌中,没有那种“重复感”。一种情绪或发现,他说过了,写成诗了,就让这首诗成为一个坐标,就如一棵树占据了森林中的一个位置,而且每一棵树形态各异。当然某种体察,可能会有分期式递进的表达,但总体上他的诗,没有形成自我的“诗歌词典”,诗中的意象或细节也都是唯一的,他是他自己的“瓦解”和“重建”。这可能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相关,他没有如很多诗人那般因各自相对固定的生存空间的影响,而将自己“定位”于某一区域,从而形成自己“取之不竭”的题材库或精神王国。
凸凹的精神世界是缤纷万象的,或光怪陆离的,也是迁移、流转与幻变中的,也许这也是他的每一首诗都能让人为之惊艳,每一个句子都像是第一次读到的原因。当然我这么说,并非否认凸凹诗歌毫无个人风格,他的“个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体现诗歌精神境界的无限拓进和语言的精确“狠劲”上,当然由此去辨识他的诗歌,又有些困难,因为他是不确定的。
比如他的《天上的人》组诗中,写给若干诗人、名人或亲人的,除了人物的不同,每一首诗的叙述方式,也都是“量身定制”的,不由得不令人叹服,无可否认的,是诗人想把每一个悼念中的人“写活”,他做到了。如写给诗人傅天琳的《柠檬黄了》,他就写了“柠檬”:“最酸的黄/最香的黄/最美的黄/最诚实的黄/——最好的黄”,浓缩于柠檬,并聚焦于柠檬的“黄”,多么纯粹的立意和抵达!写给袁隆平的诗《放牧诗》,如歌如泣,层层推进延展,自成的陡峭、拐弯和圆润:“水稻的共和国/你发明了亚当,又发明了夏娃/一粒水稻的开天劈地/一茬一茬过来,一茬一茬过去/你的一直在增加又/总比水稻少一粒的同类/在来去之间,有了来去”,这首诗有奇突的抵达人心的力,那么锐利,又那么舒心。
我认为,凸凹完成一首诗歌,也完成了他自己,但还不一定令他满意,他追求的是更接近边界的抵达,而非某种完整性。那么,请问他抵达了吗?从读者这里看,他已抵达,但诗人或许仍心有不甘。
凸凹诗歌切入的角度“刁钻”而精准,有点狠,但又不失雅致和风度,同时推进得稳妥而细腻,可靠又神奇,并将诗一步步推向高远。他诗歌的切入点一开始并不总让人惊叹,但随着文字的推进,你会惊呼妙哉。
如《最怕》这首诗,写的是男女朦胧初恋的情节:“最怕和哥在山上/在山上也无妨/最怕飘来偏东雨/飘来偏东雨也无妨/最怕附近有岩洞/附近有岩洞也无妨/最怕哥拉妹子钻进去/哥拉妹子钻进去也无妨/最怕燃起一堆柴火/燃起一堆柴火也无妨啊/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他没有写情感的火焰,而是写火烤衣裳,一切合情合理。诗人写母亲的《去火车站,或凌晨接母》,就是一首切入后迅速旋飞的节奏,步步惊心又荒诞,读毕又承认生活就该是这样子的,整首诗一气呵成,由不得读者去作“理性”推断,所以凸凹诗所形成的一种“逻辑”或“气场”,又有些摄人心魄而迷人。
我注意到诗人很注重于诗歌的“头三句”的力量,力求一下就“逮”住你,而且一首诗的“起跑”决定了后续的旋转速度和力度,既能让整首诗的气息贯穿始终,又保持着自然开合的姿态:“凌晨五时,母亲,我来了,站在你面前/你看见的,不是北站夜灯的眩影,不是/三分之一:这会儿,母亲,我是你全部——/全部的小,全部的大……”再如《母说,或家史》,一上来就是:“外爷,一支从未谋面的枪/响了整整一下午,打死的/是外爷自己。”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往下读,而“陷”得越深,但诗歌语言的自然散裂,并非一种刻意的埋设或“引人上钩”,他始终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幻化的是语言,由语言自身的开阔性与自由飞行和碰撞,如宇空,才能产生真正的光亮或深渊,还是这首诗,当我读到:“欧洲自行车外圈/五十年代革命路,左右卷舌,莫名打漩/耳朵问题是一辈子的问题,声音的胆子/在耳障中闪电、打雷、转弯,成为/高调与危塔”时,感到母亲及至亲的切肤况味是具体的,也是真实的,同时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或人类之痛,因而凸凹诗歌切开的是一个“入口”,而后续的递进与打开,方能呈现人与存在更大的格局。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凸凹总是精心地将小人物和小事件,构成时代的“微雕”,从细微处体托出大格局——无非是诗歌语言实践中,具体与抽象,局部与天下,个人与群体,现实与虚幻间,对诗人事关命运和生命的关注和释解力的考验。正如这首诗中的“家史”,也是“民族史”或“人类史”,这首诗也会超越时代,对更远阔的时空负责,如诗的结尾:“中间一直是中间/爱情、操心、跳塘未遂”。再如《蚯蚓之舞》,更是“以小搏大”的范例,蚯蚓可算是天下最柔弱细小的生命体了,但它也能“惊天动地”,首先我得叹服诗人的“选材”,二是他选定的生活中“排它”的力,三是蚯蚓的格局折射出的生命关怀:“蚯蚓的舞/排开土、排开大地蚯蚓的舞/排开地狱,和亡灵为了这天塌地陷的柔柔的一舞/蚯蚓把体内的骨头也排了出去”。
读凸凹诗的时候,时常也会想到他的一首诗在内心的酝酿过程,是否也会有一个预设的高度和辽阔?答案应是否定的。正如前述,他有话要说,恰好想起了诗歌,并无靠一首诗的面世给自身增值的打算,如他的题材,非常宽泛,了无计划,仿佛存乎于机缘。我想问:他写诗时,会不会忘了自己正在写诗呢?诗人在创作时,不可能太清醒,也不会太昏沉,而是一种“忘乎所以”和浑沌“狂放”,并无清晰的“功利心”。他内心要抵达的,服从于一腔情绪和浑然天成的语言功力,而这也是不自觉的;正是这种“不自觉”,读者也才能不自觉被一首诗所惊魂摄魄。比如在读《沱江十七行》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恰如一江之水的翻滚和浑浊,水里的影子和浪花的喧响。诗人遇山水而想起家国和父母,并非志气崇高,而是一个文人,在那一刻自然的心跳和呼吸。我想,如果禀持的不是“平常心”,那么一首诗的功效就不是完成自己,而是成就另一番事业,就偏移诗歌之魂了。诗中的“听过太多的声音/最好听的,是母亲的声音/从未见过外爷、外婆/夜深人静,我在声音里看见了他们//他们,还有卵石和鱼/一声不吭,在声音里咚咚走动/河水分走两岸,向山上爬去”,这样的句子,甚至连写好了会发表于某刊也不会想的。
凸凹的诗歌,因其纯粹和“真”,已然成为对文本高度自治的诗人,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认为,这种与诗歌“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是对诗歌的敬畏和尊重。再来看《大河》这首诗,大河是无名的,也是抽象的,甚至写的也不是“水”,而是“血”,我相信诗人写这首诗时,肯定没有被一条具体的河流感动,而是生活中的另一条河,横亘于面前,身在其中,随波逐流,但诗人并不想刻意“抬高”这条河,或歌赞,或诅咒,只能接受它,害怕它,又摆脱不了它——因为它就是命运自身,谁能跳脱开呢?
诗中写道:“这条大河,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还到不到哪里去。而那个黄昏的场景/不仅在夜晚,甚至白天,都会不时出现/仿佛一个梦魇,一种幻象,大得不流动/只有那水的声音,日夜轰鸣、咆哮、让我惊怵”,或许有读者会认为这首诗的荒诞不经,但我认为:他写了最真的“真实”,只不过他用了最简单的体验和认知,最自然的呼吸和良心。
要说一说凸凹诗歌细节或意象的力量。叙述需要有质量的情境和细节,是客观的,但又应是精心挑选的。虚假的或夸张的,过于抒情的并被赋予主观定性的细节,一定是无效的。细节即诗歌的内核,因细节和意象的生动,可以省却“抒情”,由读者自己去作出不尽相同的体味。凸凹诗歌中的细节,仅仅是坦陈,哪怕有些“欲言又止”,但绝对实在。他所叙述的人和事,很平常,但却构勒出人性化的活剧。
诗人写患病的父亲的《送行诗》,没有大呼小叫和涕泪滂沱,却撼人心扉,靠的也是由细节所架构的意象的闪烁。诗中对父亲形象的刻画,是具体的,又是诗性的:“一闪而过的风,刀子样/将窗外的物事割脱了形/像细胞、化疗,将一个人的尊严/打成鬼,又打成人——就是不打成/我少年镜中的原形”,诗人在表达一种真实,还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诚恳,或文学性的自我观照。
诗歌中的细节或意象可能有所指涉,也可能是人生经验中的痛苦或梦想,但有必要将之变形,更有感染力和思考力,或赋予平凡的细节以灵魂。
凸凹作为一个诗人,一边潜心于专业创作,一边理解生活,同时用诗歌将他捕获的经验进行提纯和分类,使之具备了寓言化的效果——包括那些读起来显得荒诞的情节。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一窥诗人既平凡又独特的人生历炼,比如曾在国家“大三线”十几年的工作,使他比大多数人多出另类神秘体验,必然也会影响到诗中细节的表达,一种“变形”后的不同时空并现交叠的意象呈现,但真实仍是它们的“底料”。
历史、现实、冷静表象下的焦虑和预感,是凸凹诗歌细节排布的主要方式,如《钉子与墙》这首诗,布景极简,但喻意深刻,细节只有一面墙和无数的钉子,至为关键的是:诗人的不信邪和墙面就是钉不了钉子的现实:“我相信/仅仅是为了叫我相信/这面墙才让所有的钉子弯曲”,我无意推导这首诗的指涉,越简单的诗往往越缺乏明确的答案,反而可能是永久的疑惑和追问,这首诗类似于哲学质询式的探险,但它又不是哲学诗。
从这首诗看,当“我”举起第一枚钉子时,应是满怀快乐遐想的,从第N颗钉子开始,直至最后一颗,诗人的心态是纯粹的,即相信总会有一颗会钉上去,遗憾的是一颗也钉不了——细节和意象虽简单,或重复,但每一颗钉子弯曲的过程,难道不是一种思考力的递进吗?诗的开头与结尾的有关系,也没有太大关系,是“我”的思考被织入其中,并一步步如花朵最后绽放。凸凹诗的意象组合,经常以一个怪异的现象开头,然后由此顺藤摸瓜般取得奇异之果,或他是用心灵的体验布下的“迷魂阵”。我很少从他诗中读到忧郁无助的句子,即便是惊惧,也坦然承认并接受,然后很快回归于镇定;他的诗中也极少青春般骚动不安的词,即便是很早期的诗,也已显示豁达式的大气和“无所谓”,仿佛早已对人生日常和注定命运有了认识;他很多诗中有一种“缓慢”跳动的节奏,指向明确的末来,或回归源头,而当下尚在雾中,如《石达开之死,或凌迟的东大街》,那一刀接一刀,共“一百多刀的时间/打开秘宫,又被拖进更大的/秘宫”,这个“秘宫”是不可测的,只是最后的一块活肉落下才会见分晓——又是可测的,再如《我》这首诗,“我”有多面性,存在各种可能,偶然一点推力或拉力,或谁多事戳破某一层纸,“我”就是另一个样子,诗中的“我”,也可能是“我们”,只不过凸凹坦然陈述而其他人心怀惴惴,但我更相信诗中的某些细节,同时发生在凸凹身上的可靠性,这实际上也是他慢慢长大、老去的一个过程,每一步都有未知难测,每一天都同时身驭生与死,这首诗的结尾实际回归人类的源头:“如果把体内的那些个我喊出来/世界就成了汪洋/如果把体内的那些个女人喊出来/我就成了全人类”。
不可忽视凸凹诗歌独特的精神气息是其主要的辨识路径。
凸凹是有“脾气”的,或有态度的,但这一点并非每一个诗人都做得到,或意识得到。要命的是,这种气息的生成大体与生活中的诗人是同一的,而不能出现两种气质。
说到这儿,几乎可以肯定,诗歌的“个性”源自诗人的天性或人生炼狱后的磨难,装是装不出来的。很多读者在读凸凹的时候,很容易被诗中的“狠劲”和愤愤然所感染,但我感觉凸凹的诗与那些被愤怒情绪所统摄的诗人,是完全或根本不同的。凸凹诗歌中的“愤懑”几乎介乎于澄明透彻和郁积牵虑之间,诗人骨血里的正直、仗义和善良,也都是同步展现于精神层面,他的诗有一种“霸气”,并不霸道,源于他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和一种大格局的追求,或他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执拗和坚执,他的“冲动”方式就是“放任”语言的突围,力求从被称之为日常的生活中,剔出多出来的部分,再加以追根溯源,责任与使命的担负与预设——我在想,诗人面对的也许是一块坚石顽壁,他能怎么样呢?当然最终他建立了自我诗歌情感的可靠,以及文本的价值,这就够了。
正如诗歌《我》中写的:“记得在心纸上写过反标,又撕碎,点火焚去”,生活于那个年代的少年诗人,大多都干过这种事,与诗人成年后乃至老去后所表现的,都属于一种情况:在诗歌中取得胜利,或妥协,绝不是哀伤。《一列火车可以打多少把菜刀诗》是凸凹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对这首诗太过随意或太浅显的解读,都可能误读诗人。把一列火车和菜刀并列于诗,这本身就如螺丝钉炒大白菜,极难相牵连,更难出诗意,问题却在于上火车不能携刀的规定,引发了诗人的思考:菜刀可以切人,而人也可以伤人——这首诗最关键的还不是菜刀,而是“坐在火车上,又突然有一种感觉/那是坐在刀鞘中的安泰”,即每个人只要时机成熟,都可能是一把刀,混迹并为害于人间。诗人在此表达的,是对社会现象的忧虑,但凝聚在一把菜刀上,或破旧的火车皮可以打成多少把菜刀上,却是一道难解之题。
凸凹对诗歌本身的看法,有更系统的论述,然而在他的一首诗《诗论》中写到:“每行诗都是一条鞭子打人/好的诗只一鞭顶多三鞭就解决问题/问题是读者的七寸大多长在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首诗中能参透出诗人的什么气息呢?这缘自诗人对自我内心的辨别和对读者投射力的关注,强大的自信和定力,以及个体写作主张的坚持,做自我统摄的“王”,这既是诗人的“野心”,也是一个大诗人必备的素质——如汤养宗所言:“一个诗人的写作指认就是自己的美学范畴”,同时凸凹期待“一鞭子”、“顶多三鞭”解决问题,既是一种美学追求,也是诗性需求,即击打力的精准和简约,但这是很难做到的,问题就在于读者的“七寸”变化莫测,或如神授般的击打力,可遇而不可求,如命中十环的靶心,是来回多次晃动的结果,所幸多是来自运气,而非实力或勤奋。所以凸凹的这三句诗的“诗论”,确实道出了一个成熟诗人的追求和困厄,就这首诗而言,他已成功,击中天下诗人的痛点。凸凹作为我敬重的前辈诗人,他的很多诗章深深“打击”了我,而且是一鞭子,至多三鞭子令我拍案叫绝,期待他持续发力,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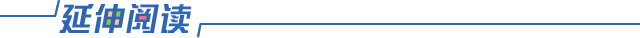
凸凹诗歌代表作选
◎爸爸的果园
爸爸,你一个喷嚏
果树
就开了花
爸爸,你一声咳嗽
果子
就落了地
爸爸,你一次哈欠
果园
就隆起了一堆土
1988.9
◎最怕
最怕和哥在山上
在山上也无妨
最怕飘来偏东雨
飘来偏东雨也无妨
最怕附近有岩洞
附近有岩洞也无妨
最怕哥拉妹子钻进去
哥拉妹子钻进去也无妨
最怕燃起一堆柴火
燃起一堆柴火也无妨啊
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
1988.11
◎钉子与墙
我在墙上钉钉子
可是,钉一颗弯一颗
始终钉不进去
“我不相信!”
我这样对自己说
并搜罗完家中所有钉子
直到把最后一颗钉弯
我相信
仅仅是为了叫我相信
这面墙才让所有的钉子弯曲
1998.9.11
◎大河
一条大河,横亘在面前,大得不流动。
整个世界,除了天空、夕阳,就是大河。
尤利西斯漂泊十年也没见过它的样子。
没有岸,水草,鱼歌,年月,蚂蝗,和蝶尘。
我甚至也是这条河的一部分。
对于这条大河,我不能增加,删节,制止,划割。
或者推波助澜,掀起一小截尾部的鱼摆。
夕阳倾泻下来,没有限度地进入我的体内。
无数条血管像无数条江流涨破中年的骨肉。
仿佛恐龙灭绝时代的那场火灾、那场大血。
布满整条大河,地球,这个黄昏的呼吸。
又仿佛混沌初开,分不清
天在哪里,地在哪里,水在哪里,血在哪里。
我见过河南的黄河,重庆的长江,青岛的海。
还见过川东地区山洪暴发的样子。
它们都没有那么大,那么红。
并且,早已先后离开我的生活,远去了。
我所在的龙泉驿没有河,因此缺少直接的联想。
现在,除了在阅读中碰见,已很难再记起它们。
这条大河,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还到不到哪里去。而那个黄昏的场景,
不仅在夜晚,甚至白天,都会不时出现。
仿佛一个梦魇,一种幻象,大得不流动。
只有那水的声音,日夜轰鸣、咆哮、让我惊怵。
2001.1.12
◎去火车站,或凌晨接母
东莞至成都的火车,经过大巴山时
一阵风,铁轨的风,裹挟了你。整个晚上,你
都在用火车的速度,想啥呢?七十五岁
怎么着,也退不回去了。即使火车倒退
还能倒回内江,你的女中时代?
理想的浪漫,就算抵不了现实的残酷
我也要被你掀起的速度,与火车的速度
两两相冲,让你能安静地睡会儿——最多
在梦中,想想离世的丈夫,和三个健在的
儿子,正如我在龙泉驿的梦中,想到你——
想到你在旺盛之龄,完成的生命
分解:我是一个你,二弟是一个你
三弟是一个你。你把自己三等分
让每一等分自由奔走,顾此失彼。这是
凌晨五时,母亲,我来了,站在你面前
你看见的,不是北站夜灯的眩影,不是
三分之一:这会儿,母亲,我是你全部——
全部的小,全部的大……
脱口而出的沉默,你无一不懂
2008.7.27
◎蚯蚓之舞
鸟的舞
排开雾
鱼的舞
排开水
人的舞
排开人
没有比蚯蚓
更困难的了
蚯蚓的舞
排开土、排开大地
蚯蚓的舞
排开地狱,和亡灵
为了这天塌地陷的柔柔的一舞
蚯蚓把体内的骨头也排了出去
2015.6.4
◎诗论
每行诗都是一条鞭子打人
好的诗只一鞭顶多三鞭就解决问题
问题是读者的七寸大多长在鞭长莫及的地方
2015.7.9
◎送行诗
一月两次赴渝。高铁很快一一
快过了一个人的生命,又很慢
一一慢过了我捂咳不出的悲伤。
一闪而过的风,刀子样
将窗外的物事割脱了形
像细胞、化疗,将一个人的尊严
打成鬼,又打成人一一就是不打成
我少年镜中的原形。死亡
从牙痛开始,在入冬的海南起火
在一个人的身体里
标注逗号、句号。这个人居重庆
是我幺爸,叫魏堂阶。
这个人的堂子里,牵连着满满的金玉
而我,正是玉的儿子。现在
堂子没了,整个重庆的气场全散了
一一江雾怎么忙碌,都是虚构。
2019.1.15-22
◎清明诗
清明是一座山
我们在向阳的一面进入阴历
我们摆酒,上香,下淅淅小雨
对着一堆土,细捻亲人的慈良、清明和伟大
清明这座山上
我们在背阴的一面进入阳历
我们喝酒,纵歌,拼舞
用郊外的踏青,为春天开光
这座叫清明的山
多少年了,不亏不盈,不悲不喜
笑声只与泪水持平
生死只与大地相当
2019.10
◎那么多草原诗
那么多草原。那么多草原的辽阔
没有哪个,躲避得了
一把刀的干旱、狭窄。即便脾气钝得
葳蕤一样麻木、天边一般模糊
也吃不住一把刀的锋利与
风头。那么多草原,冲在最前边
断在最后面,还是保护不了
自己的牛羊,那奔跑的国土。那么多
高高大大的牛羊
伏得比冬草比大地的恐惧还低,依然被风——
刀子的耳目,一望天际发现
有一天,我看见了看不见的地方
看见牛羊的筋骨和风的膘肉
在刀子的血槽里运动、喊天
变成攥握刀子的手。看见
刀子以反走、疾退的方式
步步逼近,深入草原心脏
连刀柄都陷了进去
2020.9.14
◎一列火车可以打多少把菜刀诗
一列退役的绿皮火车
可以打多少把菜刀?一把菜刀
有永远切不完的菜蔬、动物、砧板
和日子。永远磨不尽的铁。有
锋利、闪光——却从来没有
最锋利、最闪光。一把菜刀
除了切切不完的工作、责任和约定
还可以切割其他一些物事
——这是它的副业。但有时
让它一夜成名的,把闪光变成寒光
寒光变成闪光的
让它抵达一生中最锋利的高光时刻
罪恶时刻的,恰恰是它的副业
这种认识,我也是这几年
才具备的。看见菜刀
过不了火车的安检
我会突然想到什么,心头一阵紧缩
随后又松弛下来。混迹乘客队伍
一步不落,坦然过关
坐在火车上,又突然有一种感觉
那是坐在刀鞘中的安泰
2020.9.14
◎纸上游泳诗
这些年,一直在游泳
把赘肉、失眠、腰颈椎,一些问题
一些光阴,投放在
成都东山一池恒温的水中
今天,周一,泳池换水清场,我决定
在纸上游。选择的是
人少、最好无人的泳道。一个来回五十米
蛙泳二十个,仰泳一个
蝶泳和自由泳,一个来,一个回
一生的粮食,与一千一百米
形成时空共和国最精良的生命等式
多年了,一直这样
用搭上老命的体能保持一种大姿态
用四种不同的小姿态,虚构
跟上时代的步伐与荣光
此刻,经验的身体,一会儿纸的正面
一会儿纸的背面,更多的时候
藏在纸的囚室憋着,忍气吞声
然后浮出水面,像什么也没发生
运气还好,就在我游不下去
险些成为沉没的葬词,一尾美人鱼
从字里行间游来
贴身超过我,出现在正前方
我紧紧跟随,十米后,放慢速度
任她消失于防水镜的迷雾
不管此种光景是一剂良药,还是一涡陷阱
多年了,总这样。总这样吗——
纸张泳道有纸张泳道的真理
发生学的笔画,不会一成不变?
每个泳者心里都清楚这个狗屁真理——
他们清楚地在水中瞎折腾
2020.9.18-19
◎沱江十七行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座山
一座叫家,一座叫国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条河
一条叫父亲,一条叫母亲
我的母亲河
有一匹马的长度,一颗星的宽度
沱江是她胳膊肘向内拐的名字
我的母亲生在那里
离开水边七十多年了
一出口,就是沱江的声音
听过太多的声音
最好听的,是母亲的声音
从未见过外爷、外婆
夜深人静,我在声音里看见了他们
他们,还有卵石和鱼
一声不吭,在声音里咚咚走动
河水分走两岸,向山上爬去
2022.7.14
◎在儋州
在儋州
所有的味道姓苏
所有的方位叫东
所有的朝圣之路称坡
在儋州
所有的课本出自苏门
所有的药引面向东方
所有的稼穑一律种在坡上
这是一个比岛屿更热的名字
所有的海啸都在低声唤魂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2023.1.14儋州
◎兴隆湖遇水杉
这个冬天,最美的湖
是红色倒影出来的。这个冬天
最动人的红,是水杉给定的。用
初红的陈香,为水杉划桨
是乌桕为姐妹的新年
做的一个好梦
我看见,一些湖风从针叶的篦子穿过
一些时光穿针引线。掉落的部分
被一张阔叶接住
反飞成站满水杉的鸟鸣
我看见,冬水与植物
正用化石,换算古老
2024.1.11
(本文刊于《诗潮》杂志2024年第10期)

凸凹,本名魏平。出版有长篇小说《甑子场》《大三线》《汤汤水命》《安生》,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长诗《水房子》,散文随笔集《花蕊中的古驿》,批评札记《字篓里的词屑》等20余种图书。

陈啊妮,作品在《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潮》《诗歌月刊》《诗林》《延河》等百余家期刊发表并入选多部选本。评论入围第六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第二届《油脉文学》理论评论提名奖。著《与亲书》(合集)。居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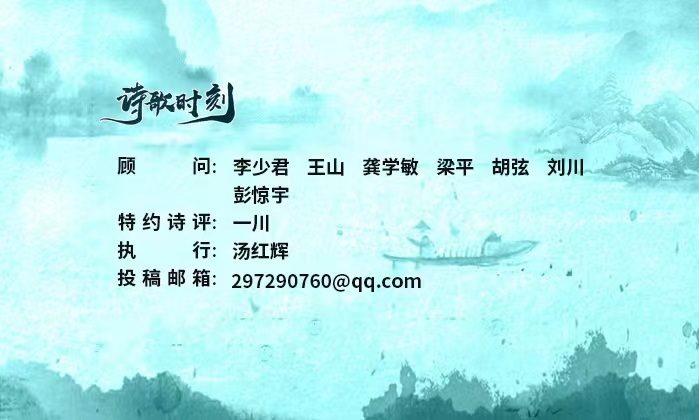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陈啊妮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