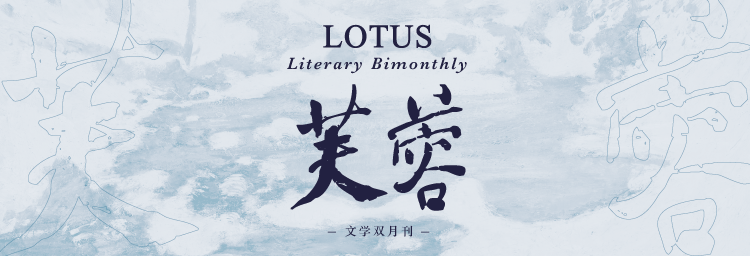

他们眼中蔡公君谟的世界
文/李晓君
因为书写是自一种不可观看(不是面对面,不是一上来就促成视觉,而是促成写与画的行动)的后退和开叉进行的,它将支撑物分成几个通道,好像是要提示出完成书写的这个复数的空无——书写就是脱离表面,在表面上编织。
——菲利普·索莱尔斯《论物质主义》
葛清源
我初见他时,他从栖身的悟空寺前来我家探望弟弟。时节已入冬,江阴的天气时阴时晴。那日冬阳甚好,仿佛搭好戏台,等待一幕才子佳人的戏上演。大凡这样的戏,以悲情为主,即便大团圆的结局也少不了过程中的几多坎坷悲催。不如此便不足以催人泪下。他一身单薄青衫,手持书卷,眉眼间有一股清气,算得上一个俊雅的书生。他孤鹤般形只影单,寒门的气息镌刻在他深沉的眼眸中,与富贵之家子弟身上那种骄矜、轻慢的神情相去甚远。
佛家讲因果。我想,我与君谟的姻缘定是修了多少辈的福德。此前,我约略在闺房听见姐夫凌景阳与父亲说起过这个名字。那是姐夫宦游在外,赴任新职途经江阴,探望父亲闲聊时说起的。他提起这个人的语气就像陈述一件精金美玉,或是描绘一幅美妙的书画,抑或演绎一支超凡脱俗的琴曲。
庭院游廊,冬阳切割出金黄和暗紫的色块、灰白的窟窿石、葱绿的冬青和篆隶般古意的红梅,以及庭院中一个难得一见的年轻书生的背影——无不使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生出几许萌动的情怀。我无法预知与他之间会发生什么,只是内心欢喜同时慌乱。我隐隐感到一个命定的缘分劈面而来,更害怕失去它。
后来读到他写于发蒙时期的诗歌,忍俊不禁,又暗自赞叹:
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
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
我仿佛能够看见他在遥远的福建惠安,与年龄相仿辈分不同的舅舅,一起欢喜地在伏虎岩寺开授教馆的外公指导下,启蒙读书的情景。这个小孩,祖上五代都是务农。自然地,起初谁也没有对他抱有更高的期待。我的公公蔡琇,是个粗通文墨的农民;婆婆卢氏出身书香门第,是个长寿且颇有眼光的女人,她在君谟5岁、弟弟君山3岁时,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将幼小的兄弟俩寄托到惠安娘家,让被称为“惠安名士”的父亲卢仁进行启蒙。
三年后,兄弟俩回到仙游乡序枫亭会心书院就读。
君谟12岁那年,遇到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人物——凌景阳。
时任仙游县尉的他到枫亭办差,目见这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小有文采的兄弟,深为赏识,旋即将他们荐入县学,后又推入郡级学堂,学习“墨义”“帖经”“诗赋”,完成了应试前完整、系统的科目学习。
我朝科举,与唐朝不同,不仅放宽了“工商杂类”不得报考的限制,还打破考生乡土籍贯限定,所谓“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尤其京师开封的府试,面向全国考生开放。
天圣七年(1029),君谟携弟千里徒步北上,参加了开封会试。对于这次考试的成功,同科进士欧阳修这样描述:“公年十八,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君谟,在开封府试拔得头魁。
那是不久前的秋闱。弟弟君山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府试中落第。也许留在京师等待来年春闱费用太高,回到老家仙游又路途甚远。正犹疑之际,姐夫建议兄弟俩到江阴他丈人家备考。这是个不错的折中选择。于是他们来到长江边这座城市。哥哥寄居悟空寺备考,弟弟留在我家学习。家父虽非进士出身,但也是饱学之士,生五男三女,大姐嫁屯田员外郎凌景阳,二姐嫁进士陈玉,我正待字闺中。
姐夫帮人帮到底。君谟赴开封参加府试,绕道芜湖拜会姐夫,请教科考事宜。姐夫特地将君谟所作赋文送三司使晏殊过目。晏殊称赞其赋必为今岁第一。姐夫甚至亲自陪同君谟到开封参加府试。揭榜正如晏公所料——这位14岁以神童昭试,赐进士出身的临川才子果真眼力不凡。
君谟与欧阳永叔一见如故。永叔出自江西庐陵,4岁丧父,母亲“画荻教子”传为美谈,虽家贫却好学。正是共同的身世,让这两个卓异的青年相见之下便在灵魂深处刻下对方身影。同出同叔门下,后来时间证明,他们没有辜负同叔的期待:永叔成为我朝诗文革新的领袖,君谟开宋代“尚意”书风先河,后世虽以“苏黄米蔡”并称宋四家,“蔡”位居末次,但君谟无疑是导路先锋,对后世书法创作影响甚巨。
天圣八年(1030)春闱,君谟通过省试进入殿试,列进士甲科第十名。永叔“连中三元”: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礼部省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解元和省元,但在殿试中被人告发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如主张考试应重策论轻诗赋等,勉强被保住功名,列为第十四名。另一个说法来自晏殊,称永叔殿试未能夺魁是因锋芒太盛,众考官想挫下他的锐气。
姐夫助力君谟中进士后,又努力撮合君谟与我的婚事。在等待吏部铨选的空当,满脸喜气同时又忐忑不安的他,特地来到江阴,一来感谢我家给予的帮助和照顾,二来拜别悟空寺方丈,三是正式向家父求婚。
我和君谟步入新人生的起点。无论如何,我要感激上天的恩赐,能与君谟这个日后注定要写在七闽大地上的才人成为伴侣,是我的幸运。虽然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数次遭遇打击,但仍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欧阳修
谈论君谟的书法,是我最乐见的事。
君谟精于茶,著有《茶录》(不仅是继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茶的重要论著,还是一幅传于书法史的小楷佳作)。范仲淹曾有《采茶歌》流布甚广,君谟指出其诗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存有瑕疵,说茶之绝品贵白,翠绿乃下品,若改成“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岂不更好?范希文服膺。
我不以书名,虽也薄有“超拔流俗,别有一番情趣”的评价,如苏轼称我书法“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欧阳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但我深知,我远非经典的书家。君谟的字如同他的诗文清美端庄。晚唐五代以后,书道颓靡100余年,此间罕有大家出现。囿于视野和师承,君谟年轻时的字虽端庄温厚,但远不能称善。我曾评价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君谟好学,幼时在乡序随处士许怀宗学书,后在江阴葛家也习书不辍。君谟对书法的理解悟性很高,中进士入京后,随着交游的扩大,特别是与苏舜钦兄弟、宋绶等人的交往,书法很快摆脱早年的局限,上升了一个层次。他像一个胃口很杂的饕餮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取法的对象,可以说是转益多师。少年时,曾学周越。说起周越,可是当今书坛一个重要存在,在天圣、景祐年间名重一时。不独君谟,更年轻的黄山谷、米襄阳,都曾拜在他门下。正如天才,总需要一座桥梁来过渡,周越正是前面几个天才人物的桥梁。周越是晚唐至宋百余年书法断层的重建者,真、草、行、隶均有所成就,法度谨严、切中规范,但也有体态娇娆、未能脱俗的弊病,山谷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就曾说:“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君谟从学习当代书家开始,进而上溯晋唐,取法高古,渐渐形成自家温润典雅、自然率真的书风。他以唐代颜真卿为首选学习对象——鲁公书风之所以在宋代兴隆,与“爱其书,兼取其为人”的价值取向相关。颜真卿在宋代衣钵的真正传人是君谟。他学鲁公楷书几可乱真,但又兼取欧阳询、虞世南、徐浩等韵味,同时还吸收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代书家风神,因而有鲁公雄厚但又不失晋人意趣。他开启了从“尚法”向“尚意”书风转变的滥觞。
君谟29岁迁调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有机会接触到皇家所藏历代法帖。此后又有两次受诏,除为秘书丞、知谏院,是著名的“四谏”之一,又进直史馆,同修起居注,与我、梅尧臣等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的书风正是在那时渐趋成熟的。
我与君谟初识,源于天圣八年(1030)开封府试,而我们建立坚实友情的基础,来自他作《四贤一不肖》诗。景祐元年(1034)春,君谟弟君山进士及第,兄弟俩先后中进士,改写了家族五代不仕的历史。君谟结束三年漳州军事判官的初次入职生涯,携弟入京等待铨选。一到京城,就听闻了朝中一场以年轻进士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政治斗争风波。这场争斗在24岁亲政3年的仁宗的裁决下,把青年进士的领袖范仲淹定为“朋党”,贬黜知饶州而结束。正当满朝谏官、御史噤声不言时,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和我先后站出来声援范仲淹,我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斥他是个落井下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小人,没有资格出入朝廷称谏官。我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耳闻目睹此种种现状,君谟义愤难平,当即写了一组五首七言古风诗《四贤一不肖》,并在众士人为我饯别的晚宴上吟唱出来,当时气氛之热烈甚为感人。我不禁感叹:“君谟作诗,道滋打拍,穆之弹琴。壮哉!何其乐也。”
君谟这组诗,无疑是给当事的五个人画像。“四贤”即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我,“一不肖”指高若讷。这组诗一出来,便在京城引起轰动,酒肆、茶楼、旅栈、城墙,到处都在张贴、抄录和传诵。
(节选自2024年第4期《芙蓉》李晓君《他们眼中蔡公君谟的世界》)

李晓君,生于1972年,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散文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多部。
来源:《芙蓉》
作者:李晓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