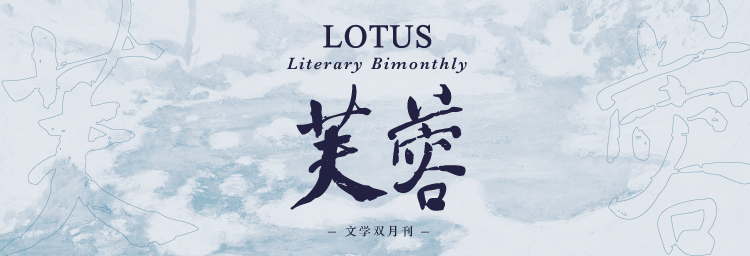

搬家十年
文/钟兆云
时光最是容易把人抛,这一抛,就抛来了搬家十年的日子,而乔迁时的情景犹在昨天。这是到省城后的第三次迁居,也是入住时间最长的一次,前两次安家,都恰好八年。
犹记第一次住上自家的房子不久,儿子呱呱坠地,算是有计划自导自演了“双喜临门”。从乡下进城帮助带娃的父母,跨进这一厅三居室,惊喜的眉目连同轻声地一问,都显得将信将疑。别笑他们没见过世面,其实祖上也曾富过。十三级踏实的石阶,左右两尊石狮把门、占地四五亩的老围屋,显现了昔日的繁荣,伴着父亲讲述的让人回味又辛酸的光阴故事,妥妥地安顿下我的孩提时代。正如好汉不提当年勇那样,炫耀祖上阔过,只会是引人讪笑的阿Q,当然这也不妨碍躬耕之余手不释卷的父亲天马行空想象豪门盛景。参加工作之初,父母见识过我在一间逼仄的小木房蜗居的窘状,清楚在省城安家的难度。我是村里较早进城且有房的人,骨子里又毫无“一阔脸就变”的遗传,对找上门来的乡亲莫不笑脸相迎。所谓的名声,传来传去也就以讹传讹了,连住上了一栋楼的说法都大行其道,哪知晓我不过只取其中一套而栖居。没有电梯,五楼就让父母爬得吃力,何况还有个胖嘟嘟日见斤两的孙子在他们背上或怀里闹腾。眼看父母年岁渐长,上下楼梯常常得分两三次才能完成,我就铆了一股劲在业余时间创作,靠稿费在市中心首付了电梯房,乔迁的黄道吉日还是父亲给选的。身居闹市的当时的高档社区,父母却大有离群索居的孤独感,远不如原先在机关小区来得习惯,出门下楼就可和一众老乡拉近乎、打牌,各家的小屁孩在草坪上一通嬉闹也就打成了一片。如今身居十六层高楼,少了老乡来往,父亲有书籍和电视为伴,倒也慢慢适应,母亲则拘束多了,因为用不来电梯,步行又腿脚不利索,平时不敢单独下楼,除了做家务活,再就是坐在飘窗前等我们下班、等孙子放学。在高楼只住了两年,落叶归根的执念一直在父亲脑海里盘桓不去,老宅子因为高速公路建设拆迁后,新居还未全面装修,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家住上了。父亲八秩那年在睡梦中西行,算是福寿。此后,老病缠身的母亲一年来省城住上一段时间,妻一点也不嫌弃,常说尽孝是为人之根本,生命中有真挚的亲情陪伴,才是最美的画卷。
为了让母亲多接地气,住得舒坦些,我们在市郊实现了别墅梦,依据老人的喜好养上了狗,种了花草树木。内心里也想好了:事不过三,这辈子搬家就此打住。母亲在新房陆陆续续住了七八年,2022年春夏之交回老家后,任凭我们怎么哄劝,她都“故步自封”,苦笑着以一句“没胆量再来”打发。母亲的身子骨确实一年不如一年,背似弯弓,弱不禁风,走平地如履高山,只能撑着拐杖一寸一寸地挪,看得让人鼻酸。母亲自知沉疴难治,担心在省城有个三长两短,拖累我们,就决定在老家“等死”。属牛的她一旦做出决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后来唯一的妥协是坐上了我们买来的轮椅。
九九归一,十全十美,中国人对十这个数字别有感情,乔迁十年总得有个仪式纪念一下。我们早就做好了计划,借此感恩岁月静好、平安顺遂,在小小奢侈一把之后,第二天我就去西安参加一场全国文学界大咖云集的会议。
谁料,当这天来临时,节奏却被猝不及防地打乱了,运行轨道因为母亲住院、可能熬不过两天的消息给带偏了。非但十年小庆不能为继,连西安之行也得取消,“父母在,不远游”,天伦之爱和古贤之言皆不能违背。儿子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奶奶很有感情的他,马上向单位请假,张罗着第一时间回家。当天下午发往老家的高铁已抢不到票,我们只好心急火燎地开车奔赴。妻儿担心我伤心分神,不许我驾驶,我还没上路,就已如鱼离水,肝肠寸断。
(节选自2024年第6期《芙蓉》钟兆云的散文《搬家十年》)

钟兆云,福建省作协副主席。迄今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作品及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刘亚楼上将》《叶飞传》《我的国籍我的血》《海的那头是中国》《奔跑的中国草》等50余部,近2000万字。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首届华侨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参与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广播剧等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
来源:《芙蓉》
作者:钟兆云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