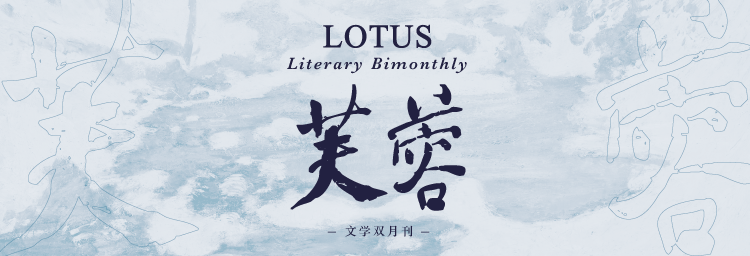

蛮好
文/赵燕飞
中午,正睡得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有些烦躁,以为又是房产中介或银行信贷员的骚扰电话,没好气地抓起身旁的手机,来电显示却是母亲的手机号,心里一咯噔,马上吓清醒了。
近几年,除了在娘家的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有时刚视完频,母亲想起什么事情,又会回拨过来。母亲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没有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一般不会在大中午打我电话。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的眼皮子扑扑乱跳,手机刚接通,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你爸昨天吃晚饭没喝酒,今天吃中饭又没喝酒,问他哪里不舒服,闭口不开,要他去诊所看一下也不肯。”
酒是父亲的命根子,只要没打针没吃抗生素,每天雷打不动两顿酒。父亲又很霸蛮,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上医院。母亲实在拿父亲没办法了,才会打我电话。
我要母亲别急,让父亲接电话。
父亲好像有些不耐烦:“莫信你妈妈的话,我就是脑壳有点疼,不想喝酒。”
“爸!”我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温柔一点,“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老人家的病拖不得,你有哪里不舒服,得马上去医院。”
“晓得呢,我要上厕所了,你和你妈讲。”
我听到母亲在电话的那头数落父亲:“犟,只晓得犟。”
父亲不肯上医院,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我毫无办法,只好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母亲,问问父亲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母亲像个情报员,父亲吃了什么东西喝了几次水上了几趟厕所,一五一十全都告诉我。第二天中午,我再打电话回去,母亲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你爸倒了半杯酒,正喝,没事了没事了。”
母亲连着说了两个“没事了”,我才相信父亲真的没事了。父亲可能感冒了,也可能是颈椎病犯了,还有可能是别的小毛病,扛过来了就好。
父亲不爱说话,是个典型的闷葫芦,和他聊天一点都不好玩,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问两句他也只答一句。
“爸,你是哪一年参的军?”
“一九六五年。”
“在哪儿当兵?”
“广西。”
“你是什么兵种?主要做什么?”我很好奇作为战士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工程兵,修马路。”父亲淡淡地说。
“修马路?你当兵那几年全在修马路吗?”
父亲“嗯”了一声。
“你那些战友还有联系吗?我好像从没见过你的战友。”
“没联系。”
……
父亲从部队退役后,被分到一家国有煤矿,成了采煤工。长年下井的人,大多有颈椎病和风湿病,父亲也不例外。为了去湿气,也为了补身体,父亲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掉那碗由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
甜酒就是母亲自酿的糯米酒,鸡蛋是母亲散养的那群母鸡下的。母亲能够喂鸡,是因为矿里分给我家的房子位于一楼。住一楼有个好处,可以在屋后的空地种点小菜,也可以搭个小棚子之类的,喂点鸡鸭或小兔子。母亲参照邻居的做法,弄了些红砖和木头,建了一个矮矮的鸡栏,喂了十几只鸡。那些鸡所生的蛋,母亲会一个个捡起来,存在一只竹篮子里。每当父亲快下班时,母亲就从竹篮子里摸一个鸡蛋出来,在菜碗的边沿磕一下,将蛋壳掰开一点缝隙,让蛋白和蛋黄都流进菜碗里,又用一根手指在蛋壳里面划一圈,白色表皮连同剩余的蛋白都被母亲抠在菜碗里。母亲手拿筷子,将菜碗里的蛋白和蛋黄搅在一起,直到分不出哪是蛋白哪是蛋黄时,才拎起烧水壶,将刚刚烧开的自来水倒进菜碗里,黄色的蛋液马上变成了好看的蛋花,母亲打开装了甜酒的大罐子,舀了两大勺甜酒放进菜碗里,又拿起筷子搅了好一会,酒香混杂着略带腥气的蛋香,在屋子里四处弥漫。我站在母亲身后,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磕鸡蛋冲开水舀甜酒,又怕母亲听见我吞口水的声音,这时便总会转身走开。鸡蛋只有那么多,除了用来给父亲冲甜酒,还是我家餐桌上的重要荤菜来源。母亲又是那么省吃俭用,我不想让她为难。
父亲喝了几十年甜酒冲鸡蛋,早就腻了。退休之后,父亲再也闻不得甜酒冲鸡蛋的气味,母亲也不劝他逼他了。
我们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喝的其实是烧酒,母亲熬制的烧酒。
当年住在老家周官桥的时候,母亲常熬烧酒,我至今仍记得熬制烧酒的大致流程。母亲将淘洗干净的糯米倒进端坐灶上的蒸锅里,加几大勺水,灶里塞着粗壮的干柴,火苗舔着锅底,蒸锅里飘出诱人的香味。我一直守在灶前,当母亲揭开蒸锅上面的木锅盖时,我赶紧将早已端在手中的饭碗和饭勺递给母亲,母亲一边骂我“好呷婆”,一边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刚出锅的糯米饭又香又黏,不用任何下饭菜,我可以站在灶前一口气吃完一碗。
母亲将糯米饭从蒸锅里端出来,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竹盘里,放一会,再往里面洒一杯凉开水。我拿起饭勺想去拌糯米饭,母亲要我别帮倒忙,我就收了手望着母亲往糯米饭上撒酒曲。母亲将酒曲和糯米饭拌匀后,装进那只褐色的大坛子里,盖好盖子,又在盖子上面压了一床厚棉被。我问母亲糯米饭为什么比我们还怕冷,母亲说这样焐出来的糯米酒更香更甜。
糯米变成了糯米酒,糯米酒要变成烧酒还得熬。母亲熬烧酒时,我喜欢凑在旁边看。糯米是在灶屋的柴火灶上蒸熟的,熬烧酒的大土灶却在屋后。这个土灶比灶屋里那个柴火灶大很多,蒸锅也大很多,旁边还连着一根小管子,小管子的另一头塞在一个塑料酒壶里。母亲将糯米酒倒进大蒸锅里,盖上黄色的木锅盖,锅盖边缘用湿布条塞得严严实实的。母亲不停地往土灶肚子里塞干柴,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蒸锅开始冒热气时,就有透明的酒水沿着那根小管子慢慢往下淌。酒壶里的酒越淌越多,我很想尝几口,母亲却不同意。母亲偶尔会煮甜酒给我们喝,但从不允许我们喝烧酒。我怀疑母亲不是担心我们喝醉,而是因为这些烧酒都要留给父亲拿去矿上喝。母亲不知道,趁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尝过烧酒,那种辣得喉咙要冒烟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父亲回家拿酒的时候,我比母亲还开心。父亲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有时是舍不得嚼碎的糖粒子,有时是嘎嘣脆的炒米糕。有一天,父亲拎回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收录机,惹得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我盼望父亲回家,哪怕他从早到晚没和我说几句话。
我最盼望的,是跟着父亲叉泥鳅。
吃过晚饭,暑热渐渐散去,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蛙声和虫鸣此起彼伏的时候,父亲去找手电筒和木柄铁叉,我连忙提起那只绿色小塑料桶,紧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并不说话,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大步走,我拎了塑料桶小跑着在后面追。稻田里,黑黢黢的禾苗站得直直的,当父亲的手电筒照过去,它们就变成了油亮油亮的深绿色。手电筒的光束不再游移的时候,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果然,父亲高举铁叉,飞快地往稻田里用力一插,又飞快地拔出铁叉,将叉尖伸到我的面前。我听到“吱吱”的呻吟声,只见亮闪闪的铁叉中间卡着一条黑乎乎的泥鳅,它的身子左右扭动着,嘴里吐出白色的泡沫。不用父亲开口,我赶紧把塑料桶放在铁叉下方,将那条可怜的泥鳅从铁叉上面撸进桶子里。
父亲的铁叉扑空时,我会哎呀一声,父亲仍不说话,边往前走边用手电筒去照脚畔的稻田。运气好的时候,只须转完两三丘稻田,我手里的塑料桶差不多就能装满。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提着桶子,很想大声唱几首歌,可父亲一句话都不说,腰板挺得比禾苗还直,我也只好一句话都不说,认真盯着脚下的路。有一回,快走到家门口了,我却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里的塑料桶倒在我身旁,大大小小的泥鳅在我眼皮子底下摇头摆尾,我急忙爬起来捉泥鳅。父亲还是不说话,蹲下来和我一起捉泥鳅。
叉回泥鳅的第二天,父亲会亲自下厨。父亲又高又瘦,家里的灶又矮又肥。父亲弯着腰站在灶前的样子,像一张薄薄的弓。父亲要煎泥鳅了,我主动坐在灶前烧火。铁锅烧红了,父亲往锅里扔几块刚切好的肥肉,拿起锅铲翻几下压一压,翻几下又压一压,锅底很快铺了浅浅一层油,父亲一只手握住木锅盖,斜挡在我面前的铁锅上方,再将沥好水的泥鳅往锅里一倒。刺啦刺啦的声音响起来,等锅里的热油不再四处飞溅的时候,父亲会将斜立着的锅盖放在一边,不时给锅里的泥鳅翻一下边,当那些黑乎乎滑溜溜的泥鳅煎得焦黄时,父亲就用筷子将它们夹进一只大菜碗里,再往锅里倒一小撮蒜蓉和半碗青椒丝,来回翻炒几下,从大菜碗里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想了想,又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我站在灶旁,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嘴巴有些发黏。终于,父亲从锅里夹了一条胖泥鳅伸到我面前,我张开嘴巴接了,顾不上烫,胡乱嚼几下就吞进了肚子里。
父亲将青椒炒泥鳅端到饭桌上,转身又炒了一碗小白菜。一家人围坐桌前,我狼吞虎咽地吃得飞快。父亲挺着笔直的腰杆,端着他那只专门用来喝酒的陶瓷杯,抿一口烧酒,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父亲又抿一口烧酒,咂巴咂巴嘴,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父亲慢慢地喝,慢慢地嚼,他咬完一条煎泥鳅,起码要喝三四口烧酒。我有时替父亲急,他吃一条煎泥鳅的工夫,我可以吃完半碗饭了。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赵燕飞的散文《蛮好》)

赵燕飞,女,1972年生于湖南邵东,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五部。多部作品入选《小说选刊》等刊及各类年度选本。曾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毛泽东文学奖、《湘江文艺》双年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赵燕飞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