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界与景深,现代诗歌语言的文本瞻顾
——《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读札
文/周朝
收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诗人周瑟瑟主编的《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一书时,正值小暑节气,窗外阳光炽热,草花荣盛。一年中最热烈的季节打开了庞大的翅膀,在山河大地上托起无边无际的生机和诗意。
我们为什么读诗?我们为什么写诗?在文化的视域,很多评论家都有着深刻的见地。我以为,在诸多文学体裁中诗歌之所以能孤峰独秀,当在于其首先的“语言美学”意义,其次即是其“思维创造”“言志抒情”“提升品质”“传承文化”等价值。诗歌就像喧嚣都市里恪守幽境的“精品屋”,工致、粹媺、悦目,以其表象存在的语言首先触达人的视界。诗歌是文学的极致表达,最难介入。其极致表现是:语言之美感、意象之多姿、立意之深邃、空间之多维。
任何时代,诗歌都不会泛众化,即使是盛唐。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兴勃,也只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思考者的催发。彼时,寥落星辰般的朦胧诗人以简洁、富藏、刻骨的诗句,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疼痛与记忆。“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那些以语言缝合理想与现实裂痕的诗行,因慎独、觉醒、反思、教化,所以可贵。
很显然,这些都归功于语言的创造。美国诗人、评论家斯蒂芬妮·伯特说:“诗歌通过语言编排来传达、分享或激发情感……当情感、态度、感受成为一首诗中的词语激发出来的最初、最终或最重要的东西时——当它们富有表现力,相比那些我们能看到的人像画或能讲述出来的故事更像我们能唱出来的歌时——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诗叫作抒情诗……奥登将其称为‘复杂感受的清晰呈现’。”正是因由文字和语言的无限发掘与编排,才有了诗行的节奏、韵律和内蕴。
这也正如周瑟瑟在该书序言《突破语言的边界》中所说:当我提出“语言的边界”,实际上承认了我们想象的边界,但,想象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说语言没有边界。如果有边界也只是暂时的,只有人类认知的边界,想象的贫乏决定了语言的边界。诗是想象,诗可以突破想象的边界,从而获得语言的恩惠。
语言没有边界,想象没有边界,诗学没有边界。优质的诗歌文本从来都是诗人置身于生活的繁冗时空,对现实进行深度思考、辨析、解读,在冲突中博弈,在博弈中建构,并突破语言的边界,呈现出可资鉴赏的诗歌意境,让读者沉浸于特定的景深,获取有价值的阅读感受。因此,良正的诗歌文本不仅内涵丰蕴、节奏明快,更兼具艺术审视和美学感染意义。
在陈先发的诗行中,我们阅读到了深邃的物理尘域和坚韧的追寻执念:
脚下山花欲燃,江上白鹭独翔/这荒芜,突然有了刻度/它以一朵花的燃烧来深化自己……/江水的流逝一动不动/坐在山间石凳上的,似是另一个我//诗人暮年,会成为全然忘我的动物/他将以更激烈的方式理解历史/从荒芜中造出虚无的蝴蝶,并捕捉它(《登燕子矶临江而作》)
诗人独坐于高阔之地,尽览人间意象,在山花、白鹭共同烘托的视界,类如“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之感慨生发天问,瞬间,满目苍茫则有了清晰的标准“刻度”,一朵花兀自开放,尽力为这喧嚣的世界裨辅动能和希望。而暮年的诗人何曾懈怠,“以更激烈的方式”将根须探进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精心创造、雕琢内心的“蝴蝶”。山花、白鹭、江水、石凳、蝴蝶……以各自的色彩和特质,共同构成了燕子矶的天然画图,及其无限的量变与景深。诗人大开大合的特色语言予以读者寥廓的审读视野。
毋庸置疑,现代诗歌语言的演进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硎发新刃过程。从上古歌谣至《诗经》,至《汉乐府》,至唐诗宋词,再至现代新诗,承载了传统文化和东方情感的诗歌语言是历代诗人首要的淬炼功课。“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即是诗人为遣词造句而苦心孤诣的见证。
诗人胡弦则善于通过风格独特的语言,构建自然与情感交织的抒情世界:
那时我去看你,/要穿过正在开花的乡村,知道了,/什么是人间最轻的音乐。//花粉一样的爱,沉睡又觉醒。/青峦在华美的天宇下,像岁月的宠儿,/它的溪流在岩树间颤动。//吻,是挥霍掉的黄昏。/桌上,玻璃水杯那么轻盈,就像你从前/依偎在我怀中时,/那种不言不语的静。(《雀舌》)
诗人以“雀舌”为意象,“穿过正在开花的乡村”,他要去看“你”,“你”是谁?但不管是飘荡在玻璃杯中的“雀舌”,还是所爱之人,“人间最轻的音乐”和“花粉一样的爱”都会在依偎天宇下,舒展一幅温馨幽静、爱意融融的文字卷轴。在语言的使用上,“雀舌”既有茶叶的细嫩形状,又有鸟雀之舌的轻盈灵动,“溪流在岩树间颤动”,将动态意象赋予人的情感心理等等,这种味觉与视觉的相互切换,人性与自然的情感投射,完美地实现了借物言志的诗意交融,拓展并强化了诗歌的审美维度。其艺术价值既承袭了古典诗歌“炼字传情”的传统,又展现出现代诗歌对语言可能性的实验探索。
诗人刘川的诗歌则深蕴哲理、发人深省。读者一旦沉浸其中,便可以在字里行间阅读到诗歌隐秘,领悟到诗歌真谛:
她是护士/夜里查完病房/就埋头/用一本空白病志写诗//其实,她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把病症(孤独、愤怒与忧伤)/如实写在症状栏//说来也怪/她的病症一些出来/她便缓解与/痊愈了//——这或许/便是诗歌的疗效/通过写/病人化为医生(《治愈》)
读者读一首诗,其实就是阅读文字深处的诗人,读诗人的经历、认知、智慧、思想。每一位诗人,都会在字里行间留下自己行走或者思考的影子,都会在无意间把自己叠加成多重意义,并呈现在文字中。因此,好的诗歌作品,让读者撷获的不仅仅是文字的丰盈、结构的美感,更多的是得到触动、力量和催化。刘川的《治愈》一诗,暗示诗人的创作如同“护士”客观记录诊断日志,这种医学术语的艺术处理体现了文字的诗化重构。文本最后一句“病人化为医生”,看似悖谬,实则蕴蓄深意,暗含世象的积弊抑阏以及诗歌拯救价值的哲理性思考。
孔子曾言:“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好的诗人能看到社会的擦伤,好的诗文能疗救社会的暗疾,这是诗人的内在品质使然,我把这归结为“诗歌精神”。优秀的诗人都是“诗歌精神”的建构者,其内心深植改良因子,热心于以抽丝剥茧的智识关注社会现象、生存状态和伦理道德,并致力以练达、峻拔、警醒的诗歌文本消弭污秽、过滤怠惰、匡正谬误、倡导文明。“诗歌精神”应该成为诗人的集体创作意识。优秀的诗歌文本一定深具社会启示意义。
《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将女性诗歌以“真的尺度”呈现,这也是对近些年女性诗歌愈发活跃与斑斓的集束观照。女性诗歌的多元气质昭示着新一代夏娃的觉醒与思考,不论是语言层面,还是结构层面,甚至立意层面,女性诗人群体的担当、真格、空灵和通透在诗行中得到了极致彰显。
王小妮应该是女性诗人群体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善于在生活中捕捉瞬间的讯息,并探索奥义:
大雁真的排成了人字/队列上下扑动/忽然贴近湖面/也许希望有谁能加入它们/可是这儿没有人了/带走我已经不可能/我离开我的身体/不知道多久了(《大雁经过》)
诗歌精短,但内涵绵长。诗人以“大雁排成了人字”的自然意象作为“诗眼”,展放了大雁、湖面、我共同构筑的图景,但这图景却给人荒凉感和疏离感,尽管大雁努力地“上下扑动”,但“这儿没有人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生态日渐撕裂。面对这样的生存窘境,“我离开我的身体”已经很久,无所皈依。诗人惜字如金,用精炼的文字完成了叙事闭环,也完成了对人类生存危机的诗性预警。周瑟瑟说:“我读出了难言的悲伤。这就是诗的命运。”
在李成恩的笔下,是另一种自然和人的对立与冲突。人类之于强大的自然力,无疑是孱弱的,不可或缺的抗争意念时时充斥于矛盾的两面:
鸟鸣弯曲,一条自然的管道/通向大海的清晨/乌云的翅膀收紧鲜花的窗口/雷声滚滚,无限放大的鸟鸣/忠告有时轻,有时重/砸在我头顶像一只睡眠中/突然下降的大鸟//……爱有爱的优雅,一个人提着鸟笼/在北方的胡同溜达,另一个人/骑一只大鸟飞向南方的大海/我就是“另一个人”//鲜花盛开的海边/海浪弯曲,像蓝色的饥饿的蛇/向我扑来,它抬起大海弯曲的头/要么吞下整个大海/要么被大海吞没……(《鸟鸣》)
诗人在诗行中提到的“鸟鸣”“乌云”“雷声”“鸟笼”与“大海”等,是大自然重量级的征象,时常会“砸在我头顶”,但我要化解困境并突围,要成为“另一个人”“骑一只大鸟飞向南方的大海”……在这首诗中,诗人驾驭语言的功力无疑是强大的。首句即用通感修辞手法,将声音“鸟鸣”通感为“弯曲”的“管道”,听觉到视觉的幻化,让诗歌瞬间空灵。“乌云的翅膀收紧鲜花的窗口”一句,隐含明暗、压抑与活力的对立,将自然之力再一次具象化,整首诗的画面感也随之增强。《鸟鸣》与王小妮的《大雁经过》异曲同工:自然生态羸患与人类存在意志该如何通融?
相比于成年诗人作品语言的成熟、冷静和理性,囿于阅历和视野,孩子们的诗歌语言显得尤其的率真、活泼,大多是直抒胸臆,但不乏超凡之语、新奇构思和深层隐喻。13岁的海菁写道:
我去影楼拍全家福/摄影师给我一本/看上去很古朴的/唐诗三百首/让我假装阅读/我翻开一看/全是白纸/我只好把自己的诗挪了上去(《唐诗三百首》)
姥姥从冷柜里拿出一条鱼/鱼死得好冷(《冷》)
《唐诗三百首》中,摄影师的一个寻常之举在现实的镜头下显露出荒诞和费解:“让我假装阅读”,一本书竟然“全是白纸”。全诗语言平实,没有刻意的修饰,看似娓娓道来,其实反讽了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以及传统文化被商业利益侵蚀的价值流失。或许,作者创作之初没有意识到作品宏大的现实针砭深意,也或许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诗挪了上去”填补文化空白的救赎功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首诗歌作品着实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只有两行诗句的《冷》则以日常口语化的文字表达,用最少的文字注脚万事万物的死亡命题。冷,即是物理属性,也暗喻对死亡的情感认知,在诗行的“飞白”中充满了关爱和疼痛。
诗歌最初的表象是语言,语言的深处是立意。没有好的语言的支撑,诗人很难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灵动、形象、准确地付诸于文本,良好的语言建设能力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素养。优秀的诗人往往能对自己所关注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深具内涵的重要事物,通过观察和感知,然后以独自的敏感和创造力,使用富有感染能量的特色语言来表现,让读者产生共振和共鸣。
周瑟瑟以诸多诗人及其文本为研理对象,编著《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敏锐地辐照出当今诗学的语言质地、创作现状和思考向度,他从纷繁的字里行间,析解诗歌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建构诗学的现场实践和理论体系,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深度见识和经验启发。
语言没有边界,诗歌没有边界。那些生命的启示和文化的底细,一直都在我的语言深处。

周朝,原名刘林,诗人、作家、资深传媒人。创作现代诗歌、文化随笔、历史散文及文学评论,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诗文作品入录二十多种年度选本,著有文学作品集《观照乡野》。历史散文《走在西湖边上》被选入山西省高三联考语文试卷、河南省名校高三语文试卷及十多家高考模拟试卷现代文阅读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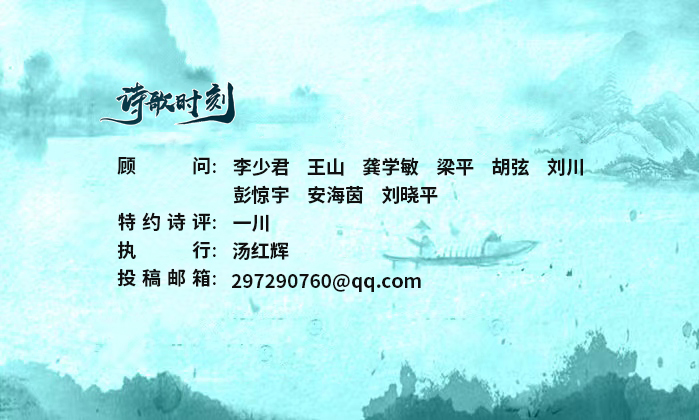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周朝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