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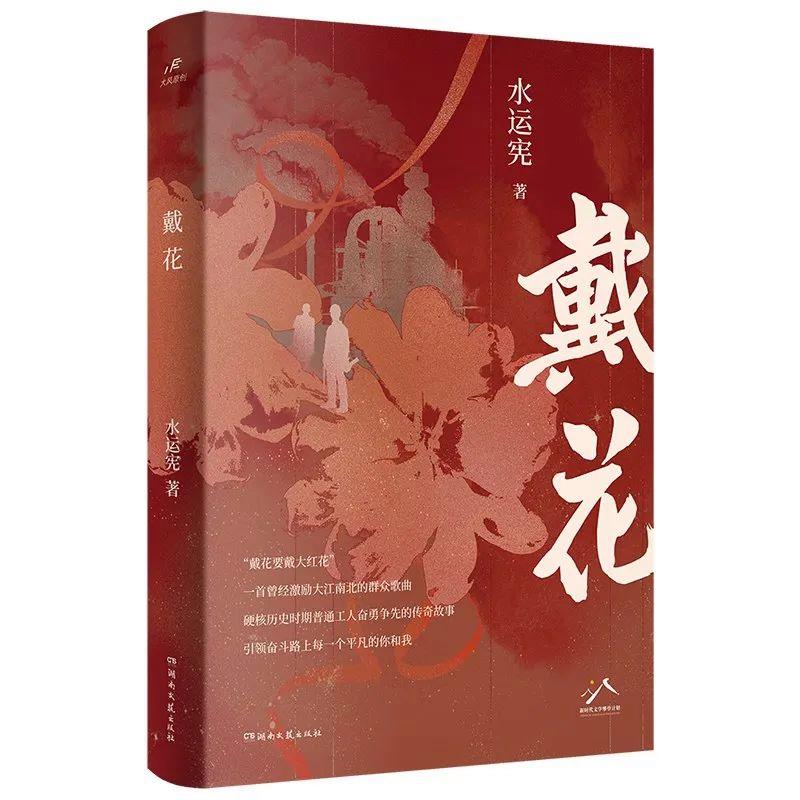
一尊矛盾的丰碑
—— 读《戴花》有感:莫正强的多棱镜像
文/袁娟
读水运宪的《戴花》,令我久久回味的,是师傅莫正强这一形象。他如一尊多棱的丰碑,立在文字之间,也立在人性的真实地带。他争劳模又亲手毁掉机会,他善良也狭隘,他偏爱徒弟却也百般提防——正是这些矛盾,让他格外鲜活,也引人深思。
对劳模的执念:从 “争”到 “让”的灵魂蜕变
师傅名叫莫正强,自幼孤苦,没读过几年书,文化水平不高,上进心却格外强。他总觉得,没文化不要紧,能当个模范也光荣,于是一门心思拼命做事,坚信把事做好了,模范自然就来了。杨哲民刚分到厂里成了他的徒弟,他言简意赅地表示,两人应携手共进,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在德华电机厂最苦最累的熔炉班,莫正强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对劳模荣誉的向往,犹如烈火般炽热,从未有过丝毫减退。当浦陵纺机厂以高薪挖他,他却觉得“工资高到底跟当劳模不能比。”“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在屋宇间永恒驻足,终将如流水般逝去,消耗殆尽。大红花那可是一辈子的财富,活在世上,给家人长脸,埋在土里,给孩子留名,光照千秋,祖祖辈辈满门光彩。”这份对劳模荣誉的渴望深深刻画在他的心中,以至于他不惜多方打听,只为确认在浦陵纺机厂是否也能有机会获得这份殊荣。即便到了生病住院的最后时光,他仍念念不忘“这辈子只怕戴不上那朵大红花”,眼见徒弟晋升为车间主任,自己却与劳模荣誉无缘,那份不甘心显而易见。正如《工人日报》所言,劳模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享有崇高的声誉和社会的尊重。劳模精神作为我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当劳模,他也动过些小心思。被提名为候选人后,他暗地里让小产不久的妻子来厂里送早饭 —— 妻子埋怨他不顾家,实则成了他“大公无私、舍小家顾大家 ”的活广告。厂里人议论纷纷,说他“想当劳模想疯了,又演双簧又做戏”,然而,正是这份私欲的暗流涌动,悄然间将他引向了荣誉之路的岔口,使得他的步伐略显踉跄,心灵略显扭曲。
更严重的是,考核小组即将来调查时,囊中羞涩的他,无力购茶待客,借贷无门反遭冷嘲热讽,一时冲动之下,伸手拿了徐士良抽屉里的五元零钱。尽管徐士良发现后并未告发,他却整夜难眠、悔恨不已,终究在验收小组的座谈会上自曝丑事。“不能昧着良心当劳模”,这句话背后,藏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挣扎与抉择——那好不容易触手可及的机会,就这样被他亲手放弃。可他的执着仍在:“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后年,后年不行就大后年,为了这朵大红花,累死都值。”
谁也没想到,住院几天后的莫正强,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他放弃了争夺劳模的念头,转而推荐了徒弟杨哲民,并言及要“胸怀宽广,放眼世界,而非局限于个人得失”。这或许正是无产阶级先进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完成灵魂蜕变的瞬间,从此在我心中成了敬畏的存在。
善良与狭隘交织:人性褶皱里的复杂光谱
莫正强的善良,藏在记恩报恩的细节里。汪春廷曾与他有过节,还是他亲手送进大牢,可汪春廷出狱后,他不计前嫌接受其回熔炉班。见汪春廷垂头丧气,他想找主任帮着补点零用钱,还动员徒弟给两块钱让他买烟;明知汪春廷可恨,却总念着对方的好,甚至把汪春廷的老相好丘桂兰接来,撮合两人过日子。
他对徐士良心怀的愧疚之情,更是触动人心,令人感慨不已。当初身无分文的他,在绝境中偷走了徐士良的五元钱,却在惊讶地发现那是两张五元钞票后,悄悄地将其中一张归还了回去。后来徐士良因感情受挫、工伤事故爬上水塔想轻生,他一边喊话安慰拖延时间,一边扔出海绵救人,最终却没能留住这条年轻的生命。他呆呆地望着徐士良冰冷的尸体,泪水汹涌而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再也没有机会报答这位曾经给予我温暖的好同学了!”
然而,在他那看似善良的底色之上,却也潜藏着狭隘与偏见的阴影。电机局局长鲁昌顺下放到熔炉班劳动时,莫正强因认定去年自己的劳模资格是被电机局刷掉的,便借分配工作之机给鲁昌顺制造难题——白日令其筹备生料,夜晚又派其清理炉渣,还蓄意倾倒剩渣余料于炉坑,反诬其“挥霍国资”,逼得鲁昌顺两次作检讨,最后还是他找环卫部门派车拖走废料才收场。这场栽赃,藏着他对 “一言堂”的怨气,也暴露了人性里的睚眦必报。
偏爱与提防:师徒间的拉扯与固守
初见莫正强,杨哲民是有些失望的。“莫胡子”这个外号很传神:稀疏的胡须东一撮西一撮,黑少白多灰不溜秋,“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让刚分到厂里的大学生怎么看都不顺眼,甚至没好意思当面叫一声“师傅”。
可莫正强对这个有文化的徒弟,是打心底里满意。刚宣布杨哲民归他带,他脸上绽放出难以掩饰的喜悦,胡须在激动中仿佛也轻轻摇曳。他温柔地牵起徒弟的手,亲切地呼唤着“民儿”——这如同父母对孩子的昵称,自此成为他对杨哲民特有的温情称谓。他带徒弟回家吃饭,在其他徒弟面前不住夸赞,甚至心底最深处的秘密也只愿与他分享;新徒弟第一次开炉时,他一边安慰“莫紧张”,一边一丝不苟地帮着穿戴防护用品;开炉出故障时,更是拼尽全力将他推开,自己毅然挡在危险的前方。到了身体快撑不住时,他还教育子女“长大要跟杨哲民学”,说这徒弟“比亲儿子还亲,是天底下最有良心的人”。
爱得深,提防也来得切。杨哲民对炉膛形状、投料比例提出新想法时,他一口否定;徒弟鼓起勇气改了炉膛,效果不错,换来的却是他劈头盖脸的冷水。他去广西疗养的两个月里,杨哲民成了车间负责人,终于能放开手脚搞技术革新,把炉膛改成了葫芦形。可他一回来,见此情景便一边痛骂一边敲敲打打,硬是改回原来的灯罩样子,结果导致开炉屡次以失败告终。他对着杨哲民怒吼,一字一顿地喊出“杨哲民”——这愤怒背后,隐藏的是对徒弟可能超越自己的恐惧,以及对风头被抢的隐隐不安。其实他怎会不懂,“名师出高徒”本是荣耀,可那份“不能失脸面”的执念,终究困住了他。
精明与守旧:经验主义者的双面镜
莫正强脑子活、爱琢磨,凡事想得周到,手上的真本事更是没话说。譬如砸铁锭一事:一条重达十公斤的铁锭,即便是几位身强力壮的汉子轮番挥锤五六下,也未能撼动分毫。而他,个头虽不及旁人,却仿佛未使全力,只一锤落下,铁锭竟应声裂为四段—— 这是炉工多年练就的巧劲,四两拨千斤,全凭经验,谁也比不过。
他的“能干”不仅限于车间之内。改造房屋是把好手,无论是自家的居所,还是厂里为杨哲民母亲分配的房屋,经他一改造,皆能巧妙地变为带有卧室与厨房的两居室,地面更是以厚油毛毡铺垫两层,再覆以木板,固定得坚如磐石,其手艺堪比专业装修师傅。国庆假期期间,一起检修窗事件发生,他仿佛预感到不寻常,提前安排了值班。案发后,他迅速保护现场并及时报案,为案件的侦破争取了宝贵时间。此外,他从丘桂兰“国庆加班摔断腿回乡下养伤”的陈述中发现了线索,通过细致的侦查工作,最终揪出了事件的始作俑者,表现出了侦探般的敏锐和专业。撮合丘桂兰和汪春廷时,他巧妙运用“试营业”的策略作为缓兵之计,给予丘桂兰半个月的时间以适应,同时,他还热心为两人寻找兼职、租赁房屋以增加收入,其心思之缜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可这般聪明的人,思想却透着古板守旧。数十载坚守熔炉岗位,未曾涉足技术革新之路,职业生涯近乎停滞,恰似经验砌成的壁垒,既捍卫了他的尊严,也束缚了他的步伐。
坚强外壳下的孤独:无人可说的苦与痛
莫正强从不露怯。师母小产、孩子生病、自己大病,再难的坎,他都不声不响扛着,照样每天上班。可坚强的外壳下,是无人诉说的孤独。师母的来历、她对汪春廷的挂念,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想装糊涂时便含糊过去,不想装时便一抓一个准,可这份计较,能跟谁说?直至后来,他才恍然惊觉,自己竟孑然一身,无处话凄凉,唯有偶尔向杨哲民倾诉衷肠。
缺钱时找不到人借,过着“今天愁明天,盼着发工资”的日子,却不肯接受堂哥的好意和徒弟的援助,硬撑着死要面子。这份孤独,是硬汉最柔软的褶皱,藏着普通人的无奈与倔强。
《戴花》中人物众多,但莫正强却以他的复杂与真实,成为一座立得住、耐品读的丰碑。他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与阴影,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正是这些挣扎、转变与坚守,让他走出纸页,走进人心,成为一尊值得反复凝视的、矛盾的丰碑。
来源:红网
作者:袁娟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