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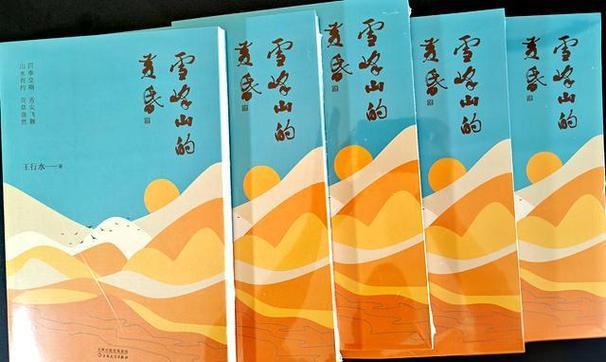
雪峰山 诗歌的百味园
——读王行水的乡菜组诗《舌尖飞舞》
文/刘代兴
王行水先生的诗集《雪峰山的黄昏》辑二《舌尖飞舞》,是我翻开诗集最先注意到的一组诗,由六十多首短诗组成,有着鲜明的诗歌个性与艺术风格。
组诗《舌尖飞舞》标新立异,皆是围绕雪峰山的乡菜下足功夫,牢牢吊住我的胃口。至于重口味的乡菜这一陌生诗歌题材,我认为这是诗歌的一片处女地,是诗人围猎的禁区,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笔墨、大阵仗的集中抒怀。中国明代隐士洪应明编著的古典名作《菜根谭》,其实是打着菜的幌子言述与菜无关的内容,只是一部关于修身养性的箴言录。食谱入诗,在中国古诗词里,最多也只是写到酒、写到鱼,再远一点写到谷粒,写到竹笋与豆苗。但王行水大胆地闯入这片偏僻领域,发现前人未留意的现象,找到诗意与灵感触发点,抒前人所未发的情怀。《舌尖飞舞》诗辑便是像当初西方的静物画一样,大胆地将侗族民间乡菜厨艺首次亮相,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新颖奇特,让人眼前一亮。
《舌尖飞舞》是一组怀化地方菜系大全,是雪峰山美味的盛宴,是五溪大地传统乡菜的汇聚。但你若是认为王行水仅仅只是在呈现怀化美食,展示山乡绝味,推介侗族菜品,炒作湘菜品牌,那你就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了,是没有品味到精髓,没有尝到此中的三味。诗歌与应用公文、新闻特写最大的区别在于想象与扩张的力度、在于灵魂飞舞的高度、在于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所以才会耐读、耐看,耐人寻味。《舌尖飞舞》恰当好处地把握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与特点,才会如此多姿多彩,打动读者。同时,诗歌的语言,有别于其他一切艺术形式的语言,多义性与跳跃性,是它的显著特征。细细地品读,在语言飞舞的尽头,诗歌的蕴意与涵义便会渐渐浮出,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飘然若羽。
王行水的雪峰山菜系集合里,在他幽隐语言的尽头,潜藏着悲欢。王行水风雨兼程,发奋图强,而又历经曲折,饱受磨炼,但他仍坚守文学的初心,热爱生活。在他的眼里,侗家的乡菜系列里,饱含着生活的馥郁与岁月的醇酽。“溆浦粉蒸肉”是肉吗?是的,诗歌描绘的当然是可口味美的家常菜溆浦粉蒸肉,但分明又是写的某个人。你看她一番浓妆艳抹、粉墨登场。她在被消费,也在消费别人,她参与社会的良性循环,最后登上人生的巅峰,“引得围观的人群欢呼雀跃”。让人想起了李太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狂喜。“回锅肉”看来是选择对了,他放弃了好汉不走回头路的想法,决定回头下一次油锅。路上遇见辣妹子,死心塌地跟着他赴汤蹈火。他俩终于在一口锅里情意绵绵,融为一体,回锅肉从此得到了新生,“成就了飘香惬意的人生”。谁说一盘菜,就只能满足口腹之欲?看似粗俗不堪,面目油腻,却也是姿色诱人、秀色可餐,有着灿烂的笑容与得意的姿态,是不是像极了人间的痴狂?
“香肠羊肉粉”成功地荣登特色小吃榜首,但这却是它经历了穿肠过肚的痛楚换来的,它身后还有白发三千丈的别恨离愁,这让它寝食难安;“牛瘪火锅”原来是一锅牛肉在火烧火燎地等待牛瘪的到来,这牛瘪原来是肚子里的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苦不堪言却被别人当成了美味佳肴大快朵颐,这是多么大的痛楚,又是多么强烈的反转。一盘盘看似普通的地方菜肴,其实深藏不露,秘隐天机。在你进食的时候,你是否尝到了人世间的苦涩?你是否从中体会到杜工部“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悲恸?
王行水的菜品里,在他恣肆语言的尽头,凝聚着坚贞。上刀山,下油锅,矢志不渝的爱情,忠贞不屈的相守,是成就一道道经典名菜的前提条件。“沅陵晒兰肉”,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离岸爱情故事,喝着沅水长大的邓家老二与二嫂,他们的相爱相亲终于制作出人间绝味;“油淋辣椒”,就是辣妹子凭一己之力对抗一众大佬小喽啰,幸好得到平时油嘴滑舌的雪峰山茶油坚定的力挺,他们赴汤蹈火终生相托的爱情结晶,终于得到了餐厅里“满堂的喝彩”。这里,人间至味不是清欢,而是共患难、同甘苦,是轰轰烈烈,是牙崩齿裂。还有像香芋与排骨、剁椒与鱼头、鳅鱼与腊肉、血粑与仔鸭、银耳与猪肝,它们义无反顾相互成就的结合与厮守,最终换来了流传千古的口感与名声。你可以认为王行水是在借“菜”发挥,书写着人世纯美爱情的诗篇。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引申取义,譬喻联想,的确触及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让人耳目一新。当然,不只是爱得死去活来,也有百般离愁,相思万里,让人酸过甜过苦过辣过之后,再掬上一把同情的眼泪。
王行水的菜单里,在他流畅语言的尽头,还演绎着玄幻。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通古今,横贯中西,甚至《西游记》里孙悟空七十二变,也在王行水的诗歌创作里大放异彩。“麻阳十八怪腊肉”,是懂了事的成年猪在通往市场的路上,一股狠劲往农历腊月狂奔,跑出了久负盛名的成功;另一头猪不甘平庸度过一生,在对世人的冷嘲热讽耿耿于怀之后,剁下自己的四只脚焖进锅里数黄豆,豆子一直没数清,却熬出了胶原蛋白奉献给人类,成就了一道大菜“黄豆焖猪蹄”。这种魔幻的诗歌艺术,还可以是一种童话、是寓言、是神话的另一种版本。在语言的尽头,呈现出劝诫、教化与某种训谕的氛围,讥讽了世间的某些阴暗、污秽、拙劣与堕落。“湘辣牛筋”,就是历史上的某一头倔强牛遭到辱骂谤讦,于是干脆抽出自己身上的这根筋来,以此证明“一根筋”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这世界太稀缺太需要它了;雪峰山的乌骨鸡志向远大一飞冲天又能怎样呢?还是有非议说它是鸡肠小肚,逼得它主动交出自己的全副肠子,证明体量与能量完全是两码事。鸡肠被高高挂起饱经烟熏火燎的考验,竟不料成全了“尖椒炒腊鸡肠”这道传奇菜品,让食客胃口大开。福祸相依,物极必反,世道轮回,否极泰来,从这些驰名三湘大地的雪峰山土菜里,让人悟出了一些人世的深刻道理。原来在魔幻的背后,藏着某些恒久不变的定律,推演着宇宙古老的阴阳相生太极法则。
冷峻的辨析、理性的探究、人性化解构、谐谑的表达,构成了这一组雪峰山乡菜诗显著的艺术特色。普通的事物与日常,很难艺术地把握与诗意地呈现,极易陷入苍白与平淡,而语言的精准锋利又会使文本偏离阅读的兴趣。这样特殊的题材,是对诗人的一次考验一次检审。而在诗人的眼里,这堪比家乡风物山村乡愁的菜谱,自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不只是美食,更像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奇遇、一次冒险、一次峰回路转的穿越。诗歌在这里不仅是思辨、审美、创意,还可以是机趣、幽默、突破。
在惊讶与大笑之后,掩卷沉思,人类的世界与美食的菜谱,何其相似。它们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抑或是暗通款曲之幽。这当然不是指弱势群体被当作一道下饭菜而被同类端上桌,进而被蚕食吞没的虚拟场景。我指的是人世间蕴含的游戏规则与秩序,在菜系的制作与厨艺的烹调过程中也同样普遍适用。
也许,读王行水的这些乡菜诗,有人会感觉太土太俗太白太扯,甚至太菜,不在阅读的舒适区,挑剔的人或许会感觉肠胃不适。但你不妨当作一次惊险的游园活动,比如过山车或者大摆钟之类的娱乐项目。那么紧张与刺激,一声尖叫,一场汗雨之后,你会渐渐地平和下来,扪心自问,对不对呢?爽不爽呢?会不会事后回想起来垂涎三尺,哈喇子流了一地?又如一次不期而遇的黄昏,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劫后余生,不是落幕,是期待下一场的揭幕。看日暮苍山,落霞孤鹜,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风景,此时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不也是一次人生难得的邂逅吗?
感谢王行水给我们带来的一次难以言述的阅读经历,那是在语言的尽头飞舞时,所拥有的启迪与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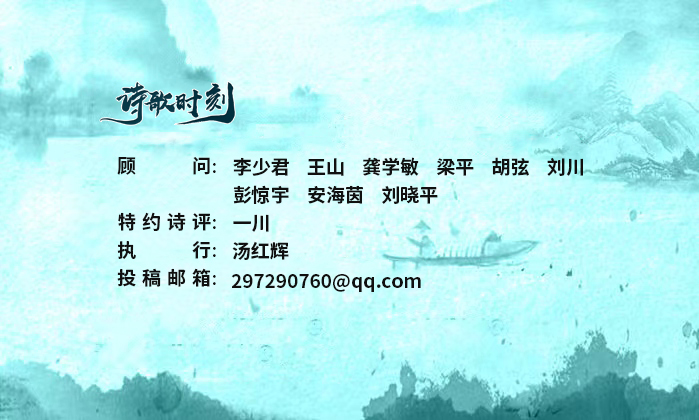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刘代兴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