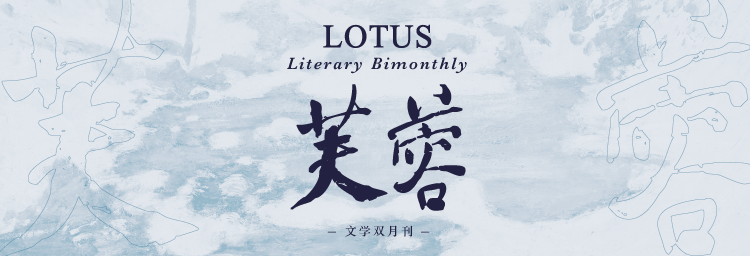

天马的骑手(短篇小说)
文/叶临之
乌兰遇到一名诵经人,诵经人告诉他,鹰跑到他的眼睛里了。
这是哈萨克人才能看到的鹰。他的铁骑爬上乌孙山的山脊,诵经人从雨雾里走来,大雨滂沱,乌兰简直看不清他的眼睛。乌兰要离开安格列特达坂了,他得一口气赶到白石峰,接下来,他感觉到这只鹰从白石峰的悬崖一路跟随着他,这三十几道弯的山壁,让他看到自己是雨雾里的鹰,他在雾里盘旋。他没有搭乘诵经人,诵经人要到底下的察县去,而不是去山那边的县城,而且看诵经人装扮,他很可能是从圣祐寺来的。
从乌孙山下来,乌兰都在盘山道中回想他的话,乌孙山的道很险,他想,这大概是今年最后一次回来县城。
乌兰回昭苏,他是放不下幸福街的马,不过,这些年他从来不说。
雨雾在乌孙山上一直伴随着,等到下了山,草原看起来清朗了,难怪没有提示伊昭公路关闭,否则,就只能从伊宁绕道特克斯过来了。乌兰还在纳闷,跟他走的鹰也随着他下山了,来到绿茵茵的草地,随着那轮月亮在后面乌孙山高高地挂起,鹰化成了水雾,成了一匹白马,在远远的那托木尔峰的衬映下模糊不清了。起伏不定的山峦有轮廓分明的雪山线,衬映着底下这块平原上辽阔的绿茵地,一时,他只看见马,看不见山下的水雾,马和车后面高高挂起的玉盘、近处的屋舍融为一体,这轮圆月照着低矮的蓝色哈萨克屋舍,璀璨的昭苏县城就在跟前。乌兰本想回到县城,就找阿桑去,阿桑离开军马场后,在湿地公园上班,当十来个年轻小巴郎的师父,那么,他就是骑手的老师了,他手头里有最好的伊犁马,宛如神驹的马会让他踏进特克斯河,领略到天山脚下十一月的刺骨寒水,那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呢?乌兰十二岁当骑手的时候就体味到了,只是现在他舍不得县城边缘的家,这同样属于哈萨克人的天地,从天山下来的月光像一道金边镶嵌在叫幸福街的小街上面。
夜晚来了,乌兰加快行车速度,他没有声响地回来了,把铁骑停在幸福街中段的那栋蓝房子前时,仍像惊动了整条街。从邻近院子里传来轻微的鼾声,那是马鼻子自带旋律,抽出来一线线能够看见的冬不拉、能够听见的赛马曲,这让幸福街更安静,连废弃的摇井,由于月光的停留,也看起来更古朴和铜亮些。
乌兰首先去马厩,他得去看看自家的马,打量妻子叶丽扎有没有按照他的吩咐给马加夜料,他在外面养冷水鱼的日子里,叶丽扎就负责照看他的爱马。现在每天早晨,叶丽扎都和他视频,视频里,叶丽扎端庄的美人脸后面,总是那匹栗色的马驹头一个出现,这匹马娃子从幸福街的尽头一出现,就迈开了蹄子,摇起尾巴,咝咝地叫,冲到他家的百十顷草地尽头,等快要到那排白杨树下,它才回过头来对着后面黑如绸缎的母马点头示好。这时,俊俏的伊犁母马一定会在叶丽扎的手上挣脱缰绳,去追赶属于它的小马驹。这对母子走在前头,跟在后面的是六头自信满满的公马,其中有两三岁刚成年的,有五六岁正在壮年的,家里有了这些马,就应了阿桑的话,“嘚,有了自家的,就不需要跨过别家的铁丝栏,也不要偷骑别人家的马了”。阿桑说完大笑,他在说少年时的乌兰偷骑马的糗事,当时没有谁家的草地围铁丝,现在可不一样了,每个养马户的草地都围上了铁丝,马匹一旦跨过铁丝栏,总是发生意外,要不被过往的汽车撞了——那些马儿面对晚上开着亮灯的汽车,总是一动不动,司机稍不留神就出了事故;要不就是马成群结队地散步去了,即使溜到百十公里外的新源,也没人知晓;而且,马与马之间会打架,有被隔壁草场的公马咬烂嘴巴和耳朵的,有尥蹶子踢坏蹄子的;至于那头待产的母马,总是步履蹒跚走在最后,距离下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看起来都是乌兰赶回幸福街的理由,他对小儿子巴图京许过诺,待明年春天冰雪融化后把出生的马驹送给他。
这些满是活力的走马放养在幸福街后面自家的草地上,当他没从伊宁回来,它们从来不越过界限,叶丽扎可以很安心地在家里做她的家务活。
看完马后,乌兰转身到前房去了,他望了望蓝色檐廊下涂成金色的一抹月光,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叶丽扎温好的奶茶和烤馕,随后,他就可以在绣着红黄相间图画的羊毛地毯上美美地睡一觉了。
乌兰作为一名前骑手,现在是遨游在伊犁和阿勒泰之间的雄鹰,他回到幸福街,总是会引起响动。
最开始察觉的自然是他的妻子叶丽扎。叶丽扎是一个温顺的女人,这个温柔、漂亮的女人,他头一次是在县里大赛遇见的,当时她二十岁,在她母亲看来是还没谈过恋爱的大龄姑娘,他呢,二十二岁,在参加一个民族赛马比赛。那匹陪伴了他十五年的乳白色的爱马获得了两千米速度赛的头名,叶丽扎就站在赛道旁边,她也是参加赛马的女骑手,获得冠军的乌兰像英雄一样骑着马往回走时,他拉了下马嚼子,这匹白马也像英雄一样扬起鬃毛,“咴、咴”地叫了两声。乌兰顺着马的目光掠去,一个身穿白色盛装的女孩站在赛道边望着他,他们的目光神奇地搅在一起了,那刻,骄傲的乌兰内心澎湃起来,他扬起马鞭,又让白马跑了一圈。乌兰成了胜利者,只是他没有和姑娘发生直接交谈,但是后来的秋天,乌兰又神奇地碰到了她,是在一个叼羊的表演赛上,他获得了奖品,是一只羊。这回,他主动了,他不想再错过这见过一次就忘不掉的姑娘,他把奖品赠送给了她。他们正式认识了,至于后来,他们的故事就漫长了,要说的是去往特克斯的那片无垠的草原上,他和她生动地表演了一场“姑娘追”,他们嬉闹着。等下了山坡,他俩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记忆多么清晰啊,当时他们忘记了所有,即使叶丽扎的家就在草原后面——那流向特克斯河的一条小溪旁边的毡房就是她的家。那两年间,叶丽扎和乌兰恋爱是秘密的事情,叶丽扎的母亲还是惊讶地发现女儿变了,曾经,这位哈萨克女子发誓不会嫁人,叶丽扎家里没有男孩,作为家里的老大,她执着地认为她要像阿爸一样做个男人。
然而二十年过去,乌兰不再是军马场的骑手,他感受到了世界的飞速发展,从伊犁到阿勒泰,从乌鲁木齐到南疆,他转了一大圈,从军马场退役后,他卖掉了家里的牛羊,从幸福街来到乌孙山那边的伊宁。他做起养殖冷水鱼,在七十七团,在尼勒克,在布尔津,在天然的赛里木湖里,他养起虹鳟、金鳟、大马哈鱼和大西洋鲑,后来,他的大儿子塔里克长大了,塔里克更是成了他生意上的助手。大儿子塔里克也不愿当骑手,这个孩子从小喜欢吃,小时候的志向就是当厨师,后来还真考了厨师学校,从学校毕业后做起了厨师。现在,乌兰让他常住伊宁,经营起一家冷水鱼餐厅,至于顾客,也是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天南地北的地方。也就是说,乌兰成了成功的商人,不再是幸福街上那个稚嫩的青年、获奖无数的骑手。自从家里的坐骑换成轿车后,叶丽扎渐渐不太管他的事了,她只是还想像以前一样生活,现在的她觉得在家带大读初中的小儿子巴图京就好,等巴图京长大后,她就可以放心地老去,然后变为乌孙山下的一棵长生树。
不过,丈夫回到家,叶丽扎还是看在眼里。叶丽扎先乌兰起床,等乌兰起床后,他洗漱完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一大早踏上家门口的铁骑前往七十七团或伊宁,等叶丽扎从草地回来看到乌兰时,乌兰站在院子里那口需要修整的馕坑前面,他从墙根那里挑了好些泥巴来,和起稀泥,然后把稀泥悉数糊在馕坑壁上。丈夫在忙,叶丽扎也没有说半句话,刚才乌兰还没起床,她把家里的马和羊赶去了自家的草场,等到红彤彤的太阳从那托木尔峰的垭口那边照射过来,她已经完成早晨该做的所有工作。这时,暮霭尚笼罩着幸福街,而一溜子白鹤盘旋在绿油油的草地和树林之上。这两年普遍干旱,特别是今年,然而九月底来一连下了几场雨,草场集体返青,草是绿茵茵的,还长起蘑菇,绿油油的草地上,蘑菇一个一个地探出头来,就像四月的春天。以往,每天早上,她做完这些工作,都要用视频向乌兰汇报,彰显她把他托付的事业放在心上,现在他回来了,自然可以减少这道程序。叶丽扎太累了,可她总是默默地承受所有。
从幸福街后面的草地里回来,叶丽扎就一直在厨房里,她要炖一锅清汤羊肉,前一天,她让乌兰留在幸福街的弟弟阿比哈尔宰了一只羊。阿比哈尔曾经也是优秀的骑手,如今是懒惰的司机,开着那辆出租车在昭苏县城晃悠过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说铁壳子车就是一匹马,遛一遛就行了,而且还自满地说,昭苏的烤羊肉两块钱一串,够一家老小一天吃五十串就行了,乌兰为这说过他多次。昨天阿比哈尔宰完了羊,叶丽扎已经把羊肉分割成好几块,她做好了乌兰要回家的准备。
一位客人的到来会打破幸福街的静谧。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叶临之的短篇小说《天马的骑手》)

叶临之,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留学日本,2019年来访学于中亚各国。在《上海文学》《天涯》《山花》《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青年文学》《长城》《作品》《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小说百万余字,《文艺报》《文学报》《百家评论》等文学评论报刊对其文学创作有专门评论与推介。代表作有《猎人》《伊斯法罕飞毯》《中亚的救赎》等。
来源:《芙蓉》
作者:叶临之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