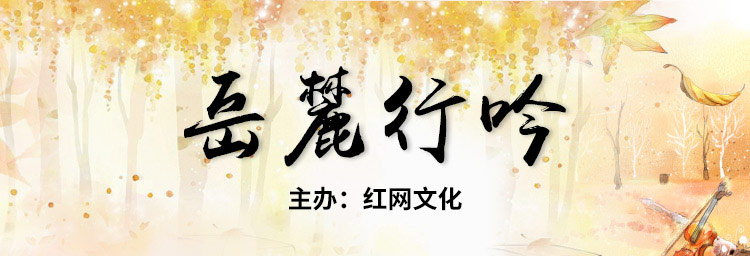

上黄门
文/王琼华
听说我要写一写上黄门的往昔,正准备为上黄门一年一度腊月年会舞龙表演的黄春森,跟我讲述了他爷爷的故事。
他爷爷叫黄礼古。
那时候,上黄门有好几家龙香作坊。好些村扎香火龙,龙香大多来上黄门挑选。
这年,才十四五岁的黄礼古,一个人来到上黄门找活干。报恩寺的老方丈,听说黄礼古老家是在有不少龙香匠人的仙殿垅村,便问:“你会做龙香吗?”黄礼古答道:“我爷爷做龙香,我父亲也做龙香。”方丈一笑,没想到这个稚气未脱、憨态可掬的孩子,这般巧妙给了自己一个回答。他说:“既然手艺是祖传,那就在寺中厢房里做龙香吧。”于是,黄礼古开始在上黄门做龙香。
过了几年,两家老字号龙香坊突然怒了,要把黄礼古撵出上黄门。原来,黄礼古的龙香做出了一点小名气,街上小作坊觉得他抢了自己的生意。不过,黄礼古不仅没离开上黄门,很快还在上黄门买了店铺,也有了龙香小作坊。黄礼古怎么在上黄门站稳脚跟的呢?这年,俩村子找他订龙香时,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条件,其中一村子位于风口,晚上风大,便跟黄礼古说:“龙香既不能被风吹灭,也不能被风吹出火苗。”另一个村是个大村,香火龙围着村子走一圈,耗时很长,所以说:“我们村的龙香烧得要慢些。”黄礼古竟然一一答应下来。有街坊不禁摇头说黄礼古是个“冇脑门”的人,竟敢接这种活。结果,两个村子顺顺当当皆大欢喜地把香火龙舞下来,黄礼古的名声就响了。那年,黄礼古才二十好几。
黄春森及他母亲陈忠秀跟我说,他们家在上黄门已经住了一百多年。
上黄门,不是一条门。
它是汝城县城一条最有名气的老街。抑或位于上黄家村朝门口,这条街才叫成了上黄门,而且自古一直叫到眼前。抱朴见素,一任古风的上黄门,早已是一条积攒着很多奇事异闻的老街。
眼前,街上有一幢仍见贵气的旧楼,挂着一方“荣华客栈”的标示牌。那时,它也称江西会馆。
我第一次走进荣华客栈时,惊讶了,里头竟有一座戏台。
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一年,汝城人喜好的祁剧,这时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祁阳艺人曾子茂组建“利济班”,由津江朱氏利济祖后裔当本家,有演职人员40余。另一艺人伍子喜组建了“凤舞班”,由下湾村胡凤璋做本家,有演职人员50多人,生日净丑齐全,属当时汝城境内最大的戏班。不久,又有了“建字班”和“胜字班”。“胜字班”后来演变成了衡阳祁剧团。这年中秋前夕,“利济班”与“凤舞班”都想在荣华客栈戏台上演戏。客栈老板左右为难,后来听了帐房先生“四只眼”的嘀咕,让两个戏班子轮流唱戏。两戏班同意了,无意中有了打擂台的阵势,戏迷当然欢喜。腰缠万贯、手上有兵的胡凤璋见“利济班”占了上风,心怀不满,就拍响枪匣劝阻戏迷看“利济班”的戏。结果,戏迷们不买账,哪怕胡凤璋宣称,送空心油糍粑,送油炸花生墩,送绿豆粉,但“凤舞班”仍遭冷场。因此呐,这场唱戏打擂台中诞生了一句歇后语:“上黄门看戏——不看人!”
除了荣华客栈的戏台,上黄门还有龙母戏台和报恩戏台。一条老街,竟有三座戏台。只见那匀脸勾眉粉扑墨描一扮,霸王虞姬吕布貂蝉们就铿锵登场、咿呀开唱,唱得上黄门人心旌摇曳、热耳酸心,唱得上黄门人凄清悲咽、涕泪涟涟,唱得上黄门人努舌瞠目、血脉偾张。说到底,上黄门人真是有一腔热血,爱憎分明,识仁诚敬,信奉忠孝节廉,也懂享受七荤八素。上黄门唱戏听戏,讲究得很呐。在荣华客栈,听戏是一种雅聚。龙母戏台唱戏,图个排场与热闹,戏班子都是有钱人家请来的,不是婚寿庆贺,就是乔迁或开业。报恩戏台,唱出来的调儿大多是祈福还愿,抑或要让报恩寺菩萨们听到,但阵阵叫好声还是街坊亮嗓发出的。这个戏台还有一传统,即过年期间,一定会演上几场祈求诸事合顺的吉祥戏《仙官庆会》,戏中演绎着驱邪使者钟馗在福、禄、寿三星的指派下打前站,在民间扫黑除恶、降服妖魔鬼怪,最后让三星分别献瑞呈祥的故事,其中的年味,既渗透在热闹非凡的情节场景里,也在于体现出人们新年伊始接福纳祥的朴素情感。上世纪四十年代,龙母戏台一侧盖成了朱氏总祠。龙母戏台日夜连唱,六天六晚,整条上黄门街人山人海,胜似过年。

比上黄门唱戏更让人叫绝的是两棵“唐柏”。所谓“唐柏”,上黄门人对柏树巷内,即荣华客栈背后两棵唐人种植柏树的尊称。有人考证,报恩寺落脚那天,两棵柏树苗也栽下了。有人说是先生种的,有人说是学童种的,反正跟读书人扯上了关系。后来,汝城民间有了一句俗语:“先有报恩寺,后有上黄门。”时至宋初,上黄门不仅有了人家,又因前来报恩寺烧香祈福的人络绎不绝,让其落脚的伙店也开张了,后来也有了杂货等店,甚至开了一家“唐柏先生”的私塾。这“唐柏先生”的后人,曾做过天柱山文昌书院的山长。据说,其母将他生在“唐柏”树下,从小聪颖,哪怕跟街坊称为“棋神”的报恩寺百岁伙夫盘腿坐在“唐柏”下对弈,三天三夜,九九八十一盘,盘盘赢一子,这让百岁伙夫惊喜万分,竟然要拜这孩童为师。一旦离开“唐柏”手谈,却是输赢不定。这事当然成了上黄门奇趣之一。依傍“唐柏”的私塾开张时,他在门头上题了两字:“唐柏”。从此,街坊称他为“唐柏先生”。至今,这两棵“唐柏”身子骨仍见硬朗,郁郁葱葱。汝城县志载,明弘治九年,即1496年,范渊与曹琚同中进士。曹琚是北门曹家人,范渊则住与上黄门北口隔江相望的三拱门范家,两人属多年同窗好友。范渊喜欢来到“唐柏”一侧读书。树上有好几个鸟窝,平时叽叽喳喳,热闹得很,但范渊一来,也就鸦雀无声了。所以,范渊这书读得如疾如醉。离家赴考前一日,他邀曹琚来到“唐柏”树下,一块温习功课,却听到鸟鸣声不断。范渊几分诧异地:“这鸟今日怎么顽皮了呢?”曹琚抬头一看:“原来是两只喜鹊呐。”之后,曹琚中了进士,跟范渊作揖说道:“多谢兄长,本来属于兄长的喜鹊报喜,让愚弟也沾了光呐。”范渊即说:“喜鹊又不是一只。两只喜鹊。同喜同喜。”这事传为美谈,家喻户晓。从此,很多读书人喜欢到“唐柏”前许愿。
我突然想,哪天再去看看古“唐柏”,抑或还能看见那两只喜鹊仍栖在树上呐。要不,汝城这小地方怎么会有三十九名进士呢?还有状元呐。当今更是年年有子弟考上清华北大,他们大多跟上黄门结过缘,其中状元朱经贯就住在离上黄门一步之遥的村子。我跟一友人说过,哪怕来人杰地灵的上黄门逛一逛,也会沾一身才气回去。前些日子,文友宋意心看到上黄门正在修缮,便建议在上黄门筑一方进士录。这“金点子”落地,它将与“唐柏”一块成为游人们追捧的景观。
也许,“唐柏”仅仅是一个可信可疑的传说。
上黄门的涛锦堂,却是一家地地道道,仍在呵护上黄门人的百年诊所。这日,我遇到朱秋菊,她是诊所的女主人。涛锦堂,她丈夫李军平家祖上传下来的堂号。朱秋菊的丈夫叫李军平,算上他正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念书的儿子,李家有了六七代人从医的历史。但始初它不叫涛锦堂。当年,李军平的爷爷李仁涛,刚得一儿子,取名叫李显锦。抓周那日,李显锦没半点迟疑,伸手抓到最能代表郎中的标志物——小葫芦。郎中看重葫芦,就是彰显“悬壶济世”的寓意。李仁涛大喜,后继有人,便改堂号称“涛锦堂”,即是从父子名中各挑一字组成。
如今,涛锦堂坐诊的医生是朱秋菊。
“你可别小看朱秋菊,她是更有名气的中医世家传人呐。”跟我说话的是朱由旦,今年九十多岁。十来岁时,他就在全福堂学徒。他说:“全福堂也是中医诊所。当时,全城里最有名的中医诊所就是全福堂、万茂堂和寿康堂三家。万茂堂堂主是个江西人。我学徒的全福堂是三拱门范家人开的。寿康堂属井坡人的堂号。三家诊所,各有千秋,但寿康堂名气最大。朱秋菊就是寿康堂的传人。她爷爷出诊,一定会有轿子接送。轿子发出的嘎嘎声,让一街人都往轿子看去。”朱秋菊的爷爷最擅长治疗不育不孕症。老街坊还在传说,这位郎中有一习惯,不育不孕患者吃了三个疗程的药,没能怀上孩子,第四个及之后的疗程药只收半价,如果两年内没怀见“喜孕”,便会退回银票。
朱秋菊的爷爷性格是爽朗。
朱秋菊个性也是如此,一个很热心的女子。有了她的引导,我才遇上了已有四十几年未见过的朱由旦。朱由旦老人的儿子八古便是我的发小。

朱由旦,一个知道上黄门前世今生的人。
他有印象,上黄门北口有一闸门。清晨公鸡咯咯一啼,闸门就开了。这时,街上店铺早已拆去门板,屋里的空气换得干干净净。上黄门里开有南杂店、百货店、药店、饮食店,还有伙店、票号、当铺。连米店也分为糙米行、熟米行。甚至还有牙行,后改叫平码馆。最有名的牙人叫“朱半仙”,据说其家七代做牙人,直至民国初期。“朱半仙”系第六代掌柜,最有特色的是他们大都戴着一副石头眼镜,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并获得“没有‘朱半仙’扯不成的买卖”这般赞誉。当然,上黄门也称不上“应有尽有”。朱由旦称,整条上黄门老街,找不到一间鞋店。老百姓大热天都穿“三眼骑”,冬天穿布鞋。有钱人一年到头穿三接头皮鞋。比如米行的朱掌柜,最喜欢在米行门口擦自己的皮鞋。“朱掌柜,擦皮鞋呐。”街坊招呼道。朱掌柜会笑容可掬地回上一句:“嗯,擦皮鞋呐。”如果一时没街坊这般招呼,朱掌柜就会没完没了把这双皮鞋擦下去。至于为什么上黄门不开鞋店,朱由旦似乎也没弄明白。我倒是听到过一个解释:上黄门人信奉“财不往外走”,街坊只要听说某人要租店开鞋店,都会毫不客气地把人家“请”出去。上黄门,这么多年来都被视为一个纳银蓄金的地方,跟这习俗有些关系吧。
上黄门不甘冷寂。上黄门人一直用心经营着这条老街。
“永吉祥”,堪称上黄门一家名店。当年的店主叫朱汉臣。朱汉臣年轻时只是一个货郎,常去泰来圩、土桥圩和外沙赶圩,脑子活,待人又厚道,攒钱开了一家日杂店,取名“永吉祥”。大年初一,好些上黄门人出门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喜欢挑“永吉祥”,图个好兆头。这一天,朱汉臣让家人早早煮上一大锅圆鸡蛋,只只涂得红彤彤。进店的街坊,不论男女老少,他都是一人两只红鸡蛋地送。公私合营时,仍用了“永吉祥”这店名。看到所挂新店牌时,朱汉臣努出一语:“顺天应人,聚祥纳瑞。”即便之后有了颇多感受与无奈,朱汉臣仍是坚守了自己这般祈福。
“我爷爷可评为‘上黄门好人’!”朱汉臣的孙子朱诗慧说道。朱诗慧打算把“永吉祥”旧址改造成一处文友雅集的场所。平时喜爱爬格子的朱诗慧,觉得上黄门是雅致之地。
吉狄马加也有这种触动。
初夏的一日,我陪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和《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的女儿魏萍一块逛进上黄门。吉狄马加看得很仔细。古街文韵,历久弥新,即便它穿越几百上千年,也让人一见如故,感到非常亲切。吉狄马加怦然心动了,赞叹这里有一股浓浓烟火气,称道:“仍有原住民居住,才叫有灵魂的古街。”

这时,我陪客人们走入静荷阁。
店主胡巧莲得知客人身份,非常惊喜,赶紧把吉狄马加、魏萍等请到茶桌前落座,并泡茶相待。吉狄马加喝了一口菜,说:“香郁回甘,味鲜甜淳,在汝城老街,竟能喝到这般地道的白茶,真是不俗。”胡巧莲笑道:“它是汝城白毛茶,采用九龙江野生大叶种二叶一芽精制而成。你看,这茶叶相间,白露显露,汤色杏黄明亮。”一番交流,吉狄马加非常高兴,主动邀请胡巧莲一块合影,跟胡巧莲说:“这么好的茶,一定会让人喝出上黄门老街原味来。”
是的,稍稍一品,静荷阁也有一种“香郁回甘”的韵味。
当年城里趋之若鹜的娱乐窝,要数南薰门子城上的紫烟楼。但说到喝茶好去处,上黄门的静荷阁算是其中一家。静荷阁的主人姓胡。胡氏痴茶如命,当初不顾兄弟反对,竟把祖上田土卖了大半,再在上黄门盘下一店铺,作了茶楼。怎么取个名号呢?胡氏站在街上,愣愣望着门头。“胡兄看个啥?”有人问话。胡氏侧身一看,原来是素日茶友周源公,顿时大喜,连声地:“有了有了。”周源公不解:“啥有了?”“茶楼有名号了。”胡氏说。周源公左右看看,仍困惑地:“呵,名号在哪呢?”胡氏冲他说道:“在贤弟嘴上!”周源公这才恍然,胡氏要让自己取名。也算胡氏找对人了。周源公,长塘周家人,一个肚子里灌满了墨汁的邑庠,曾参修《桂阳县志》。刚好胡氏的小女儿捧着一只荷花跑了过来,发现有客人与父亲在一块聊天,便忽地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站住了,连怀里的荷花也再没晃荡一下。周源公冲她看去,忽地愣了愣,说:“哪用得上周某取名号?你丫头把名号捧来了。就称静荷阁。”胡氏大喜,邀周源公入店喝茶。周源公见静荷阁弄得极为雅致,兴奋不已,当即提笔从其诗作中抄录两句赠与茶楼:“香风水面莲花净,新月墙头竹影低。茶话不忘三笑处,殷勤相送过前溪。”于是乎,店、名与诗句三位一体,再加上店里挂有进士所赠的一幅《玉臂藕图》,题款即是“玉腕枕香腮,荷花藕上开”一语,构成了上黄门人文一景,雅士乡绅纷纷来这品茶论道,吟诗作赋。
后听街坊说到,静荷阁的老板去了衡阳,不仅把多年攒下的一笔积蓄交给守军,而且自己挥起大刀冲上炮声隆隆的战场。
是的,他也是上黄门的耍刀武师。令人唏嘘的,这么有功夫的上黄门人,再也没回到他熟悉的上黄门。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有一日,胡巧莲与我等文友来上黄门逛街。喜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的胡巧莲,刹那间有了一个念头:不妨来这开个茶楼,得几分惬意多好呀。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子,茶楼很快开张了,并以自己的笔名“静荷”作为店名,称“静荷阁”。无巧不成书,胡巧莲这时才知道,“静荷阁”本来就是上黄门一家老茶楼的名号,而且她也是胡氏后人。天之造化,其实有其机缘。后经考证,“静荷阁”,取的是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中的“静”……
上黄门,注定是一个跌宕起伏、屡见奇观或创造奇迹的地方。
上黄门东门口的朱氏总祠,它一度成了“大礼堂”,万人大会在这里召开时,即有锣鼓喧天、彩旗漫卷的场景。那年,县里给每个公社配发新款电影放映机,发放仪式的当晚,十几台放映机同时在朱氏总祠大院子放电影,让上黄门人以及周边街坊眼花缭乱,直呼过瘾。后来,这座大院改建成每天弥漫着香酥味的县饼干厂。十六岁那年,高中毕业的我,就在饼干厂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岗位。白天或晚间都上一个半班,多做半个班的饼干,可多领几毛钱。是的,一个班也拿不到一块钱。但那时一块钱可以邀上几位发小吃遍整条上黄门。中秋节前,月饼成了抢手货。黄春森跟我说,当时他父亲开了上黄门新时期第一家私营南杂店,半夜就得去饼干厂排队批发月饼和撒满黑白芝麻的桃酥。上黄门曾经也有饼干作坊,叫“荣顺馆”,它做出来的饼干,咸味中裹挟着甜蜜,甜味中夹杂着咸香,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挑逗,让上黄门人吃出了一种“梦里寻它千百度”的心绪。
如今,朱氏总祠创办了祠堂展陈馆,集中呈现汝城九百多座古祠堂不一般的风貌。
上黄门还有一祠堂——黄氏宗庙,游客可在这里赏戏听曲,祁剧、京剧、花鼓戏和黄梅戏节目轮番上演,引得人们不断拍手叫好。黄氏宗庙曾做了二十几年盐仓库,之前储存过茶油,旧时还一度成为商品集散地。黄氏宗庙最显高光的时刻,当属秋收起义时,革命武装连克桂东、汝城两县,继而在这座黄氏宗庙里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

生活变迁之下,阳光和风尘把上黄门当成了一卷宣纸,在上面泼洒墨色,时而浓烈,时而疏朗,才让人有了铭记,也有了沧桑的唏嘘。
而这时,我正伫立在上黄门街头,看到那一砖一瓦、一楼一铺,好像又将自己重新拉回到了年少时的日子。上小学,念初中,我在上黄门来来往往穿梭了七八个年头。
有个周末,我和一同学上街买作业本。我们回家时刚走近上黄门街口,突然炸雷下大雨,只得跑进一家面馆。
一百年前,它是一间做布匹生意的店铺,名称“庆昌祥”,老板叫陈舜臣。青布皆是陈老板自己染的,几口大染缸摆在苏仙岭脚陈家村的作坊里。后来听好友陈一帆介绍过,他曾祖父陈舜臣的手艺属其家传,但数陈舜臣把这生意做得无比红火,也成了一名德高望重的乡绅。1926年,他在陈家村盖成一座大宅院,朝门上有一“三君名家”的题额,显得格外含神蓄韵。1934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这座院子成为彭德怀率部攻打苏仙岭战斗的临时指挥部。值得骄傲的是这宅院至今保存完好。当然,他最好的口碑留在了上黄门。有些街坊买布时,还可以在“庆昌祥”赊账,但陈舜臣从不催款,一旦得知赊账者家境贫寒,又会将他从账上将其名字删去。过年时,陈舜臣一定会给上黄门的每一位古稀老人送上九尺布。
记得当时那场雨下了好久,我和同学没法赶回家里吃午饭。我的同学摸摸肚子,不由叫道:“肚子饿扁呐。”过了一会儿,两只碗魔法般摆到我俩跟前。原来,店里的阿姨刚才听到我同学的说话声,便端来了两只碗。碗里没面条,只有大半碗煮过面条的水,不过放了点盐和葱花。回家后,我跟妈妈说起这事,站在旁边的同学抱怨道:“面馆阿姨是个小气鬼,几根面条也舍不得放。”我也附和着。妈妈说:“面馆里的面条是公家的。她不做损公的事,要表扬。你俩又没饿晕。”
再说一件事,我少年时最尊敬的一个偶像,就住在上黄门。
他叫朱石祥,参加抗美援朝时受了重伤,双目失明,左手也炸断了,抢救几天几夜才醒过来。那年,朱石祥才16岁。朱石祥回国后,被安排在湖南省荣军医院疗养康复。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主动要求回到老家汝城,并和爱人一块安置到了县伤残军人福利厂。朱石祥身残志坚,用单手协助爱人铺棉被,摸索着搬布匹,以这种方式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几乎每个学期,朱石祥都会应邀来到上黄门旁的城南中学,跟我们学生讲述志愿军英勇作战的故事。那时,我听得热血沸腾,连小拳头也攥了起来。初二那年,我以他的事迹刻成一套幻灯片,叫《英雄朱石祥》。在上黄门发小家的阁楼里用手电筒放这部幻灯片时,赢得了不少喝彩声。秋时,与同班同学何雪浪一块在学校出黑板报,我也写过这位英雄的故事。
我记得,上黄门当时住着好几个老战士。他们让老街有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是呵,上黄门每一步路、每一个店铺,都映射出曾经奔波的身影;每一片瓦、每一块青砖,都在诉说着千百年来留下的悠长挂念和它曾经的漫长岁月。如今,经过一番修缮的上黄门,唤醒了老街记忆,也唤醒了街坊生活。于是,人们纷沓而至,行走在历史与当下的融汇、古老与鲜活并存的老街上,温故知新,鉴古思今,寻找昔日悠长韵味的同时,也可欣赏到汝城这一条充满地域文化符号的老街所演绎的新传奇……


王琼华,笔名王京。籍贯嘉禾,生于汝城。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美协会员。湖南电影评论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入选作家。全国文代会代表。曾在郴州市文联工作。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公开出版《还我风骚》《官方女人》《咣当》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29部。
来源:红网
作者:王琼华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