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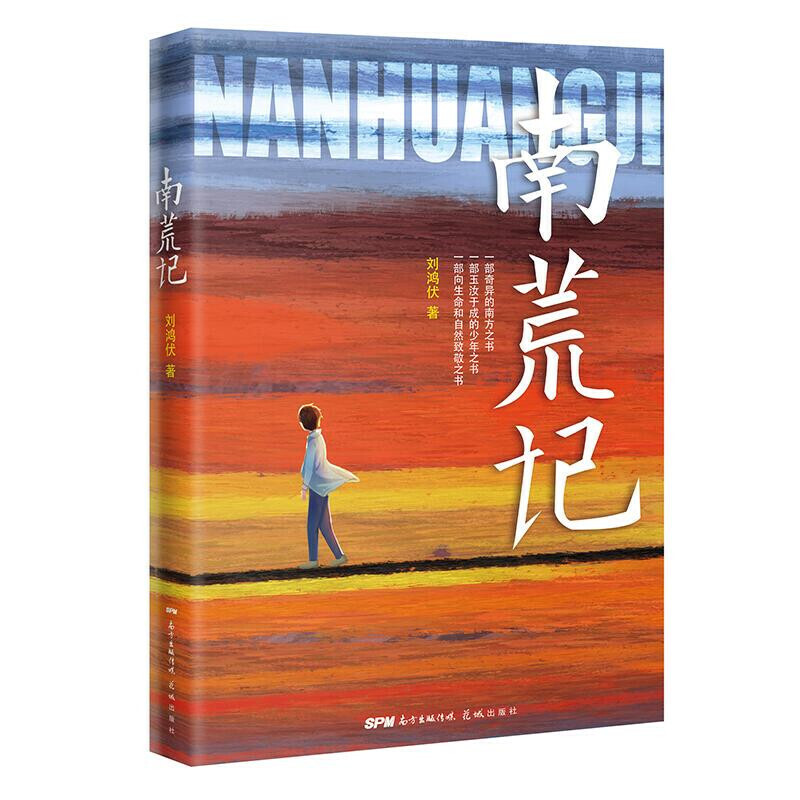
刘鸿伏长篇小说《南荒记》图书封面。
文学话语的实验与创新
——论刘鸿伏长篇小说《南荒记》语言艺术
文/张建安
刘鸿伏长篇小说《南荒记》(花城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突破了一般抒情性、散文化小说相对短小的局囿,做到诗性、抒情性和故事性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家对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技巧融合的探索不同凡俗。特别是小说中南方乡土人物个性化语言,富有寓意的魔幻话语和象征性语言自然融汇,让小说显得隽永而富有韵味。
一、南方方言融入乡土叙事。《南荒记》以作家童年少年生活为参照,通过文学话语的苦难叙事,表现出特殊年代的集体迷茫和个体忧伤。刘鸿伏来自古老的梅山腹地,梅山文化是湘中地区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保留着丰富的原始文物,存留着人类原始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等文化信息,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属于中国文化两大主流之一的荆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脉,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共同架构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南荒记》对方言的合理运用,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历时性、乡土味及地域色彩。小说中的方言土语所呈现的特殊审美价值,读者在艺术审美中感受湖湘文化的独特意蕴。小说大量使用充满乡土味道的方言词、修辞、俗语和歌谣等,读者可通过其语言蕴含的自然感,较好地体会作家精心描画的“湘中世界”,因此,《南荒记》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野趣和蓬勃的生命力。
阅读《南荒记》时,感觉是身处于湘中巫风氤氲之地,仿佛是在跟当地的民众对话,让人情致盎然。如小说写刘务童年的诗意时光:“箍箩大的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照着刘务和爹,还有晚归的农人,以及这尘世上的事物,恍如古老的剪纸。”“刘务听三麻子这么说,心里吓得不行。东山一角,月亮已露出半个头了,凉飕飕的风吹在脸上,刘务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背后仿佛有人追着自己跑,壮起胆子回头看看,又只有自己的影子跟着。转过一片竹林,听见林子里沙沙的响声,好像有人站在高处朝自己撒沙子。”这里的“箍箩大”“凉飕飕”“撒沙子”等都是湘中一带的方言词汇,用在这里别有一番韵味。“方言叙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野气横生的文学现象,充满着人间烟火与民间文化活力,叙事的现代性,使之散发出一种生动的异质性与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刘鸿伏《南荒记》中虽然运用了方言特色的一些词语和表达方式,但他没有任由方言土语在小说叙事中铺排恣肆,而是很有节制和技巧的,并不影响阅读节奏感、流畅度,而能够产生一种魅惑感和别有韵味。让平凡不过的乡村场景、物事,平添许多韵致。文字中散发出一种清新自然,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油然而生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二、诗性文字表达乡村情怀。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也是语言的艺术,刘鸿伏是一位语言意识很强的作家。《南荒记》语言流畅顺达,极具美感。小说的语言有隐喻性和跳跃性,有弹性亦有张力。可以说,《南荒记》就是刘鸿伏文学话语活动和驰骋的实验场。《南荒记》在文本叙事中大量使用修辞,有形象生动的比喻、整洁凝练的排比,有寓意深刻的象征等,运用独到,想象丰富。特别是小说中湖南乡土语言、人物个性对话和象征性表达相互交融,使小说显得清丽隽永,诗意盎然。
文字诗意灵动。刘鸿伏深得文法之妙,其小说语言清新、鲜活而灵动。如“夕阳像满世界流动的金子,辉煌到无以复加,风一样跑跳的少年仿佛金帘子上跃动的一个光点。” “从破旧的木窗外涌进来的,一半是月光,一半是雾气。”“山里的岁月总是完整的,缓慢、清澈。没有灯火,更接近自然之道,睡和醒都跟太阳同步。”前一句写月光安静,而用一个动词“涌”字,便写出了月光的动态之美;后一句说岁月“清澈”,凸显出山村的寂静和纯美。还有“那鸮鸟是不祥鸟,平时不开口,一开口就会有死人的事发生。鸮鸟在樟树上连续叫了三声,第一声短促而急迫,突如其来,让村子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吃了一惊并开始忐忑不安,怀疑有祸事落到自己或者家里老人头上。第二声起伏悠长,带着拖音,好像要把什么不吉利的暗示送到每一双耳朵里去。第三声,似乎是仰起脑壳朝天上叫的,那声音落下来时,仿佛极其锐利的铁屑,散落进人的心里,能割伤世上任何东西。”这里描述“鸮鸟”的三声鸣叫,魔幻而尖新。
风景情韵交融。刘鸿伏一生好学不倦,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之阅历丰富,善于思考,所以他的小说语言富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小说中不少地方情理并茂,具有丰沛的文化意蕴。如“月下草垛丛中,藏着村中男女的隐秘,仿佛苦难岁月里难以描述的秘境。一些微妙的声响和熟悉的身影,让月光和村舍里不为人知的情事,花一样开在朦胧处,开在草垛以外的红尘岁月,让苦难的生活有了些许甘甜和回味。在乡间,偷情原本是一种让人不耻的行为,但因了草垛和月光的掩护,就有了诗意。许多时候,一个村庄都能原谅。”“刘务看苍穹浮云,忽然就明白世上的人和事,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会消失,一切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浮生如寄。”这其中既有苦难人生的喟叹,也有哲学层面的思考。“这天地人间,除了风雪,万事万物都不语、不闻、不见,进入参禅的境界和神佛的境界。雪地里挑柴的少年,幻化为一个小小黑点,像一个执念,不停地朝前移动着,仿佛一只渐渐隐匿不见的蚂蚁。”这里抒发的是人生的浩茫与无奈,印记着沧桑岁月的流影波光。
感觉转换修辞运用。“感觉转换”又称“通感”,它是把两种或多种感觉沟通起来,调动多种感觉器官,从不同的角度去状物抒情,以增强艺术感染力,使语言表达显得新颖、别致,耐人寻味。心理学的有关实验也表明:人们这种感觉相通的联想是完全可能的,它是一种正常的感觉挪移、转化和渗透现象。如“刘务躲进柳树阴凉里去,知了的叫声密密麻麻落在脑壳上。”作者在这里运用了积极修辞中的“通感”手法,“叫声”是一种声音,刺激的应该是人的听觉系统,但作者说成是“密密麻麻地落在脑壳上”,刺激的是人的“视觉”系统和“触觉”系统,实现了感觉转移。又如“刘务走出堂屋,太阳像一朵向日葵开在天上,他听见液体的光从屋檐倾泻下来,哗哗地落在台阶上。”作者在这里频繁地运用积极修辞手法。“太阳像一朵向日葵”这显然是比喻,说“光”是液体,这是视觉转移,它“从屋檐倾泻下来”表现出光的动态,至于它落在台阶上还发出“哗哗”的声音,这显然是视觉转换为听觉了,足见当时太阳光的强烈和灼热!“晚霞像胭脂一样在西边天际流动,滚烫的落日‘扑哧’一声掉进山那边的大河里去,惊起一滩鸥鹭。”落日西沉是可视可见的一种情景画面,用‘扑哧’一声激发听觉系统,写出了太阳下山的突然与律动,巧妙传神!再如“撑船的人戴斗笠披蓑衣,出没在烟波里,那篙,斜进浪涛去。”“斜”本是形容词,在此起到动词的作用,“斜进波涛里”显得有情趣,有韵味。“阳光忽然寂寞,竹凳和灶屋都寂寞了。屋角西边桃树上的蝉声,落下来,仿佛落到苦日子的尽头,隐约没了。”这些充满弹性和张力文学语言实验,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轻松和快乐,不经意间可能会心一笑或拍手叫绝!在《南荒记》中此类隽永清新的句子还很多,如“那寂静就如一匹无涯的丝绸,将天地间的一切笼罩并且无有罅隙。”“偶尔,他会关上那门,隔断一河恼人的涛声。”这些诗性文字点亮了文本,也让读者获得了阅读的惊喜。当然,作者在运用诗意语言的同时,也积极从生活中吸取语言为我所用。如用“天烂了”说大雨滂沱,“硬翘翘”指人的死去,用“一对油盐坛子”描述人关系密切,形象生动,且散发出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
三、魔幻话语虚化感伤岁月。《南荒记》主人公刘务和村人生活在巫风遍地的“南方”似乎万物有灵,仿佛到处充满了神秘与魔幻色彩。如上百年的老树,那棵高入云霄的板栗树,砍之前要做法事,刘务被一把短柄飞来的利斧瞬间劈进前额。伙伴三麻子的爹为了救刘务,不得不破了祖师爷传下来的禁忌,使用了“强盗水”。会使用“强盗水”的人,在乡间很受尊重,他们也许就是上古已经失传的医术在当代的传承:施术人在伤者筋骨断处先绑上去皮柳枝,使断了的筋骨连接,再用清水一碗,画了符、念了咒之后,喷在伤处。然后还会敷一种秘制的草药……“强盗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几百年来,没有人能说得清。
魔幻的乡土与神奇的乡民。一部《南荒记》,简直就是一部湖湘民间人物的“草根杂传”。刘务的小伙伴三麻子的爹,外号利猴子,是巫师。三麻子对刘务他们吹嘘自己的爹会法术,可以把全村的鸡蛋都运用搬运术搬到自己家里去。后来三麻子说出自己家吃的是大樟树上的白鹭蛋——至于是不是也用了搬运术,小说家隐而不谈。三麻子他爹很会打草鞋,也会梅山呼蛇术。如果太久不见荤腥,利猴子就会到人迹罕至的芭茅大山去,作法呼蛇,呼蛇的利猴子法力神奇,有点巫公甚或“奇侠”的味道,最终他会拎了黄纸伞和巨蛇下山,吃蛇胆、炖蛇肉……他曾经逗刘务,要吃他屋里的辣椒炒泥鳅,就要做他的干崽。等刘务真被老锯匠的利斧砍中前额,他不惜折损自己的阳寿也要用祖传秘术“强盗水”救治刘务。特别是写到那位带刘务去挖草药攒钱好做一条裤子的隔壁稳叔,在村里算半个采药人。面对刘务的央求,稳叔并没有说行或不行,但刘务最终还是跟着稳叔到了人迹罕至的绝地孤峰金鸡岭,可能因缺少稳叔的攀山本领,刘务远远落在后面。稳叔却轻轻松松,见刘务落在后面,只好坐在一片岩石上等。稳叔慢腾腾卷了一支喇叭筒烟,用打火石打燃纸媒子,点上,烟从鼻孔里一股一股冒出来。稳叔宛如一位得道的神仙,让少年刘务肃然起敬。
此外,《南荒记》还写到乡间、民间各色人物形象,如阉鸡的阉匠和拥有神秘莫测传奇经历的瓦匠。刘务那被关在坚固木笼子里的疯叔,在河岸边捡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露水,并把她含辛茹苦养大的驼背四爹,与屠夫打赌赢了许多猪板油的毛五,刘务的老师陶爱爱,刘务的老老舅,刘务的娘亲,刘务的爹,刘务的奶奶,甚至刘务年纪尚小的弟弟细伢子等……都是《南荒记》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家就像是一个湖湘说书人,不紧不慢地讲述乡土民间故事,回忆着乡村的流年往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又很接地气的民间奇人。他们虽然都是草根人物,但是能救灾救难,有情有义,心怀良善,他们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又确确实实是行走在湘山楚水的活菩萨。
散文化书写与抒情气息。抒情性作品通常呈现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诗意想象空间。作为一部小说,《南荒记》的叙事结构和节奏带有散文化倾向。作家采用细腻的笔法,用最充沛的情感来抒发自己对故乡最真诚、最纯洁的爱。小说中既有将近乎散淡的日常生活书写,也有如诗如画的风景描绘,这让作品变得很唯美,读起来很畅快。如“刘务看见从山那边的大河里飞起几百几千只白鹭,在最后一抹夕阳里,它们银色翅膀的边缘涂上了一层金粉。几千只翅膀银光闪闪、金光耀眼地从大河那边鼓涌而来,越过一排奶子一样的圆形山丘,煽动的翅声像潮水由远及近,淹没了整个村庄,声音浩大得有点惊天动地,让人心神不安,它们最后都落到了大樟树上去。那棵巨大无比的樟树顿时像下了一场暴雪,变成了白皑皑的一棵树。刘务看白鹭鸟落在樟树上,最后一朵晚霞也落在樟树上,三麻子家的瓦屋顶,这个时候就升起第一缕炊烟了。”这一文字写得浪漫抒情,富有诗意。作家很注重人物活动环境的营造,尽管小说书写的都是小人物,都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现实里,但小说却为人物活动安排设置了充满诗性和人情的社会环境——艰辛的岁月里也有人性的美好。如“刘务睡不着,侧耳听村子里的动静有些诡异,仿佛在月亮下面,在村子上空,飘动着黑白的无常和人形的烟雾,还有断断续续、时有若无、轻如落叶的脚步声。几只土狗在静夜里朝天空的月亮拖着长腔吠叫,声音粗哑凄凉。”“风过渔梁坝,吹过头顶,翻动着大地的书页,人间的苦难和欢喜,仿佛就是长进血脉里的段落,删也删不掉,抹也抹不平。但这部书却是沙之书,永远无头无尾,无休无止,你看见的文字会很快消失,但它们又会在别的章节、别的页面不断地再生长出来,而你却永远无法找见。渔梁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惊叹号,刘务和老老舅,只是这部大书里永远找不见的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千百年来,这一方乡民不但克服了偏居一隅、条件苦寒的生存之苦,而且顶住了难言的心灵焦虑,他们在这奇特的逆境中不屈不挠、奋斗不息!作家在叙述故事、推动情节时,还不时来点幽默,但刘鸿伏的幽默不是那种轻松的谐趣,也不是开怀放肆的大笑,而是一种带着淡淡苦涩的微笑。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评价,不是那种尖刻的、金刚怒目式的,而是淡化和过滤了愤激之后的冷静言说。他的幽默,是在历经了起落沉浮、坎坷波折的道路,或阅尽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人生世相之后超拔的人生风度和写作心态,是对世事平静通达的洞彻以后而产生的会心反讽,苦涩但不绝望。
(本文系教育部“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编号:47)阶段性成果之一。)

刘鸿伏,第九届湖南省青年文学奖获得者,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集和文物文化专著36部。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选入中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长篇小说《南荒记》为天猫旗舰店热销榜和京东书城好书人气榜常客,短篇小说《鸬鹚出逃记》改成同名皮影戏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散文书画合集《屋檐下的南方》入选晋版好书榜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年度好书优秀原创出版奖。散文《父亲》与朱自清、梁衡等名家名作选入中学教材三大版块之一的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文,选入人教版新课标高二语文及人教版高等职业教育语文课文、沪教版初三语文课文。

张建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人才“三百工程”文艺家人选,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曾获第二届湖南文学艺术奖、第五届湖南省文艺评论奖、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和湖南省首届湘江散文奖。
来源:红网
作者:张建安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