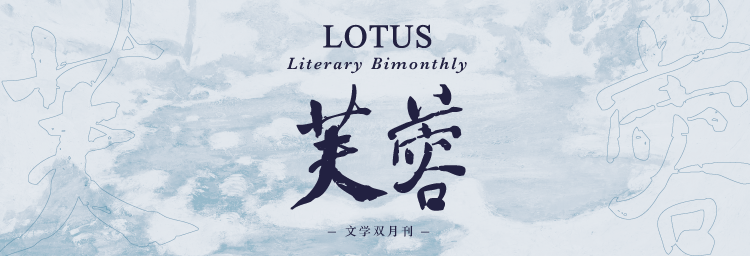

裂叶独活(中篇小说)
文/万宁
在地下车库,启动车时,我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时间,八点一十五。略略有些沮丧,怎么又晚了。一脚油门出了小区,而街道上正在拥堵。我混入车流慢慢行驶,绿化带上的红枫与银杏,扑闪出浓浓秋意。左拐后上了直行快速道,车流量大,快速道无法快速,四个车道的车辆不疾不缓。我突然头皮一麻——在第四车道与第三车道的白线上,有位女子迎着车辆逆向走来。她长发波浪般散开,笑容羞怯,眼睛却望向远方。她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周围的车流她似乎看不见。她若有所思地往前迈步,光脚踩着黑色一字拖鞋,浅棕色布裙刚刚过膝。她走着走着,手里的一串钥匙掉了下来,她暂停步,满脸含笑地弯腰拾起。弯腰时她那丰硕的双乳在一件宽松的白T恤里乱动,她显然不知道自己没穿胸衣。最糟糕的是她走几步,手里的钥匙又掉了下来,她又去捡,也不管迎面驶来的车辆。像是在无人的空地上,自己与自己玩着重复的游戏。
我心口发紧,在如此密集的车流中逆行,随时有被撞到的可能。我的车走在第四车道,在这女子直腰抬头的刹那,我认出她是弟弟丁冬晓的同学的妹妹,我想把车停下来,把她扶到路边去。我刚有停下来的意思,后面的车辆便开始鸣笛,这车流完全把我裹挟了。没有果敢停下,便与这女子擦肩而过,且渐行渐远,她在我车子的后视镜里小成一个黑点,到最后那点也消失了。
车停到单位车库时,我才想起给冬晓打电话,告诉他我刚刚看到的场面,冬晓说他这就联系同学,接着叹了口气,像是在感叹这妹子遇人不淑。
妹子叫罗芸,是个全职妈妈,曾来过我单位。六月里一个周三下午,窗外合欢树粉白色的花开得声势浩大,腻腻的香甜味密布在空气里。在我办公室,她吞吞吐吐说了一大堆琐事,而真正要说的,她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其实我挺怕她讲出来,讲出来了我根本无能为力。都知道妇联是为妇女维权的,可是维权这件事有时候很玄乎。她嘴唇抿得紧紧的,忧伤呆滞的眼神看得我扎心,而我又本能地躲避。谈话在停顿或是长久的沉默里。忽然间罗芸起身,说要去接孩子。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六岁,小的三岁。我跟她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就出去工作吧。她嘴角扯出一丝浅笑,低声说,没地方要我这种人了。她说的是事实。女人生娃带娃几年后,哪怕你是研究生学历,也难有单位要你了。她抬眼再看我时眼眶就泛红了,我装作没看见,脚步随她往外走。我心虚,不敢与她延伸任何话题。望着她走远的背影,我拨通弟弟的电话,接着又按下。冬晓当年还想追她,最终临阵脱逃了,他不正经地说熟人不好下手,到时没追上,只怕与她哥哥同学也做不成。
弟弟这调皮话只能说明他们缘分浅,而此刻,我有种后怕,只是说不清这后怕来自哪里。
我在办公室坐了好长时间,罗芸光脚趿着拖鞋向着车流大步行走的情景依然挥之不去。天已经很凉了,她的穿着还在夏天。我一连喝了两杯热茶,心绪还没平静,这是周五的上午,整栋楼里鸦雀无声,没人敲我的门,以前就很少,现在就更少了。上周正式发文了,解决了我的四调,享受正处待遇,剔除了副处实职。其实我来不来,没人管了,只是我还不太适应,上班总怕来晚了。
没想到将在妇联退休,好多人为我抱不平。坐着无事,我开始清理柜子里的书及其他杂物,该丢的,就在这里丢了,省得到家里又去清。
最下面的双门柜里,有几个牛皮纸档案袋,里边装了我的工作笔记,我把它们扔进废纸堆里,都是些又沉又重的硬壳本,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废书,家里没地方放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什么东西都得做减法。
门在这时被敲开了,办公室主任唐甜犹犹豫豫地移步进来。东西摊了一地,像是被人看到内衣,我用一只脚踢了踢那些书与本子,唐甜的目光跟着我的脚扫了过来,看不见的笑在她脸上略略滑过。她定睛望了我两秒钟,而后口气很正式地说,丁主任,孟主任交代,下午这个会您还得参加。她又解释,准备了好久的会,要人的时候,偏偏这个时候,单位连着有好几人居家隔离。我也听说了这事,孟主任觉得这个会议重要。
下午两点,我就到了会场,主席台上方电子屏的字幕已经显示——“家庭助廉 团团圆圆”。这是个以中秋节的名义召开的“一把手”家属会议。我在妇联待了若干年,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开一个这样的会。正想着,见孟主任在主席台挪动名签,她把她自己的名字放在最边上,让纪委监委、市直机关工委等部门的放中间。我佯装没看见,心里却在叹服,80后的成熟不可小觑。孟主任是年初来妇联的,很多人说,她来只是走个过场,上个级别,多个经历。也因她来,别人说我是到手的鸭子飞走了。我干了若干年常务副主任,而主任的位子也空了好几个月,所有人都认为我接主任一职是板上钉钉,可悲的是我也这样想。可最后是年轻漂亮的孟主任来了。她齐耳短发,一双眼睛在黑框镜片后扑闪扑闪,她穿的套装得体庄重,颜色永远是深灰、深蓝与黑色,但款式却换得勤,就像她的头发,看似随意,其实细心打理过,至少修剪频率高。
我戴着口罩胸前挂着工作人员的蓝牌,站在会场后面,注视着陆陆续续进来的参会人员。大多是女人,当然也有男人。来这的男人低调得很,专拣角落里坐。女人啥样的都有,明明是家属,却带着领导范,装扮阔绰不说,神情还不可一世,在会场走来走去。不过明白人还是多,她们终究知道这会议的性质,所以安静谦卑是大多数人的表情。
台上几位领导轮番讲过话后,灯就暗下来。播放警示片是会议的重要内容。片子里的犯人是很多人的熟人,几乎都曾是某县区某部门的“一把手”。这些人我都认识,有的甚至还共过事,也算是朋友。他们在片子里失魂落魄,痛哭流涕,后悔不已。我视线有些模糊。好好的一辈子,怎么就万劫不复了?内心正五味杂陈,我的右肩突然被人暧昧地掐了一下。我扭转脸,盖玥坐在我后面的座位上。我猫腰过去,她往里挪了个位子,我坐到她的位子上。我们没说话,眼睛盯着屏幕。冷不丁她用嘴凑近我的耳朵,说了句什么。我吓得捏了她一下,她却正襟危坐,静静地看着片子,我怀疑自己幻听了。
盖玥的老公饶酉冰是枫城某某委主任,本来传说他要升的,可是他秘书生涯唯一服务过的人进去了,他也就悬了。最后播放的警示片在空气里炸锅了,会场陷入死寂。我屏气凝神,他们曾是枫城的“一把手”与“二把手”,此刻片子里的他们穿着横条纹套头衫,神情与前面出现的人毫无二致,我无法将过去的他们与现在的模样叠放在一起,只能说曾经的光芒已经灰飞烟灭了。片子放完,灯光刺眼,我与盖玥紧握在一起的手缩了回来。大家霜打了样缓缓移步,难以言说的表情在空气里沉寂。
好久不见盖玥,见着了,自然要黏糊一下,吃个饭聊个天什么的。在湘江边的河畔小院,我们选了个可以透过玻璃看到一个回水湾的包间。盖玥先泡上了她自带的正山小种,茶汤鲜亮,香气浓稠。盖玥嗞啦啦地喝上一口,吁出一口长气,而后说憋坏了,一下午没喝口茶。会场明明是泡了茶的。我咬嘴轻笑,说盖玥,你比从前娇气多了。盖玥送往嘴边的那盏茶,停了片刻,又还是送到了嘴里,只是少了刚才的嗞啦声。放下茶盏,她白了我一眼。这年头,女人不好好娇自己,谁会娇你?说完,还不忘朝我哼了一声。
我有点无趣,不会聊天的毛病,老改不了。好在盖玥不跟我计较,她神秘地告诉我,她发现儿子在处女朋友,她想问又不敢问。儿大不由娘。我一脸鬼笑,饶冰过三十了,早该找了。她不动声色,不咸不淡地问我啥时当外婆。她这一问,我脸上的笑就有了喜悦,这个喜悦我没法掩饰。我说,明年春天吧。盖玥听闻,牙巴啧啧地咂起来,说就你命好,女儿不但会读书,这事也省心。我忍不住嘚瑟,笑意在脸上放肆,盖玥没来由地横了我一眼,切,当初要你找何岸,你还不肯,委屈你似的。
菜上来了。鲫鱼豌豆酸菜汤、樟树港辣椒炒肉、凉拌芫荽菜。我先喝汤,这鲫鱼新鲜,汤煮得奶白奶白的,在喉咙里轻轻一滑,便口齿留香了。我嘟起嘴连说几声好喝,盖玥夹起几根芫荽菜往嘴里送,然后敲了敲碟子,说多吃点,这个养颜补血。我差点爆笑,盖玥眼睛里射出两把利剑,说就知道你文盲,它可不是芫荽菜,是当归苗!比芫荽菜贵几十倍。我满眼狐疑,夹起一根在鼻子前闻了闻,当归香果真浓浓袭来。我吃了一筷子,入口涩涩的,好在有回甘。盖玥说,女人吃东西,就要吃对自己身体好的。凉拌当归苗,比当归的药味淡些,似有似无,只是我胃里的怪味突然冲了出来,幸亏动作快,我侧身捂住了嘴。你,你啥毛病?盖玥丢来嫌弃的眼神,我还没缓过劲来,那残留的冲力仍在作祟。
我眯紧了眼睛,摆着手。
(节选自2024年第5期《芙蓉》万宁的中篇小说《裂叶独活》)

万宁,湖南岳阳人。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作品被多家选刊多个选本选载,已出版《城堡之外》《麻将》《纸牌》《讲述》等。
来源:《芙蓉》
作者:万宁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