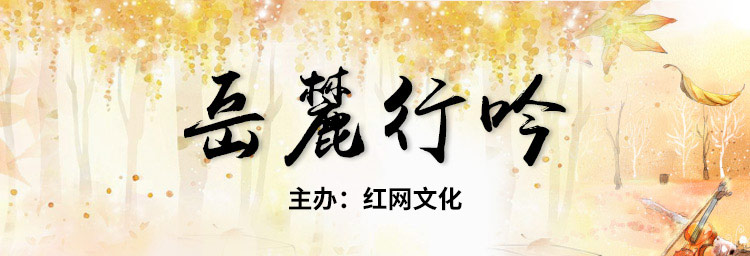

父亲的油菜花田
文/郭建中
父亲走的那天,湘江的桃花汛还没到来。凌晨四点多接到母亲的电话,我没有多想,驾车就往回走,泪珠子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路过当年父亲栽下的竹子林,它们似乎在春寒料峭里暗自抽泣。老人说,就用这片地里的竹子搭灵棚,送上最后一程。
我蹲在老屋门槛上磨那把生锈的镰刀,铁锈混着檐角滴落的雨水,在青石板上洇出暗红色的溪流。春燕掠过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父亲蹲在堂屋门口修蜂箱,木屑落在刚写好的春联上,他说:“莫要慌,墨迹干了就看不见了。”
一
1982年的春分比往年都冷。联产承包的合同纸还带着油墨香,父亲把摸勾分到的五亩多薄田走了十几遍。烂泥巴黏住他的胶鞋,每拔一次脚都要带出半斤春泥,他却笑得像拾了金元宝:“泥巴越黏,稻穗越沉。”
那年,我总看见他蹲在田埂上数稻种,糙黄的手掌摊开着,仿佛捧着整个春天的希望。总看见他起得比别人早,围着一条长长的旧毛巾,借着微弱的星光就赶去车水,悠悠的水车声伴奏我的整个童年,至今仍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乐章。略微瘦削的他身体却很结实,背农具、打肥料、刨田坎、挑谷子、犁田插秧是样样在行,干净利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政策好,多打点粮食,能吃饱饭。”他说他苦了一辈子,现在累点,但是可以饱肚子,挖荠菜过苦日子的那些年不想再有了。
谷雨前夜,他忽然把全家叫到灶屋,煤油灯在土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我盘算着养长毛兔。”他蘸着茶水在桌上画圈,“公社老刘说浙江那边收兔毛,三十块钱一斤,好的卖六十到九十,划算。”
兔场是红砖砌的,兔笼是用竹片搭的。一年上百只长毛兔,口粮不够。每天天刚发亮,父亲就背着竹篓去扯青草、摘树叶,露水把他的裤管浸得能拧出水来。有次我跟着去,见他蹲在塘边搓洗沾满兔粪的围裙,手指节被冷水泡得发白,却哼着花鼓戏:“刘大娘我笑呵呵啊,叫我过来洗裹脚……”
深秋时兔毛卖了钱,他连夜走二十里路去县城,给我带回人生第一支英雄钢笔,笔帽上还沾着百货大楼门前的桂花香。
二
五年后兔毛行情下跌,他连夜把最后两笼兔子送到镇上。回来时军大衣兜着个搪瓷缸,揭开盖是热腾腾的糖油粑粑。“养蜂,养中蜂,中蜂成本不高,蜜糖价好。”他咬开结着糖壳的粑粑,琥珀色的糖丝在晨光里发亮,“我观察后山那片野板栗花、槐树花、樟子木花三年了,流蜜期比油菜还长。”
蜂箱是父亲自己一个一个打的。刨子推过杉木的清香里,总混着他熬制蜂蜡的甜腻。从1988年盛夏开始,每年带着四十箱中蜂跟着各种花期迁徙,他追着蜜源,领着我们兄弟俩跑遍县里的每个乡镇。有次在隔壁乡“百步陡”迷了路,背着蜂箱在深山里转了大半天,回来时水壶里装着野樟子树蜜,说是留给母亲治咳嗽。
最难忘那个暴风雨夜。惊雷劈断老槐树,蜂群炸了营。父亲只穿件汗衫就冲进雨幕,举着冒烟的火把绕蜂箱画圈。我和母亲举着竹匾替他挡雨,闪电劈开夜幕的刹那,我看见万千金点在他周身飞舞,恍若银河倾泻在凡人肩头。
父亲随我们在城里住了七八年,蜜蜂也养到城里来了,很多人变成了他的城市“蜜友”。“多可惜,城市公园花多草多,周边农村养蜂人少,他们看不起。”城里人生活条件好了,蜂蜜也卖不上价,父亲说很多店家都是假货,吃了不管用。真有需要的人,他一家一家半卖半送。父亲走了之后,一直还有人惦记着那些沁心的蜂蜜。
三
祖上留下来的茅草土砖房,冬暖夏凉,守护着几代人,却要年年翻新,容纳不下一家人的生计。父亲说咱们盖红砖房,房子生火时烧不着,孩子们睡个安稳觉。娘点点头,咱们穷点可以自己干。
外面有人买石头,打一方可赚两元钱,重体力活别人不敢接。父亲接过活,自己做了辆板车,一拉就是一个冬天。他弓着腰拉板车,肩上的皮一块接一块地脱。“比打一个月工都要好,攒钱建个房子。”他数着数,脸上写满了喜悦。
我放学就坐在父亲拉的板车上回家。“你以前上学也是接送,顺便也帮我推推板车。”他弓着腰拉板车,车辙在黄土路上犁出两道深沟,像刻在大地上的年轮。父亲说,“现在你们带孩子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幸福从哪里来的。”
红砖窑开烧那天,父亲在窑洞口摆了三碗米酒。泥胚要摔打七七四十九遍,他说这是跟老窑工学来的规矩。他教我把黏土摔打成方正的模样,烟囱腾起的灰云落在他鬓角,不知不觉就积成了霜。一砖窑,硬生生烧了半个月。
放在砖窑顶上的石头却烧过了,结晶成一坨。他蹲在废墟里扒拉出半截烟囱管,突然笑出声:“正好给蜂箱做保温层。”那年春节,他用红砖砌了个存钱罐,烧制时偷偷掺了从小河里捡来的彩石,出窑时竟泛着星子似的微光。
红砖房护佑我们走过四季,见证一代人成长的足迹。三十年过去后,隔壁的两个叔叔要建房。父亲说我们现在有了新房子,放蜜蜂的地方也够了,把三间红砖房、两间土砖房拆了,让给他们,乡里乡亲的,拉扯一把。
四
父亲是老初中生,村民说他有文化、人厚道,硬是把他推到生产队长。当生产队长的二十多年里,父亲总在寅时末吹响第一声哨。哨音掠过打谷场边的苦楝树,惊飞宿在稻草堆里的麻雀。村里五保户常说,这哨声比队里的公鸡还准时。
那年修水渠正值三伏,父亲把全队的饭盒收走:“晌午太阳毒,妇女在树荫下吃。”他独自挑着两个大木桶,踩着滚烫的鹅卵石挨个送白糖掺凉水。我躲在槐树后数他脖颈晒脱的皮,一层层像老樟树斑驳的树皮。
包产到户后,不用出工了,有人劝他收起哨子。他却用石灰在晒谷场画格子,张家三亩李户五垄,硬是把碎布似的薄田分得滴水不漏,还赢得一个“老先生”的绰号。分完田那夜,我看见他蹲在灶屋磨那把生锈的柴刀,月光从瓦缝漏进来,在他佝偻的背上写满未竟的诺言。
五
癌细胞是在春天里油菜花开采蜜时查出来的。他坚持要把最后几箱蜂搬到向阳坡,说南风天采的蜜能止咳。
在医院放疗时他总盯着窗外的树,有次突然说:“记得把老蜂王移到三号箱,它认路。”
病痛最凶的夜晚,他让我扶他到老屋里。柜子里还有当队长时的账本。枯枝般的手指抚过那些密语般的符号:“这个圈是给雷瘸子多记的工分……他家里苦,腿脚不好还没讨亲……”止痛片的药效过去时,他额头抵着账本昏睡,鼾声里翻涌着一千多个饥饿的春天。
最后一次放疗回来,他执意要去看那片土地。已经步履蹒跚的他,走在田埂上,夕阳把1946年那个放牛娃的身影,拉得和2022年这个佝偻老人一样长。枯瘦手指划过田野里的杂草树叶,仿佛在抚摸那些被哨声唤醒的时光。秋旱的景象在他浑浊的瞳孔里翻涌成海。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村里的电排该修修了,那些田荒了太可惜了……”
出殡那日,后山的野板栗花突然开了。成群的蜜蜂围着棺木打转,养蜂人说是老蜂王带着工蜂来送行。我跪在坟前烧那些泛黄的纸片,火苗蹿起时,恍惚看见父亲站在1982年的春雨里,蓝布衫上落满梨花,正把最后一粒稻种按进温暖的春泥。
今年清明,我把他最后没用完的蜂巢埋在了山茶树下。细雨斜斜地织,漫山油菜花翻涌如海。恍惚听见板车吱呀,转头却只有金黄的浪花漫过田埂,轻轻吻着他曾丈量过千万遍的土地。

郭建中,1972年6月出生,高级政工师,衡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曾有多篇作品见诸报刊杂志。
来源:红网
作者:郭建中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