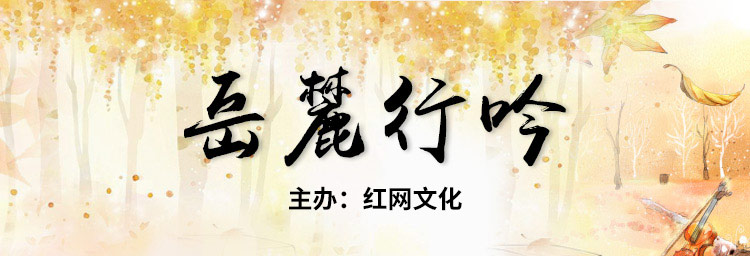

2015年,作者体验湘军航空小飞机。作者供图
古稀感怀:砚田与镜头间的七秩回望
文/刘军麒
公历十月五日,国庆的余温尚在,农历八月十四的月光已悄然铺洒。亲友们簇拥着为我齐唱生日歌的瞬间,烛火映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亲人、朋友、老同事,还有我教过的多名学生……一声声真挚的祝福,让我在烛光的摇曳中,忽然意识到:刘军麒,这个名字,已经在岁月长河里淌过了七十个春秋。
这七十年,像一卷缓缓展开的长轴,起点在湖南省安化市羊角塘镇的一个偏远农家。父母世代农耕,勤劳质朴。我从小在田埂间长大,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泥土的气息和父母“勤能补拙”的叮嘱,是我最早的启蒙。上学后,我把这份勤奋带到了课堂,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天真地以为,读书、考试、升学,会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
可命运总爱与人开玩笑。1973年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已停滞多年。我只能回到农村,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劳动。白天在田埂间挥汗如雨,夜晚回到农家木屋,我仍舍不得放下书本。煤油灯下,我一遍遍翻看仅有的教材,心里总有一丝不甘:难道就这样了吗?
转机出现在1976年。教育开始复苏,教师队伍紧缺,我有幸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走上初中教学的讲台。学校师资匮乏,我几乎教过初中的所有科目,文理兼修,哪里需要就顶上去。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便觉得一切都值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像一道惊雷划破长空。我兴奋之余抓住机会,一边教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由于多种原因,至1980年,我才有机会参加全国统考并被录取,1982年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并被作为骨干教师,派往安化县边远山区的原苍场乡中学任教。
苍场中学条件艰苦,学校远离城镇,设在大山深处的山窝窝里,教室简陋,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学生们大多住得远,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上学。我既是老师,也是他们的“家长”,不仅要教好课,给他们灌输知识,还要关心他们的冷暖与安危,好在短短四年,我和学校一群年轻教师,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乡镇,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后来,他们中有人走进了县、市乃至省里的政府机关,成为了优秀的管理人才,有人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每当想起这些,身为曾经的教师,心中的自豪与感动便久久不散。
后来,我又先后到现冷市镇原三洲乡中学、安化十中、羊角塘镇中学任教。教学重心也逐渐聚焦到理科,最终深耕初中化学教学领域。
为了教好化学,我想尽了办法。学校实验条件有限,我就用墨水瓶做酒精灯,用输液管当导管,把家里的搪瓷碗拿来做反应容器。我把抽象的化学方程式编成口诀,把复杂的实验步骤拆分成简单流程。慢慢地,教学有了起色,所带班级的化学成绩在全县统考中名列前茅,我也在县、市级教学比武中崭露头角。更让我欣慰的是,辅导的学生参加化学奥赛,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奥赛辅导员”。这些成绩,后来被安化县教育局作为改革开放十年的教育成果上报省里。
我原以为,也曾立志在讲台上一直站到退休。可命运在2007年给了我沉重一击。那年,上大三的儿子突患重病,住进医院,医生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如刀绞,当即向学校递交了紧急请假报告,暂别心爱的讲台,带着儿子辗转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寻医问药。近五年的治疗,耗尽了家财,还让我背上了近百万的债务。幸运的是,儿子最终转危为安。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安稳的生活,我向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申请延长特许假期,只身投入长沙闯荡。这座陌生的省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却少有熟悉的面孔。年过五十的我,既无年轻的体魄,又无行业经验,只能从零开始。想起自己年轻时爱摆弄相机,写过的教学通讯常被县、市报刊采用,便毛遂自荐,应了几家媒体做兼职。
初入新闻行当,比当年第一次登台讲课还难。为了拍好一张拆迁现场的照片,在寒风里蹲守整整一天;为了核实一个数据,骑着二手自行车跑遍大半个长沙;深夜在出租屋里改稿,台灯坏了就借着手机微光继续。没想到这一拼就是二十年,镜头和笔成了我新的“粉笔”,而新闻人的担当,让我在记录中重新找到价值。我始终记住,要为时代的好人立传,为家乡的好物发声。
“湖南好人”王心亮投身公益十六载,从最初的零星善举到现在的系统帮扶及常规公益行动,我追踪报道了十六年,用文字记录他为困难群体奔走的脚步,用镜头定格他助人时的温暖笑容,看着他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被社会各界认可,带动起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加入公益队伍。而对家乡的非遗与特产,我更是倾注了全部热忱。安化纸包腊肉的首创者黄建设,为传承古法工艺反复试验,我一次次往返他的作坊和工厂,记录下纸张包裹、慢火熏制的独特流程,细致描写这种“撕纸见金黄”的健康美味;还有致力于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云天阁茶业李云、湖南十八洞酒袁乐云等企业家,我全程挖掘和推动他们的特色产品走向市场的故事,从产品研发到品牌推广,一篇篇报道让家乡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最终成了湖南的热卖特色产品走向全国乃至海外。
这二十年里,我还写过社区“百姓食堂”的公益暖心故事,拍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坚守的身影,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文字与画面,让湖湘文化、梅山文化的底蕴慢慢走进大众视野。有读者说我的报道让他读懂了基层的坚守,有企业家说我的文字帮他们打通了销路,这份被需要的感觉,像极了当年在讲台收到学生家长的感谢信。
如今,我依然每天背着相机出门,案头的笔记本总在更新。有人问我古稀之年为何还这般奔波,他们不懂,这支笔、这台相机,是我这辈子的魂。就像十月五日的庆生会上,当年的学生带着我三十年前批改的作业本赶来,新闻行业的伙伴翻出我早年拍的照片,亲友们念叨着“都熬过来了”,那些瞬间让我明白,所有坚持都有意义。
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站在七秩的门槛回望,从安化田埂到三尺讲台,从病房走廊到新闻现场,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对教育的热爱、对家庭的责任、对记录的执着。月光依旧明亮,桌上的相机还在充电,采访提纲写了一页又一页。古稀从不是终点,往后我还要带着镜头走街串巷,握着笔书写人间,把安化的茶香、长沙的烟火、时代的温暖,都细细珍藏。
如此,便不负岁月,不负此生。

刘军麒,安化县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1974年参加工作,先于安化执教三十余载,后投身省城长沙新闻媒体行业。从业近五十载,笔耕不辍,30余篇论文获国家、省市奖项,摄影作品与新闻报道也屡获嘉奖。
来源:红网
作者:刘军麒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