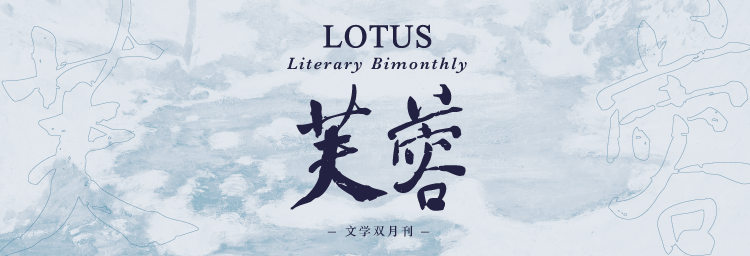

十三个半的乡愁
文/王芸
大榕树是寒信村的常住居民,一棵一棵数来,约有三十棵。榕树们散立在弯月形峡谷抱持的村庄四处。对一座有码头属性的村庄而言,流动是生活的常态。日夜是流动的,云雾是流动的,江水是流动的,船是流动的,船上承载的货物是流动的,还有会行走的人和他们的声音、心思是流动的。树才是这座村庄更稳定的生命存在,落土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将自己的根用力地、强健地、深深地扎进这座村庄的土地中,枝叶尽可能地朝着天空生长,吸纳阳光、雨露、氧气和养分,还有风动、鸟鸣、雨落、花开、冰凝的声响,慢慢地,这些树与一座村庄就长成了一体,成了村庄皮肤上的纹饰,也构成内在的筋骨。
梅江从赣南群山中奔出,以弯月的弧度流过寒信村,波不急、浪不猛,呈娴静之态,蓄鱼鲜,也利行船。江边有三棵榕树,年岁都不小了。居中一棵,像拔地而出、虎口张开朝天的巨手,微向后倾的树身上缠满虬曲交错的枝条,似有强劲的风持续吹刮,天长日久,让它袒露出了脏腑和暴突的青筋,生命挣扎努力的迹象一览无遗。树身复杂的肌理与脉络,让我分辨不清是因为藤对树的侵袭纠缠,还是因为一棵树矛盾纠结的自我繁衍,才有了如此沧桑怪异的面目。
另一棵树离它不足百米,有更加粗壮的、向四面伸展的枝干,其中一脉几与地面平行,仿佛想将指尖探进梅江中。粗粗细细的筋脉布满了躯体,但它的模样周正、挺拔,承受住了横向和纵向分扯之力,没有一点衰颓的样子,树干上寄生的蕨类植物也多而丰茂。想来,夏天它舒展开的枝叶,可为树下人提供惬意的阴凉。
此时是深冬,阳光却暖,暖过了江风吹卷而来的寒意。有一蓬阳光恰好落在盘缠的树根上,我们坐在阳光里喝热乎乎的擂茶。从大大的擂钵中,舀出浓绿色的汤汁,抿一口,鲜茶、豆子、芝麻、花生、炒米、姜、盐、油交融的香,在唇舌尖弥漫。那股独特的香,在赣南民间传承千年,传说是客家人从中原带来,曾是做苦力者快速补充体力的佳品,是赣南女人午后聚叙的茶饮,也是家有喜事不可缺少的待客美食,给尊贵客人奉上的滚烫心意。在不同的地方,擂茶的做法小有差异,但都是多种食材被反复碾磨后,各自敞开怀抱,经注水煮沸,温温一盏,滚入脏腑,暖胃,抚心,提神。
一桌子女人围桌而坐,每人捧一杯擂茶,不一会儿,从外到内都暖和起来。放眼看去,懒洋洋的阳光下,寒信村沿梅江伸展,江水与村庄之间是黄色的沙滩。据说五百来米长的河堤始建于清朝中叶,最繁华时段,十三座码头如珠穿线,在江岸边绵延。最大的当数水府庙前那一座。村人告诉我,红麻石条铺成的码头台阶,一级一级数来,有十三级半。自码头上岸,行不多远,有一座回龙祠,是寒信村的社公庙,屋顶上的青黑色瓦片,一行一行数来,有十三行半。这不约而同或刻意而为的“十三个半”,是在异乡漂泊的寒信村人彼此相认的“暗号”。
第三棵榕树有粗壮而中凹的基部,凹处经络虬突,向上分举出两翼。我们到达时,他坐在这棵树下,蓝色斜襟布衣、黑色礼帽,领口翻卷出一线白边来。阳光透过枝叶正落在他身上,也将二胡的剪影落刻在蓝衣服上。
他听见了脚步和语声,启动弓弦,二胡与他一起亮开嗓,两股声音交缠、环绕、扭结,一瞬间将时光拉向了远方。
我知道这是客家古文,一种植根民间的说唱艺术,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音律如一条起伏的河流,我不能全然听懂的客家方言在其中摇曳,浮沉,翻腾,旋转,行止。空气和阳光也漾动起来,有了水波的形态和触感。
十三级半红石台阶和梅江边的三棵大榕树,是离开村庄的一代代寒信人拉远的目光中,最后淡隐的故乡风物,又在他们归来时最先进入他们的视线。还是漂泊异乡时,在幽暗夜幕上闪烁的星光和浮动在心头的一丝牵念。
他的名字在不远的展示板上,肖南京,第五代客家古文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土生土长在寒信村。
他端坐树下的身影,叠加有无数客家古文吟唱者的身影。
来过赣州几次,我已了解客家人是生活在南方的独特族群,他们因战乱或生存需要自晋代开始从中原南迁,走走停停,为找到一处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远离故土,漂泊成为客家人无法改写的宿命。他们携带这宿命,在南方的山野间跋涉、突围、斩棘、开荒,自中原携带的血脉基因、语言习惯和文化密码,与南方水土、人文在隔膜中磨合至融合,有变化,有坚守,于是,形成了这一族群独特的生活习性、语言特征、精神面相、文化遗存。
为了在异乡建造一处安全、自洽、自足的堡垒,客家人创造了院墙四合壁立高耸、内部构造完备自成一统的围屋建筑样式,一个大家族拥抱在一起,合力抵御外来的侵扰与威胁;竭力保留中原汉语的古音、古义,形成了与南方方言不同的客家语言系统,那是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彼此身份认同的“有声符号”。自故乡带来、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风俗礼仪,由一代代客家人接力传承,在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中,慰藉萦绕不去的一腔乡愁。
泅渡时间的长河,客家人由外来者逐渐演变为南方土地局部的主人。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有太多渴望诉说的话语,有太多需要抚慰的情绪,有太多对故土和先辈的忆念,这些成为客家古文孕育生长的土壤。
清代道光年间,许多客家人在南方山野间扎下了根须,可关于原乡的念想并未消退,反而被时光酝酿得愈加浓稠。客家古文自民间悄然出现,渐呈蔚然之势。这种流传于民间乡土的吟唱形式,唱词多为七字韵文,含有许多中原汉语的古音,一个本子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曲折故事,情节不乏巧合、奇遇和让人难以置信的传奇,含有善恶报应的劝诫,对忠贞、义气、善良、正义的赞颂,表露对光耀门庭、多子多福的欣羡,也表达对恶意劣行的谴责。吟唱者多为盲人,这成为他们体面谋生的途径之一。
数百年间,一个个目盲人踽踽独行在赣南的山野小径,时走时停,走进集市、店铺、人家,逢到有人请唱时,就摆开家什,亮开嗓门。句句唱来,时而庄重,时而诙谐,时而激越,时而欢愉,时而悲切。在许多冬闲的时段,这吟唱如流动的江河,填充了因无聊而显得格外空洞的时光。在许多灯火暗淡的夜晚,点亮了一双双眼睛里的星光,直抵一个个朴实而沉默的生命最脆弱处……而目盲人的生命,也被这一次次吟唱点亮、拓展、升华。
时光深处,一群群客家人围在一起,目光的中心是那个操着乐器、婉转吟唱的目盲人。那一刻,客家古文不只是一个个唱本、一段段好听的故事,还是客家人之间的促膝交心,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一起用耳朵倾听、用心灵感受、用精神共振,来眺望和怀念他们共同的先祖和回不去的故土。
(节选自2025年第4期《芙蓉》王芸的散文《十三个半的乡愁》)

王芸,中国作协会员。生于湖北,现为江西省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三百多万字小说、散文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中国作家》《新华文摘》《长城》《江南》《上海文学》《天涯》《长江文艺》《散文》《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有作品被收入五十余种选本。出版有长篇小说《对花》《江风烈》,小说集《请叫她天鹅》《薇薇安曾来过》《与孔雀说话》《羽毛》,散文集《此生》《穿越历史的楚风》《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经历着异常美丽》,儿童文学《会飞的板凳龙》等。
来源:《芙蓉》
作者:王芸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