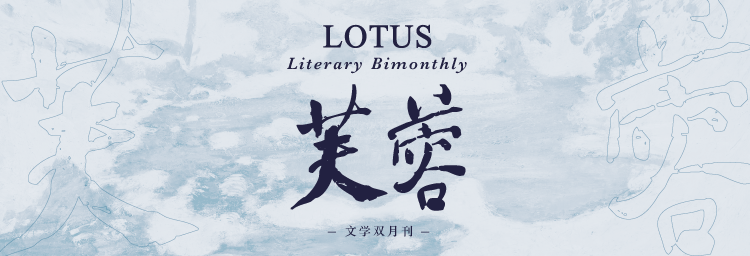

绿挎包(短篇小说)
文/裘山山
婆婆走后第七天,晚上,公公突然发来一条信息:小王,你明天有空吗?我想和你说个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追了一条:不要告诉家明。我感到困惑,可以说是很困惑。今天白天我们才见过,一起为婆婆举行头七仪式,他都没正眼看我。我顿了顿回复说,是要我去您那里吗?他回复说,在外面见吧,你找个可以坐坐的地方,把位置发给我,我打车过来。
如果不是明确显示着发信人是“家明老爸”,并且头像是个绿挎包,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他老人家发的。连家明都不会发这样的信息。我回了个“好的”。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公公婆婆,也就是家明的父母,分别是83岁和84岁。母亲年长一岁,一周前突发心梗离世。而我和家明也都年过半百了。我半百加三,家明半百加五。还需要介绍一下,我嫁给家明快三十年了,平日里很少叫他们爸爸妈妈,时常随着孩子叫爷爷奶奶(背地里经常叫老张老刘)。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叫我小王,没改过口。由此可见,我们并不是那种相亲相爱一家人。
所以,我回了一个“好的”。回了之后,心里还是觉得奇奇怪怪的。这老张要干吗?他能和我说什么事儿?还不让告诉家明?
收到老张的信息是晚上10点多。幸好我和家明各睡各的,我不用担心自己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被他察觉。我洗漱完毕,跟他打了个招呼就回自己房间了。自从女儿搬出去后,我就占了女儿的房间,一个人睡舒服多了,自在、安静。一般来说,我玩上个把小时手机就困了,倒头就睡。
但是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因为公公的这条莫名其妙的信息,也因为婆婆一周前离世,往事纷至沓来,在我脑海里翻腾。不知别人是怎样的,反正我一失眠情绪就糟糕透顶,脑海里翻腾出来的全是生气的事,气得要死还无处发泄。你总不能半夜给谁打个电话倾诉吧?你也不能半夜起来逛街购物胡吃海喝吧?
自打结婚,我公公婆婆,这对一直叫我“小王”的夫妻就看我不顺眼。一个人对自己是否被喜欢是很敏感的,从进这个家的门起我就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尤其是婆婆,好像她儿子娶了我吃了多么大的亏,不明确表达出来就无法挽回损失。我结婚,她连双新袜子都没给我,我知道他们不富裕,可是亲切的笑容又不花钱,她也舍不得给我,只给我脸色。当然,她没有破口大骂,她是损,时常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家明从小成绩好,考第一是家常便饭,这人生大考怎么就考砸了?人家说丑女多作怪,还真是有点儿道理呢。再或者:我们张家(其实她也不姓张)真是衰败了,媳妇一代不如一代啊等等。我万分委屈。本人虽算不上明眸皓齿,杨柳细腰,但是要打分的话也在良好以上,怎么就成丑女多作怪了?何况我还大学毕业,我收入也不比家明低。我在家明面前哭,家明安慰我说,这说明她把你当家人了,这个家有谁没挨过她的骂?我俩姐、俩姐夫,都挨骂好几年了。
婚后两年我们没要孩子,是家明的意思,想先积攒点儿家底再说。好家伙,这回她直接开骂了,吓得我不敢回老家。她还是不放过,写信来骂。她可不是没文化的人,会写,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比如连个娃都生不出,空有一副臭皮囊。再比如,想当绝代佳人,怕是不够资格哦。群众语言加书面语言,鞭辟入里。我俩招架不住了,赶紧生吧。偏偏生了个女儿,又没讨到欢心。她从老家赶来,在产房门口听说是女儿,丢下背来的一袋红枣小米转身就走。真是很决绝。
我被伤透了心。结婚前十年,只要一想到要回老家去看他们,我就紧张不安。回老家成了我和家明之间的一个哏。比如家明求我时会说,你帮我把这个文件整理出来,今年咱们就不回家过年。我会说,你要能把你女儿数学成绩搞上去,我今年就跟你回老家过年。
有一次过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去了。还没过完年三十她就开始骂。由头是家明没穿新衣服,说我对家明不好,然后说我是母老虎,虐待家明,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了。这次是家明“造反”了,拉着我抱着孩子就走。我们跑到县城汽车站已经没车了,想住旅店,那个小地方就一家旅店,还住满了。只得在候车室过了年三十,第二天一早买票回城。唉,若不是家明待我不错,我哪能忍到今天。
对了,每次婆婆骂我时,我公公,就是约我谈事的这位,就在旁边一言不发,板着脸,丝毫没有劝阻的意思,偶尔会帮个腔、拉个偏架。家明私下里总和我说,其实我妈脾气暴躁就怪我爸,我爸一辈子不爱她。可是婆婆再暴躁也从来不骂他,对他和蔼可亲。就骂我们几个,尤其是我。我在她面前低到尘埃里都没用,她都会拍出来给我一顿骂。
不行我难受死了,不能再这么想下去了。我拉开灯爬起来吃了半颗安定,决定把自己放倒。且看明天。
(节选自2024年第6期《芙蓉》裘山山的短篇小说《绿挎包》)

裘山山,女,1958年生,祖籍浙江,现居成都。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儿童文学《雪山上的达娃》,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五百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来源:《芙蓉》
作者:裘山山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