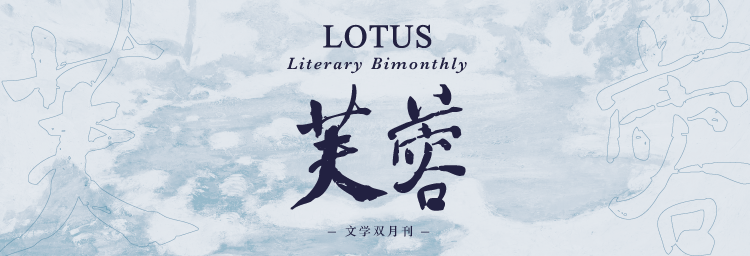

骨肉(长篇小说)
文/马金莲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堵土墙的左右两边,两家院里的女主人,开始说上话了。
这天马一山从大门进来,看见他女人身子靠在西边的墙上,扯着脖子,头望着那边,正忙着说话呢,身后脚下一个塑料盘子里晒着一些辣椒面,被几只鸡打翻了,鸡可能品尝过,被辣着了,报仇一样拿爪子踩踏那红艳艳的粉末,女主人聊得过于投入,根本就没有察觉。
他们搬进这个院子十几年了,当初马一山亲自拿着杵子打起来的墙,眼下显出破败陈旧的景象,墙头上零星长着蒿子、冰草,最下面分布着一层青苔。青苔隐隐,女人趴着的豁口处露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半个头,头上搭着一块红艳艳的包巾。马一山没有走近去打扰,站在房台子上望了望,轻手轻脚进了屋。
晚饭时分女人才结束隔墙长谈,看得出她心情很好,顺带着原谅了鸡闯的祸,那些辣椒面也不要了,抱着空盘子走进厨房。“二愣媳妇,硬缠着跟我说话哩。”她向丈夫解释,“我就没想着招惹她,可她热情得很么,嘴也甜,把我喊姐——”
马一山注意到女人的眼神里有一抹柔润的光在闪烁,好像不仅仅是和邻居女人说了话,被喊了姐,更重要的是她还另外获得了什么乐趣。
女人见马一山许久都不吭声,以为他不高兴,神情就有一点紧张,狠狠地揉着一疙瘩面,说:“那二愣看着不是个东西,但是他媳妇儿人还行,我想着这邻里邻居地住着,以后日子还长着哩,总不能连嘴都不招吧?”
马一山忍着笑反问她:“既然人家都主动搭话了,为啥我们要绷着不理哩?隔墙邻居,隔墙邻居,要没了那一堵墙,就跟在一个院里过日子一样的,有啥仇非得乌鸡眼一样瞪着?那女人不错,看着比一般的女人大气——二愣也就是个二哄哄,直肠子,要说跟那些小人比,人还算不错的。”
一席话把女人听愣了,傻了傻,忍不住咧嘴笑了,甩着面手在马一山胸口捣了一拳:“老东西,一天到黑看着啥事不管,其实满肠子都是鬼点子,把谁的心思都能揣摩个差不多!叫你个狗头军师还真不冤枉。”
马一山胸口顿时染上一坨白,他连连后退,喊:“死婆娘,我衣裳糊了!三天没打,要上房揭瓦吗!”
别看两口子骂得起劲,却丝毫不见生气的迹象,都笑呵呵的。
这一顿说笑,女人也就知道了男人的态度,他不反对她跟隔壁二愣媳妇来往,她这就放心了,其实她也不是无目的地跟别人家女人搅和,她是觉得那二愣女人确实挺热情的,看着为人还不错,再说自从上次二愣挖窖,大水漫灌了这边的牛圈窑以后,两家人算是臭了,把梁子结下了,二愣见了马一山老远绕着走,马一山也不会主动凑上去问好。两家人隔一堵墙住着,抬头不见低头就得见,总这么臭下去也不是个事,她有一个打算,如果有可能,先从她和隔壁女人这里好起来吧,多厚的冰层,只要开始融化,慢慢地,总会有看到希望的一天,往后说不定两家的关系也能缓和呢。
2
等祖祖拉着一个大箱子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她妈和二愣媳妇已经成了连手,两个人的关系好到一天不隔着墙拉呱几句话儿,就想得不行。尤其那二愣媳妇,殷勤得很,个子又高,嗓音又好,嘴巴也甜,没事就扯着脖子把半个脑袋露在墙头上,喊姐:“姐啊,忙啥着哩?”要么问:“姐,今儿晚饭准备咋吃?”再或者说:“姐呀,哪天我们去跟个集吧,我听说葫芦镇上有人卖做凉皮的锅锅呢,咱姊妹两个合事买一套,回来蒸凉皮吃。”
祖祖一到家就问父母舍娃联系上了吗,近况如何。
马一山两口子看女儿这么焦急,这才不由得跟着着急起来,女人说:“已经打过电话了呀,没人接,可能是忙,你也晓得,他上班不能接电话,要扣工资。”
祖祖一听急了,涨红了脸追问:“妈你究竟打了没有呀?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打!”
马一山也瞪大眼看女人:“是不是你没打?你和三三媳妇不和睦,又没去葫芦镇,你倒是在哪哒打的这个电话?”
女人也才慌了,两手揉搓膝盖:“我去牛三炮家打了,牛三炮女人帮着按的号码,按了好几回咋都没人应答,她说可能是舍娃上班哩不能接电话,我就想着真是上班哩。你们都瞪我做啥?我又不会打电话,我是个睁眼瞎子嘛——”她又羞又急,拖出一丝哭腔,“我不是有意瞒你们的——再说你个老东西咋不亲自去打哩?你一天天,就晓得瞎忙活!把啥事都推到我头上!”
祖祖一看这情景就知道母亲没打这个电话,她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再和父母纠缠没意义,赶紧掏出手机,按那串号码——自从买手机以来,这几天她每天都要拨打好几回,盼望着舍娃忽然就接了电话,她还给这个号码发了几回短信,告诉舍娃她有手机了,如果看到短信请给姐回话。
还是停机。
她放到免提上,停机提示父母都听到了。
“他还给你们留别的号码了吗?”
马一山摇头:“没有呀,就这一个。”
马一山女人已经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在第一页上,那串号码正是舍娃的。
祖祖看到了父亲的笔体,“儿子”,他是这样标注的。本子上确实只写了这么一串号码。
“就算换号,也该跟我们说一声呀——至少得跟你们说一下不是么?”祖祖喃喃自语,满脑子寻思着各种可能性。
她不甘心,往三妈家跑去,见了三三两口子匆匆点个头笑笑,顾不上多说,先要求打个电话。电话拨出去,还是停机。祖祖死心了。感觉一颗心在忽悠悠往低处落,不知道要掉落到多黑的深渊里去。她脸上还是强装出笑颜,给三巴三妈打招呼。三三媳妇缠住她不放,问东问西问了一大堆,无非就是大学念光了呀,念光了该工作了吧,准备在哪哒上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对象瞅下了么,家在川里还是山里,啥时节领回来给我们见见呀。
一连串问题,没有一个好回答的,祖祖只能用傻笑招架,一张脸禁不住红透了。
三三可能感觉出了侄女的窘迫,赶紧拦他女人:“哪有你这么问话的,小心把娃问羞了。”
他媳妇哪会在意这个,一巴掌拍在祖祖肩膀头上,嘁嘁嘁笑:“哎哟哟,还是大学生哩,有啥可害羞的!脸皮这么薄!看这样子你还真没有瞅下对象么——三妈跟你说,遇上好男人要赶紧抓住,错过再后悔也没用。对象还得自个儿瞅,不要学你三妈,糊里糊涂地,就叫父母塞了黑牛的沟子!”
身后三三拿鼻子哼了一声,说:“你我半辈子都过下来了,你咋啥时节都不忘嫌弃我哩?”
祖祖一看这两口子要借机又闹腾起来,赶紧向他们告辞,退出门,一溜烟地往家跑去。
细想三妈这辈子还真是算不上幸福,就算三巴对她很好,啥事都由着她,从来不存在打骂虐待,可女人仅仅是不挨打不受气就是幸福的吗,祖祖知道不是,肯定有更深刻的幸福要追求。也许她很快就得面对,并且必须懂得这些东西。
从这天起这个家罩上了一层愁雾。
马一山是男人家,还能咬着牙照旧过日子,女人比不得男人肚量大,心里搁不住事,脸上早就挂出来了,靠住墙根出长气,和二愣媳妇扯磨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事情告诉了她。二愣媳妇也是吓一跳,不过很快就稳定下来,说她娘家庄里有个娃娃也是这样,跑出去挣钱,慢慢地失去了联系,家里人等得没有妄想的时候,忽然他就回来了,原来是跟上一伙淘金的人去青海沙窝里淘金去了,钱自然没挣上,好在一条命捡回来了。
马一山女人明白这隔墙闺蜜的好意,是在变着法儿地给她宽心呢,她也就拼命暗示自己往好处想,也想象自己的儿子舍娃是跟上淘金人进了戈壁沙漠。她把这话跟马一山一说,马一山脸色暗了,说:“真要跑去淘金子,那就坏了,娃的小命儿十分里有八分不保了。你晓得那淘金的都是些啥人吗,是杀人放火不要命的亡命徒啊,把头别在裤腰带上才去干那种活儿——”他看过一本关于淘金的书,所以听女人一说淘金,就马上联想到书里的情节。看到女人的脸顿时一片死灰,他心里不忍,赶紧开解:“不会的,我觉得咱舍娃不会跑去淘金,他大半是暂时遇上了啥困难才没有跟我们联系,再等一些日子,肯定就会来电话了。”
女人已经把“淘金”两个字吃进了心里,马一山咋哄都无法转移注意力,灰着一张脸干啥都没心劲,不管靠住什么都要傻坐下去,愣愣地发呆,两个眼里灌满了忧愁。那忧愁是一层雾,有一股弥漫性力量,照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跟着变得沉重起来。祖祖简直不敢看这眼睛。她每天都给舍娃的那串号码打电话,打上无数次都是停机,盼望中的那个熟悉的声音迟迟都没有出现。她心里好像揣了块大石头一样压抑。
这个家里只有碎女好像完全不在意亲人们正被什么难题困扰,她该吃就吃,该睡的时候倒头便睡。这天夜里祖祖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想着舍娃可能遭遇的各种可能,她发现自己还是太单纯,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除了往返路上一个人坐火车,好像再没有什么惊险的经历,过的是单纯的校园生活,而舍娃呢,自从那年出门南下,谁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在和什么人打交道——姐,你等着,接下来我要加班攒钱给你买手机!舍娃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祖祖发现她是这样想念这个声音。如今想来,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亲的声音,天籁也不过如此啊。
眼眶里汪起两团热水,注满了,泡得眼窝酸涩胀痛。她轻轻侧头,顿时水流下滑,热烘烘两道,顺着脸往下淌。泪落无声。窗帘上有一个大月亮,好像粘贴上去的,在隔着窗帘望她呢,迟迟不肯移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刻的舍娃,会不会也在异乡的土地上仰望月亮呢?
此事古难全啊。此刻回味苏轼词,真是说不出地胆战心惊,祖祖默默在心里说胡大慈悯呀,希望舍娃他还好,平平安安的,啥麻烦都没遇上,快点和我们联系。
碎女可能是脖子窝住了,发出很响的鼾声。这女子本来就有打鼾的毛病,只是今夜的鼾声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挣扎,在深夜里逃命,高一脚,低一脚,深一下,浅一下,好像她随时都要断气。祖祖听着难受,摸黑搡一把,把她脑袋掉转个方向。鼾声停了。不等祖祖睡稳,又开始了。像一个疯女人在拉风匣,“哗啦——呼噜——”风匣杆子简直能扯断。祖祖再伸手搡一把。碎女在梦里哼一声,扭过头去继续酣睡。鼾声很快又响了起来。
没治了。祖祖苦笑。睡不着,干脆开了灯,准备趴着看书,坐起来看到了一个暄腾腾白生生的胸脯。是碎女睡热了,梦里自己把自己扒拉开,露出了上半个身子。祖祖不敢看,替她拉被子掩盖。手捏着被角,又迟疑了,她目光里好像有手,伸出来不愿意往回收,硬是被眼前的景致黏住了。
那就只看一眼——她跟自己谈判。只能一眼。得到了许可,目光就变得大胆了。先做贼一样试着往下落,忍着心里的惊诧,慢慢地,从一个点铺开,变成了一个面,覆盖住所有裸露的部分。碎女怕热,睡觉脱光了外头的衣裳,只留一个宽薄的小背心挂在肩头,等被子蹬开,小背心滑落,她上半身就全露在外头。她发育得很好,身上皮肤比露在外头的面部肤色白嫩得多,饱满,细白,散发出少女特有的气息。
屋顶的灯泡挂在半空时间长了,落了灰尘,脏兮兮的,发出的光昏沉沉的,落在碎女裸露的身体上,却变得分外柔和,好像灯光也知道怜惜这娇柔饱满的躯体,所以极力收敛着自己,要映照出一种油画般的静美来。
死丫头,一天到黑咋咋呼呼的,总是一副假小子的模样,没注意她已经长到了这么大,发育得这样齐全——祖祖的目光里有了溺爱,感觉无法把眼前这副身躯和记忆里那个拖着小辫流着长鼻涕串儿的小女孩联系起来。
眼前完全是一个散发着成熟气息的少女,就连胳膊都圆鼓鼓的,细白的皮肤下包裹着汁水充盈的肌肉和骨骼。一对乳房发育得尤其好,高高翘着,圆圆的小馒头上还被筷子点了小红点儿,那是两颗豌豆粒大的乳头。乳房像一对逃出家门,不受父母管束的淘气孩子,好奇地打量着衣服外面的世界。祖祖咽了一口唾沫。她自己就没有这样好的胸,她青春期正发育的那几年在县城念书,总是吃不好,严重缺乏了营养,倒是虚胖过一阵,到大学里又瘦下去了,胸前至今没什么料。眼前这对好胸能给自己匀一点多好。她忽然感觉自己有些下流,赶紧一把将被子拉上去,严严盖住了妹妹的身躯。熄了灯,合上眼,直挺挺躺着,心里汹涌的一股热浪才被压平息了。
这个点隔壁屋里马一山女人已经在一个梦里兜转。迷迷糊糊来到一个被大水环绕的地方,好像坐在一种叫作船的东西上,摇摇晃晃中不觉意又上了岸,等她回头看,船没了,水也没了,眼前只剩下一片沙。她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葫芦镇,哪里见过这么大片的沙呢,茫茫的都是沙子山,她找不到路了,一脚一个沙坑,走得很艰难。走了很久还是找不到一个人影子,远处隐隐地传来动物的嚎叫,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那就是狼群,已经饿了几天几夜了,就等着能有一个人出现好让它们填一下肚子。话还没说完,嚎叫声裹着大风,四面八方向她扑压下来。她吓得魂都没了,明明在张大嘴喊救命,可好像嗓子哑了,一声都喊不出去。腿也软得半步都拔不动。她软软地倒成一堆儿,心里说胡大呀,这辈子造了啥孽,连个囫囵的死身子都不能落下——
“我的娘呀——”她哭着喊。眼前头一黑,接着亮了,一个大手推搡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问:“咋了,咋了?魇住了吗?”
她醒了。睁开眼,看到头顶上灯泡亮着,身边马一山笑着调侃:“多大的人了,还跟碎娃娃一样,能叫睡梦给魇住?”
女人慢慢绷大眼睛,彻底看清楚眼前还是熟悉的现实,那些困扰她的危险都只是梦境,这才把绷紧的身子和神经一起放松下来,两手把脸一捂,呜呜哭了起来。
“舍娃,我的儿,我的儿怕是回不来了——把小命送到外头了!”
马一山的心猛一抽,吓得不轻,赶紧骂女人:“胡说啥哩你满嘴胡说?好好的,哪来的这些胡话?现如今跑出去打工的娃娃那么多,谁家的娃娃不是风里雨里地蹦跶着,一个个活蹦乱跳地活着,偏偏你儿子就要出事?我跟你说啊,舍娃那条瘦命儿,不值钱,也没人要,会好好回来的!”
女人被男人镇住了,眨巴着迷离睡眼想了想,梦里的情景历历在目,便又接着往下哭。“那肯定是淘金子的地方,除了黄沙就是黄沙,还有狼!成群的野狼,眼睛都饿红了,嘴张得跟簸箕一样大,就等着吃人哩!我的舍娃呀,一个娃娃芽芽儿,还连媳妇都没领哩——妈的心里疼呀——我的娃太可怜了——”
马一山看女人实在哭得伤心,就猜想她做的梦不好,而且和儿子舍娃有关,知道是母子连心,她日夜思念舍娃,梦里自然就梦到了。其实他这心里何尝没有时刻牵挂呢,就叹了一口气,把女人拉进怀里,像哄娃娃一样拍着背:“你呀,就是心太窄了,做个睡梦也当真了!我跟你说,睡梦都是反着的。你是不是梦见舍娃遭罪着哩?反过来讲的话,舍娃好好的,说不定在哪里挣大钱着哩!你想想啊,前几年咱们家才叫艰难哩,祖祖念大学,一年好几千块,钱财那个紧困呀,逼得我简直要尿裤子,不也还是熬过来了?!我觉着以后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你就不要愁,舍娃肯定好着哩!咱就想办法赶紧攒钱吧,万一哪天他猛然回来了,咱要预备着给他领媳妇哩!”
马一山真要是温和起来,其实挺暖人的,女人本来瑟瑟颤抖的身子,埋进他宽大温厚的怀抱后,又被这刻意的温存所抚慰,心头渐渐平复下来,她紧紧贴着男人,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眼里伤心的泪水还没干,却已经破涕为笑了,手心摩挲着男人胸口的肌肉:“你说舍娃他瞅下媳妇了吗?长啥样子?要是长得不惹人疼咋办?”
马一山哭笑不得,这就是女人,哭也是她,笑也是她,阴晴之间转换起来连过渡都不用。他只能继续挖掘哄孩子的潜能:“那一定心疼得很,咱舍娃本身就长得好么,好马配好鞍,他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
(节选自2024年第2期《芙蓉》长篇小说《骨肉》)

马金莲,女,回族,宁夏西吉人,80后,民盟盟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坚持文学创作24年,发表作品6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长河》《1987的浆水和酸菜》《我的母亲喜进花》等15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等4部。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茅盾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马金莲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