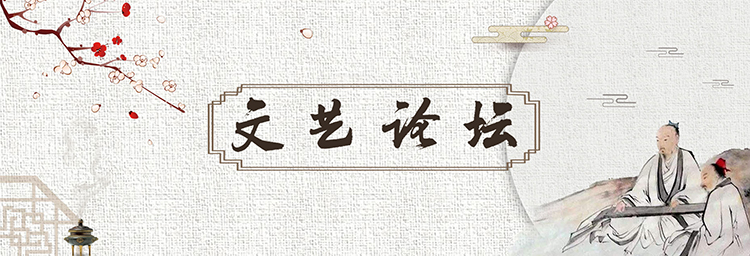

创意写作学的基本理念透视:问题与可能
文/刘卫东
摘 要:2009年以来国内创意写作研究领域提出了包括自我发掘、文类成规、创意转换等多个观点,但对其中蕴含的理念、学科史语境、涉及的写作学传统与当代写作学论题,以及拓展方向缺少系统阐发,这反过来影响了创意写作学的概念界定、学理勘察及学科构建。自我发掘、文类成规与创意转换分别涉及创意写作主体的自我表达、文本层面的规律以及社会、产业层面的跨界转化,是作者、文本、社会三位一体的创造性转换生成实践劳动,是主体创造力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也是其抽象的灵感、文化资源不断向具体产品转化的过程。新时代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话语建构,需要在这些基本理念基础上寻求新的拓展,兼容并汲取传统和现当代写作学资源,适应创意写作中国化的现实。
关键词:创意写作;自我发掘;文类成规;文化产业;创意转换
中国创意写作学研究迄今已有十多年历史,在概念勘察与基本学理拓进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2009年创意写作作为学科被正式引介到中国,2011年国内就提出了加强自我发掘、文类成规等基础研究的观点,[1]较早系统介绍创意写作的原创理论专著也强调了这两点在创意写作学研究中的地位。葛红兵明确指出“创意写作的两大基础理论为‘自我发掘论’和‘文类成规论’,分别是从创意写作者和创意阅读者的视角出发的,‘自我发掘’立足于创作主体,强调从内部激发创作者的创意潜能,运用心理学和心灵学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潜能的激发”[2]。不过,虽然创意写作理论的本土化向度与问题提出已久,但目前尚未明确从话语、理论层面进行整合,对自我发掘、文类成规和创意写作的逻辑关系、概念结构缺少阐释,这影响了中国创意写作学理论的进一步构建。“没有系统的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创意写作的根本规律,也不能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创意写作技能教学和培养训练,甚至不能说服高校开设类似课程,也不能说服学生来学创意写作、接受创意写作技能培训。”[3]近十余年来,学界对自我发掘、文类成规和创意转换分别从创意写作的内在层面、文本规律、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对个体内在文学经验、生活经验、审美意识,文本层面的文类知识、创作规律、创作方法,以及社会层面的跨文类、跨媒介、跨产业转化分别进行了勘察。立足于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现象和问题,整合这些理念是促进创意写作学学理建设的必要工作。
一、自我发掘:创意写作的初阶起点
自我发掘是指作者以写作实践为方式,不断发现和重塑自身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和创作经验,将之作为认识自我的基本途径,参照格雷姆·哈珀的研究,可以译为self-exposition或self-explore。[4]自我发掘理念在创意写作学科史上对应的核心概念是休斯·默恩斯等人于20世纪早期提倡的“自我表达”。1920年代美国教育家默恩斯在林肯学校开设面向中学生的创意写作课,强调通过多种方法引导自我表达,以激发内在情感、想象力。自我发掘本身并不神秘,它最重要的目的和方法,都是侧重引导作者进入内在经验,调动生活经验、情感、想象力等,与以背诵、语法修辞为中心的写作教学形成了鲜明对照。[5]19世纪末期哈佛大学温德尔的英语写作课所主张的创造性想象,鼓励学生表达自我经验就是如此,同样充分肯定写作者的情感、想象能力,鼓励借助写作实践进行自由、创造性的自我表达。
中国创意写作学研究将自我发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之一,可以追溯到2009年与2011年发表的《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两篇论文。葛红兵、许道军在《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一文中提出了“开拓创意习得和读者接受两个新视野,并加强‘自我发掘’‘文类成规’等基础理论研究,确立新型学科理论体系”。[6]葛红兵还进一步在《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一文中明确了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指向,认为学科的核心不在于语法修辞方面,而在于个体创意能力的提升和实现。[7]这两篇文章正式将自我发掘、文类成规作为创意写作学的两种理论基础。另外张永禄也较早指出在创意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个初步的理论建构分别是“潜能研究”“艺术成规”。[8]国内学者所提出的“自我发掘”包含了巴雷特·温德尔、休斯·默恩斯所倡导的创造性自我表达,自我表达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自我发掘内在的一个层面。
自我表达被纳入自我发掘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但作为创意写作学科史上的重要概念,并非简单地鼓励学生宣泄自己的主观情绪、想象,而是突出个体经验,激发作者的创造性想象,是走出修辞、语篇写作法,去除创作活动、作家天才论,将创作神秘化的第一步,将书写和表达权利下放给普通的学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基于自我表达构建起来的创意写作教学实践强调,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化,作品不再是某种天才的、少数人创造的,而是自我不断表达、建构的创造过程,它具有可被认识的内在的“经验模式”。作家的独特之处不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天赋,而是隐含在作品之中,这恰是现象学文论和英美新批评与创意写作理念吻合之处。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早期推崇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写作课程大量涌现,实际上代表了走出浪漫主义对天才崇拜的迷思,以及19世纪语文学主导的写作教育模式的新突破。自我表达的提出是现代创作论观念的重新奠基,其次才是对个体不同情绪、形象、经验的方法论层面的肯定。对自我情感和想象的表达是人类普遍的行为,但只有当它随着现代个体主体性的确立而被作为创作的基本理念替代工具论、教化论、神学论等写作观念,发展出一套明确、系统的方法时,创意写作学才得以确立。作品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关涉的创造性因素虽然仍旧不容易驾驭,它是可以解释的,这是走出对创作活动的神秘化、天才论迷思的重要一步。就此而言,潜能激发与“作家障碍”问题的提出正是这一逻辑的持续展开。
在吸收自我表达这一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国内创意写作学研究整合本土资源,进一步提出了“潜能激发”,目的是构建创意写作的创作论,将创作实践推至面向普通人的创意能力和创新能力教育的层面。“潜能激发”是指运用各种去修辞化的、跨学科的方法等多种创意实践不断激发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感受力、情感力量,使之获得一种“审美能力”,[9]以语言为媒介进入原创活动,这是创意写作学自我发掘理论构建的第一步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写作是写作本身,不再是为其他课程服务的学术活动; 要求审美能力(‘感知能力’) 和文学评价(‘判断力’) 的自我提升 ”[10];以感知、审美和独立的判断力等要点的潜能激发为具体入手点,自我发掘注重的是自我经验、创造潜能的多方面激发,以此不断构建一种去修辞化、语篇教学、形式化的写作激发理念,它是“基于个体的感性的身体本位的创意实践论写作学研究”。[11]
创意写作学的自我发掘提出与运用具有双重背景:第一是创意学、西方心理学的视域。第二是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语境。在创意学方面,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规律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葛红兵、雷勇等吸收禅宗思想资源提出了潜能激发研究,并借鉴赖声川的创意学研究成果,探索克服“作家障碍”,激发创造潜能的方法。而在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史的发展方面,自我发掘的提出则主要是顺应创意写作提倡的去修辞化。中国创意写作学在构建自我发掘理论的过程中,不仅从西方创意写作学科史汲取了“自我表达”作为其分支,还结合本土文化资源提出了“潜能激发”,整合已经初步完成。这使得自我发掘具有弹性空间和可塑性,它从内在层面解决创意写作主体,与创意写作兴起早期经验理念的梳理和整合式建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自我发掘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内生的概念,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人员在融汇中西创意写作学,立足于创意写作实践中对个体内在经验、自我表达重视的基本经验提出的。自我发掘未来可以借助通识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艺术疗愈实践研究的资源,导向一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形成内部的理论拓展。
二、文类成规:文本生成的内在规律
2009年国内就已经形成了小说类型学的概念,并对基础学理进行了初步勘察,对类型学理论、小说类型演进、类型学视野下的现代小说研究等都有一定的梳理。文类成规的提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类成规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模型和方法多方面进行了勘察,对创作和相关教学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目前学界对文类成规的接纳和多种类型的成规研究,已经有相对深入的梳理。在基本理念层面,也形成了立足成规走向文学创造的共识。张永禄、陈鸣、叶炜在训练方法层的研究,都是类型小说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为创意写作的教学打下了重要基础,为相关类型的作家工坊实践提供了学理基础。例如,历史小说、官场小说、动物小说、科幻小说、校园小说等类型学层面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小说的叙事规律,对相关的工坊创作训练具有指导意义。
文类成规是文学创作中具有某些类型规律,文类、文本的生产、创作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事文类成规研究的学者观点颇多,但有基本的共同点。“具体来说,他们的基本观点有:艺术来自成规、成规的‘生成’与‘凝定’有规可循、艺术成规是生成性的等等。”[12]文类成规建立在对小说叙事学、类型学等研究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文类成规因此成为创意写作课程设计的重要依据之一,能够从创作方法、叙事语法等层面为写作者提供可操作的训练。如果说创意写作学研究在提出自我发掘主要强调突破语法、修辞、语篇等限制,那么文类成规则进一步探寻文本内部的规律,将写作视为一种融合自身经验,具有规律的手艺(craft),二者可谓相互补充。
2011年前后,国内的创意写作学研究人员一度将文类成规与自我发掘并列,将之视为核心的基础理论支撑,并在不同的论著中加以强调。[13]如果说自我发掘注重的是作者内在经验的激发和呈现,是对创作主体的研究,那么文类成规则是聚焦文本自身,探究的是文本的角色、序列、故事、类型等方面的深层语法和规律。文类成规在融合类型学、叙事学、文化人类学资源的基础上,对文本创作过程方法、叙事类型、创作规律等方面有深入的揭示,其研究对创意写作学提出的“写作可以教”“作家可以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创意写作设立的各类虚构、非虚构、诗歌工坊教学和各种类型化的学位方向互为支撑,这正是创意写作研究人员将之视为两大基本理论方向之一内在原因。
当前类型成规方面的研究以网络文学的叙事成规探究最为突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同样与其高度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现象密切相关。包括穿越、宫斗、修仙等不同网络文学的类型研究、叙事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欧阳友权、夏烈、张永禄、叶炜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欧阳友权强调在评价体系中应注重“题材类型出圈的拓新力”,[14]叶炜认为“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先熟悉‘文类成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造,是切实可行的训练路径。就目前的中国写作教育而言,作为类型化写作的网络小说,是创意写作教学的最可行路径”。[15]张永禄还提出“运用小说类型学方法对其中相对成熟的网络武侠小说子类型及代表作品进行定性研究”。[16]这些研究从叙事规律、类型结构、创作过程和训练方法多方面着眼,表明文类成规在网络文学的研究、原创和工坊教学设计等层面已经有了初步运用和融合。
文类成规的研究是创意写作学的基础理论突破口之一,也是创意写作学不断吸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学科成果的交汇点、切入点,它表明创意写作学的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在话语层面存在交叉,与文学生产、文化产业具有密切联系,文学研究、文学原创与文化生产之间彼此交互共生,共同构成完整的文学生态。目前基于类型成规的研究已经在工坊教学等方面提出了基于模仿、作家障碍克服、潜能激发等解决方式,王宏图、谭旭东、许道军、张永禄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探索。王宏图对模仿为基础的创意写作课程的提倡,主要是从现象学的视域出发将文本视为复杂的多层结构,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创造性模仿。[17]谭旭东和葛红兵也同样强调类型模仿的重要性,前者将文类成规意识融入不同层级的写作教学设计的基础理念,后者将类型成规视为创意写作工坊教学法的核心之一。
不过,目前文类成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薄弱点。第一,文类成规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与创意写作学研究融合,与创意阅读、创意批评等共同发展。文类成规是进一步进行创意阅读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支撑,但该方面的探索较少。第二,文类成规研究对经典作品、网络文学等作品的研究较多,但与当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创作笔谈、对话等仍待展开。文类成规除了需要分别研究网络文学、电影文学创作方法、叙事层面的规律,还需要接续自我发掘的理论观点,在具体的层面上说明自我发掘向特定文类转化的类型学方法,在操作上解决由语言、形式、文本、观念等模仿到创造性模仿的学理。第三,除了文学类型等方面的分类研究,内涵与文学的心理层面、作品精神层面的成规等解释和研究尚匮乏,形式层面的研究多,异质性的、复杂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第四,小说作品之外其他的广告写作等文本的成规研究尚需进一步总结和归纳。第五,文类成规的研究需要与语言学层面、认知层面的微观研究结合,以更好地进行学理阐释。
三、创意转换:文学创意的跨界转码
“创意转换”是指以写作为内容生成方式将文学灵感、文学作品乃至广义上的文学资源转换为不同形态产品、文本的现象,一般具有跨媒介、跨产业门类的特点,是文学创意的形态衍变、价值增值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在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教学研究视域中,创意转换主要具有三种不同的意涵:第一是指主体经验的整理和内部转化,自我表达是它最基本的形式。第二是抽象的创意向具体的作品、产品转换,文类成规是它通用的方法、策略,即格雷姆·哈珀强调的文本在不同媒介间的“可转化性”(transportable)。[18]第三是借用某一领域的知识内容将之运用到新的领域,赋予创意、作品新的物质性、形态和价值。除此之外,在更早的时期,它主要是指历史上某些文化资源、重要概念的变迁与转化。
随着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文本的创意转换也越来越频繁,跨媒介、跨产业转换成为常态。在创意写作学研究的视域中,主要有葛红兵强调的“跨媒介转换和流转”,聚焦创意写作作品的转换规律、基本方法、路径,以及金永兵提出的“创意写家”等观点。如果说自我发掘主要是激发创作主体的内在经验、唤醒其审美感受,文类成规主要是在方法、规律等层面引导作者,那么创意转化则是更高层面的作品价值拓展,它不仅仅关注主体内在创意向文本的具体转换,还研究创意—文本—产品、资源—服务—社会的多维度、全方位转换。这意味着创意写作实践不限于文学写作范围,不仅是个人创意向小说、诗歌、散文等纯文学文本转化,而是进一步向广告、影视、动漫、策展、文旅等文创领域文化产品转化。即许道军所指出的,创意写作首先是面向文化创意产业,在培养文学作家之时,为文化创意产业培养和输送人才。[19]
创意写作视域中文学的创意转换是多维度的,它涉及文学的跨媒介、文本的跨产业、作品的跨类型转化。其中,文学的产业化、数字化是文学创意增值、内容文本变现的驱动力量,其本质是借助新媒介实现从文学想象到文创产品、文化服务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学价值不断变现和拓展的过程。
首先,文学创意的转化是一种跨文类的价值传递与更新。创意写作跨文类的转化是指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广播、展览、品牌等相关文本之间的交互转化,这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也是创意写作创意转化的第一层。这类转化的范围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链不断延伸的,在不同的创意作品类型中转化。如王海峰认为“创意写作在文化产业中的衍伸,朝向媒介融合、媒介素养、泛媒化三方面发展。文化产业中的创意写作文本形态衍变,主要表现在文体、语言、形式、交互四个层面”。[20]这其实正是创意写作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创造性写作实践的特点所在,它跳出了从修辞、语篇、主题等层面定义写作实践的角度,主体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谭旭东还指出这类基于创意写作的新媒体人才培养的特点,认为“作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意写作并不仅仅局限于通识教育和作家培养,而是逐渐地面向更为广阔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面向国家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21]。这些观点主要从社会文化生产机制层面看待写作实践的基础性意义,将之作为文化原创生产活动,并研究此类活动的基本方法、规律。
其次,文学创意的转化是一种跨媒介的多模态转化。创意写作的跨媒介转化是指由单一的文字的语言文本借助声音媒介、视觉媒介、身体媒介等不断转化为影视作品、音频作品、舞台艺术作品等。这类转化的特点在于语言文本随着不同媒介载体变化,是创意转换的第二层。媒介技术决定了创意写作原始文本转化的广度,并影响其具体的产品形态。这些特点使得当前的创意写作实践与20世纪80年代以纸媒为核心的文学原创相比,其传播和变现路径更加灵活多样。媒介是创意写作跨文类转化的技术维度,跨文类转化又使得媒介融合进一步加深,并不断产生新形态的文创内容、作品,其传播路径更为广泛。
再次,与跨文类、跨媒介多模态转化伴随的创意转换还包括了跨文类、跨媒介基础上形成的跨形态的转化。在创意写作的视域中,创意转换是一种跨形态的转换,是从抽象的想法向具体的文本转化,再由文字文本向视觉文本、表演文本的多种形态转化,即包括了从文本向各种不同形态的产品转化。在这一层面的转化中,文学实现了它向游戏、影视、广告、策展等各种不同行业的输出、协同与价值转化。梁慕灵将这类能够同新媒体领域工作人员协同工作,以创意写作从事创意产业内容生产的写作实践称为“写作艺术”。[22]这类写作艺术人才的工作目的就是实现文学的价值多方面流通和变现,并可以在跨产业链的链条中不断转换。跨形态的转化使得文学想象能够与具体的文创产品、文化服务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文学创意也成为个体文化价值观念、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表达的普遍方式,文学的精英底色不断被剥离,在此基础上突起的“创意作者”更能表征文学创意的现代内涵。
创意写作学视域的创意转换将是创意作者借助写作实践不断参与社会文化生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社会文化事业的一种基础能力。创意转换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转换,也是创意思维的训练、行业意识、文化原创意识训练的过程。其中,创意写作学视域中的创意转换还包括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维度。借助创意写作训练,培养具有文化原创意识、转换意识、产品意识的高级写作人才,以语言文本策划、可供生产性的创意文本为基础,不断将文化资源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等。例如,葛红兵提出“将送电影、送戏剧等提供文化成品的方式,改为营建社区创意写作工作坊、社区戏剧工作坊等,帮助社区居民创作发声,让社区组织起来,成为文化创意型社区、具有文化塑造和自我认同能力的社区”[23]。余文翰则提出立足于“文学地景”的书写,探究文学景观、文学观光和城市经验之间的转化问题。[24]总体来说,创意转换更进一步突出了创意写作学对创意第一位、作品第二位的理念特质,它表明单一的文学文本生成并不是创意写作的终点,也不是个体能力、文学价值实现的终点,它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广义上的文创产业的作品、产品,这无疑开拓了写作实践和文学性的内涵。正如雷勇所指出:“当下时代,创意写作能够承担起‘文学性’的迁移和弥散这一命题,以‘创意’为第一属性的创意写作,不以完整形制的文学作品为一元性追求,这更加适应数字时代多元性的表达需求。”[25]创意转换的过程是文学价值链、产业链不断延伸的过程,是文学价值、文学性不断丰富,也是逐步构成新的基于文学原创的文化创新链的过程。
自我发掘、文类成规和创意转换作为创意写作学研究近年来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具体的措辞与概念界定方面仍有模糊之处,但总体上它所代表的理念广受关注,从多个不同角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如果说自我发掘是在内在层面激发主体经验,文类成规是在文本、形式层面进行训练,那么创意转化则是基于新时代数字化、多模态、产业化的现实,不断实现文学创作的跨界转化和作品成果的全面流通。这一方面符合当前文化产业、文学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不断从学科史中获取话语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素养、媒介素养和创意素养得以转换和衔接,文学知识教育、文学创作教育和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教育得以紧密融通,创意写作作为创意实践的社会化、大众性、民主性乃至“人民性”特征也随之不断凸显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个基本理念内在也具有关联,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创意写作中国化过程中国内学者积极进行建构的结果,其内在指向即“创意本体论”“以人人能写作为圭臬”。[26]从学术发展角度看,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吸收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也突出了中国话语;从学科话语角度看,它们也是多学科话语不断交互、碰撞的产物,涉及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教育学等。而从理论建设角度看,它们都是中国学者主导的创意写作学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包括“创意写作与新文科人才培养”[27]“作为情感教育的创意写作”“作为创意写作新景观的人工智能写作”[28]等许多创意写作研究成果都可以在这些理念下进行阐释和对话。目前以自我发掘、文类成规和创意转化为基础构建中国创意写作学话语体系尚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只有兼容传统、现代写作学的资源,在此基础上熔铸民族性、世界性,衔接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才能更好地展开新时代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话语、理论体系的全面构建。
注释:
[1][6]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2]葛红兵、高尔雅、徐毅成:《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
[3][7]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Graeme Harper. Critical Approaches to Creative Writing,London: Routledge,2019.
[5]Hughes Mearns. Creative Youth, New Yorker: Doubleday, 1925.
[8][13]张永禄:《我国创意写作基础理论的初步探索》,《写作(上旬刊)》2014年第12期。
[9]刘旭光:《审美能力的构成》,《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10]张永禄:《创意写作在当代文学教育中的可能形式与实践途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1]葛红兵、王冰云:《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基于个体的感性的身体本位的创意实践论写作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3]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版,第11页。
[1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树状”结构》,《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
[15]叶炜、黄倩倩:《突破“作家障碍”的意义及其路径、方法研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6]张永禄、杨至元:《圈层设定下网络武侠小说的创作走势与问题——基于2019—2020年的平台数据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7]王宏图:《从摹仿到创造——创意写作教学训练的一种途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2年第1辑。
[18]Graeme Harper. Critical Approaches to Creative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2019, p. 30.
[19]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使命与愿景》,《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20]王海峰:《创意写作的文化产业衍伸》,《文艺评论》2021年第2期。
[21]谭旭东:《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与探索“新文科”之可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22]梁慕灵:《创意写作不只是写作 :香港都会大学创意艺术学系“写作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考察》,《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2年第2辑。
[23]葛红兵:《以创意城市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
[24]余文翰:《从文学地景到文学观光的香港经验》,《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第十辑)》2023年第1辑。
[25]雷勇:《数字化交互式新媒体平台与创意写作的新形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26]葛红兵、李枭银:《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意写作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27]金永兵:《新文科与创意写作人才培养》,《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1-2期。
[28]张永禄,刘卫东:《人工智能写作:创意写作的新景观》,《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本文系2022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创意写作视域下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JGY202206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刘卫东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