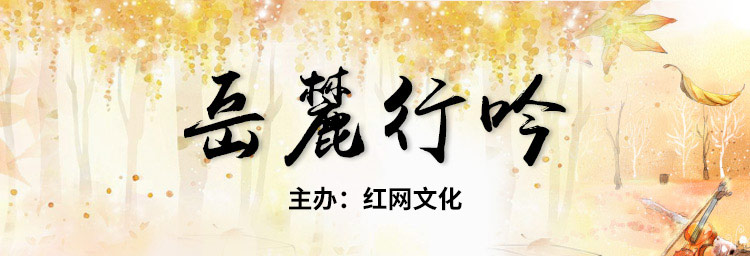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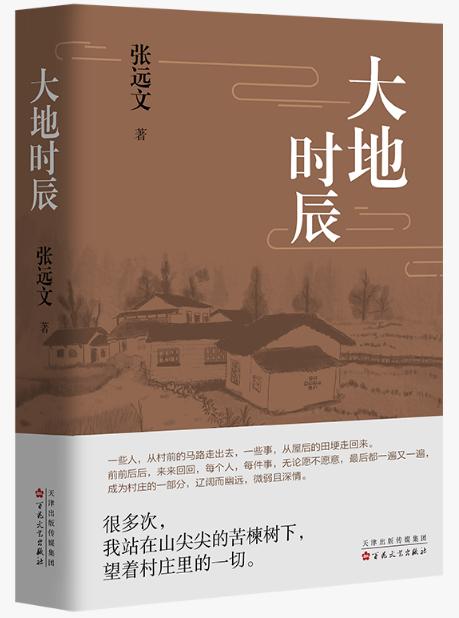
张远文散文集《大地时辰》图书封面。
低处的匍匐与时光的飞翔
——张远文散文集《大地时辰》阅读印象
文/陈源
1986年6月14日的那个下午,当18岁的张远文用黑板刷无意间在脸上留下白痕时,地球另一端的博尔赫斯正沉入永恒的黑暗。这个充满隐喻的巧合,仿佛预示着一个乡村教师与文学不可逆转的宿命相遇。
打开《大地时辰》,我细细地抚摸远文的每一粒文字,这些跳跃的文字,越过书桌的边缘,延展到苍黄的大地与时辰。我感觉触摸到了远文既微弱又强大的心跳。我仿佛看见一个贴近大地的生命,在挣扎、彷徨、矛盾、痛苦、孤独、无奈。光阴中,那些“哦嗬翻天”的疼痛,以及大地上的一些野花、一些流水、一些云朵、一些炊烟、一些鸟鸣、一些星辰,或高或低,都在窗口的月下,融入夜色,沉淀为光。
一
小满过后三天,远文出生。“这一天,就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风轻轻地吹,雨淅淅地下,雨点落到哪里,哪里就是人间的低处。”这个“人间的低处”,是生命最贴近大地的地方。贴近大地的生命,才能获得最饱满的呼吸。
节气到了小满,暑气初萌,雨水渐丰,小荷初绽,枇杷熟黄,荞麦飘香。元代元淮《小满》有“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的句子。远文写他出生时“紫盈盈的苦楝树花,密匝匝的,一丛丛,一簇簇,朵云一般,泛出湿漉漉的光彩与清香。”其实,此时的苦楝树花早已凋谢结籽,他何以推迟苦楝树的花期呢?远文的老屋坐落在319国道旁,苦楝树是一种很常见的行道树。远文笔下那些推迟花期的苦楝树,从来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个匍匐在大地上的生命的诗意重构——唯有让苦楝在记忆里永远绽放,才能让那个“满脸皱纹来到世上”的婴孩,始终保有与苦难对峙的温柔武器。
远文获得了自己的名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远文却说:“远是辈分,文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质朴、纯粹,并无任何新意与深意。”
出水痘,出麻疹。远文第一次感到,生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并幻想着能够一直病下去。当远文经历了奶奶的死亡,大姑姑与二姑姑的死亡,大哥、二哥、二姐的死亡,并亲手将年迈的母亲与父亲埋葬掉,远文逐渐明白了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箴言:“苦难没有价值,对苦难的凝视才有。”
两个妹妹来到人间时,“青蛙似的”,目光呆滞。屋是老屋,斜得松松垮垮,摇摇欲坠。松木壁板,变形腐烂。“床头屋漏无干处”时,瞄准漏的位置,脸盆、水桶、瓜瓢、大瓷碗,全派上用场。烂了个洞的竹篾簟,油腻得黑不溜秋的破棉絮,整个冬日寒冷的漫漫长夜,“我都是那个渴盼春天第一个到来的人”。漏雨的茅屋瓦缝折射着杜甫的星芒。事隔多年,恰如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所写:生活,就是扛着痛苦穿行人世间。慢慢地,所有的苦难都熬成了酒,酿成了诗。
饥饿,对于少年远文来说,是更能贴近,甚至匍匐大地的一种手段。大地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成为远文身体的一部分,生长着,力量着,心有灵犀地活着。
让生命贴近山边溪岸的一棵树、一丛草、一朵花、一只鸟、一尾虫,远文觉得它们是念兹在兹的恩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值得好好地敬仰,好好地看护,好好地善待。
远文像一头牛一样,不急不躁,慢条斯理地反刍。躺在牛吃过的草地里,听石头与溪水说话,青草与泥土说话,小鸟与枞树说话,云朵与天空说话。
鸟鸣流水,群山炊烟,初来乍到的远文,比孤单还瘦弱,比泪水更忧伤,却又不得不满怀一丝希望。
二
低处,也会黎明。炊烟升起。蓼子草给泥土上色,花朵为果实让路,一只瓢虫趴在露水里击壤而歌。晨光熹微中,少年远文渴望从自家的水缸里舀起半瓢月光。
月光,是个好东西。半夜三更的,洒在庄稼地里,浮在树梢、草叶上,也溶在屋瓦、篱笆中。晒谷坪里,草树垛中的嬉闹,野天野地的刺激,那是属于少年远文的月光。人随锄倾,锄随人动,这是属于父母、大哥与二哥的月光。看着月光一点一点流进父母的皱纹,流进大哥、二哥的眼睛,流进土地的深处。犁田耙地,割茅打草,伐木烧炭,拾柴火、捡稻穗,扯猎草、熬猪食,生灶火、煮夜饭。想起灶台那口嗷嗷待哺的锅,想起五黄六月的愁眉苦脸,远文不知在何处完成自己。这些诗性隐喻的笔触,令人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乡村诗人克留耶夫——同样是用最土气的方言,讲述最形而上的哀愁。
米酒,烟叶哄来的故事,让远文打发掉懵懂而又瑟索的童年。远文开始探寻马底驿的来历,有了探寻自己命运的欲望。想看见一匹马,骑上一回马,差不多成为少年远文最大的梦想。
收油司、取吓、安煞、安六甲、掐时、杠仙。远文觉得这些诡谲的奇门遁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甚是魔幻。巫风傩韵,让远文产生阅读《九歌》《山鬼》的兴趣。文白夹杂,这种独特的语言实验,是远文刻意为之的“陌生化”策略,旨在打破流畅阅读的惯性,迫使读者驻足沉思。它既是远文在乡土口语的鲜活质地,与古典书面语的典雅韵味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也隐隐透露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犹疑与张力。这种语言的“毛边感”,本身或许就是远文贴近“大地”的粗糙与真实的某种隐喻。
远文心中的月亮逐渐丰满。庄稼与月色喁喁私语。晨曦的炊烟,与月色最为亲近。他等待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小草开始拱出许多鸟儿的叫声,脆脆的,沾满无可比拟的露水。远文的文字不是描绘风景,而是唤醒沉睡在万物内部的灵性。
积肥、双抢、捡茶籽、参加学校建设。远文觉得自己该习得另外一种本事,需努力读书跳出“农门”。抬头听课,低头走路。远文逐渐明白,山并非完全不动,是水在替它走得很远很远;水也并非一直匍匐得很低,是山在替它站得很高很高。
当月亮升起,一些远方正变得暧昧而温暖。
远文精心编制日常生活的经纬,正如梭罗所言:“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青灰色的汉字如种子般沉入时光的土壤,就像《小王子》里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远文的乡村书写呼应了全球范围内“在地写作”的思潮。他试图呈现那些被文明割裂的、被速度遗忘的、被虚荣遮蔽的生命本相。
时间之上,月光之下,远文的窗台竹影婆娑。这是远文的大地与时辰。一个以节气与时辰为经纬、经由他细细抚摸过、流浪过的世界。
三
如果说,童年的苦难让远文学会俯身触摸泥土,那么,青年的阅读则教会他仰望星空。
远文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村小,这所村小是远离集镇甚至远离国道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所以他最初考虑的应该是参加自学考试,考大专,读本科,去教初中,教高中,这几乎是当时的他摆脱村小,通往集镇和县城的唯一出路。我愿意相信,写作只是他读书过程中的一丁点副产品而已。
夜钓、排筲、炊炉子、喝大碗的米酒。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待在学校,黑天墨地寂寂地守望。自制煤油灯,将黢黑的夜燃出一丁点光明。
灯下,远文读老庄、读孔子、读离骚、读老杜、读西厢、读红楼、读神曲、读浮士德、读莎士比亚。无数的哲人智者穿越历史的天空,用其博大的智识,滋润一脉迷失久远的心魂。“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 一个人寂寂地享受着读书的时光,守望那一畦碧绿的精神家园,灵魂便有了一种沉甸甸的丰盈。
远文对柳宗元的偏爱,不仅源于文学上的敬仰,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远文固执地相信,柳宗元的永州之野是可以咏而归的精神家园。他在永州的山水里,看到了自己栖居的“怡溪”村小的影子。远文与柳子相隔了无数个朝代,却因“龙兴”而近,因永州而亲,感到彼此并不陌生。永州十年,是柳子最艰难,最孤寂、最郁愤的十年,山川小景,风物人事,丘涧溪石,莫不使柳子在困顿中轻叩生命的价值。“生下来,活下去”,远文与柳子的隔空对话,让他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远文或许也会在某一天,望着怡溪的流水,默念一句:“此心安处是怡溪。”
长沙的某个小宾馆里,远文在等待,等待一场大自然风雨的到来。以此为引,远文方能斜进风雨之中,直奔湘江岸边的杜甫江阁,然后坐着闷罐车一路向西,让自己微弱的身躯,贴近杜甫的精神肌理,在千年时光的飞翔里与杜甫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远文追寻着杜甫的足迹,看见他在流浪的路上把世间所有的苦难一点一点地收拾,掮起。看见他一面颠沛流离,一面忧国忧民。远文感叹:“一生漂泊,身在草野,贫病潦倒,怀才见弃,然而落日楼头,仍是心忧社稷,乾坤之内,天地之间,此等腐儒能有几人?”
世事芜杂,路在远方。远文明白,一个诗人之所以伟大,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建立在社会和历史的根基之上。杜甫作为一介布衣,却始终关注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这样走过他伟大的一生。他没有别的办法来为这个时代改变什么。他用诗含着血泪把这个时代的苦难给记录下来。杜甫代表的是社会的良知,是贴近大地心忧天下,他的心始终在人间。这是远文偏爱老杜的地方。可以这样说,远文继承了杜甫“在个人苦难与大地褶皱中书写普遍人性”的伟大传统。在当代浮躁社会中,这种“贴着地面飞行”的悲悯视角尤为珍贵。
四
远文读博尔赫斯,最迟应在他儿子读高中时。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大约在2007年被选入湖南的语文教材。这是博尔赫斯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首末之间,无穷无尽。远文笔下具体而微的乡土风物,如同博尔赫斯那些无限的书页,同样承载着宇宙的密码和时间的褶皱。他们都试图在具象中寻找抽象,在有限中窥见无限。这回应了人类对永恒与意义的共同追寻。
从村小走出去的远文,做电视,做教育科研,做专职督学,对诸多风物人事有了幽微切身的生命体验。于是乎,书越读越多,路越走越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灵魂越是远行,身体越是在低处扎根。他从初醒的码头出发,在烟雨中来到肖家桥,坐在北纬二十八度草木碣滩的深处,远文试图将自己坐成一座山,只此青绿,馨香四溢。梦回明月山,远文“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在莲花池,视浮云而意长。在老洞村,高山枯荷,蕴明月之诗。在垣上,远文听见古老的苗歌,仿佛是从土地深处迸出来的,裂隙而出,随风而至,经得起绝望,也承得住欢颜。在虚掩的板梁,远文远远地看着,这个村落用美好的想法,应对生活与生命的不幸,用一双大大的脚板,将驿马古道漫长的日子,一天天走黑,又一年年走亮。远文行走的奥秘,不在于低处的位移,而在于每一次驻足时灵魂的震颤。
越是靠近龙场驿,痛风就越是发作得厉害。痛风困扰远文已有多年。《西辞东归》以“痛风”这一现代顽疾切入,颇具深意。低处的苦难可能成为精神的磨刀石。当远文因足疾“呲牙咧嘴”瘫坐在大碑垭口时,与五百年前“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的王阳明形成了奇妙的疼痛共振。身体痛感在此成为“破心中贼”的修炼道场。他对待苦难的态度,可以联想到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在荒诞与苦难中寻找意义。作者刻意放大痛风的感官强度,是为了印证心学的根本命题:外在困厄终将回归内心战场,真正的自由不在免除痛苦,而在超越痛苦的认知重构。当远文在文末凝视“正在凋落的树叶”,那抹疼痛淬炼出的澄明目光,恰与阳明“此心光明”的临终偈语遥相印证。远文的行走与书写,本身就是一种“事上练”,是对“知行合一”的当代实践,以此证悟,精神的高地可以在最卑微的泥土中筑就。
回到大唐龙兴讲寺,那里有飞檐翘角的袅袅梵音,有可以摒除一切纷扰的心灵袈裟,有可以为灵魂沐浴的佛风天雨,有坐看云起时的生生不息,有入定凝神的物我契合,有自然悠远的耐人寻味。当阳光透过古老的窗棂,将斑驳的光影投在青砖地上时,现代人浮躁的心灵或许能在此找到片刻的宁静,于不动声色中完成一番精神的洗礼。那些被阳光晒透的唐砖宋瓦,在远文的文字中重新获得了呼吸的韵律,让龙兴讲寺不再只是文物保护名录上的编号,而成为流动的精神现场。古树、碑刻、古道等意象,在几篇散文中反复出现,固然可视为某种“文化大散文”范式的痕迹,但更深层地看,它们构成了远文精神地图上的关键坐标点,是其反复叩问历史与存在的基本语汇。这些“反复”的意象,如同他行走大地时一次次确认的精神界碑,标记着他与这片土地深度对话的轨迹。
武陵苍苍,沅水汤汤。虎溪山,王阳明传授“心学”的“处女地”和第一站。虎溪布道,是王阳明在湖南讲学时间最长、弘道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举。虎溪山,由此而高大峻茂,成为一座澄静之山,良知之山,本性之山,光明之山。知行合一,搞教育的远文,怎能不对阳明先生顶礼膜拜呢!“极目远眺,对岸的一脉群山,无不像一个个手执朝笏的大臣,面对着虎溪山遥相揖拜。”当远文在虎溪山追寻“此心光明”时,是否也如阳明先生一般,将“低处”的苦难抽象成了精神修炼的祭品?立功、立德、立言,这将是远文全部的日子与所有的追寻,即便有所遗憾,也都是对未来的成全。
春意漫上书山。人们大可不必纠结,隐逸在武陵与雪峰山脉深处的二酉山,到底是不是中华书山。文字在竹简上逃亡,又在纸张里重生。远文认为,无论伏胜藏书于鲁壁,抑或是藏书于二酉,都已成为一种文化与文明薪火传承的意义与符号。“书山”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的象征。
夜深,许多事物沉沉地睡去,惟月光与书山醒着。黎明,远文仰头看见,书山顶上,一方蓝色的海正在追赶着天空。
五
小满已过,芒种未至。夜雨落在二酉山的青石阶上,远文的文字便从石缝里长出茸毛似的苔藓。这让我想起他描述过的某个清晨——父亲佝偻着腰,在贫瘠的泥土里埋下土豆,而少年远文蹲在田埂,第一次发觉腐烂的块茎也能举着嫩芽向天空宣示主权。
《大地时辰》里所有匍匐的姿势,最终都获得了垂直的张力。就像王阳明在龙场驿的瘴气中豢养光明,杜甫于漏雨的茅草间囤积星斗,加缪的西西弗斯在推石上山,他们无疑,都在某种悖论里种植坚韧与自由。远文用湘西的方言改写了这些崇高的命题:当他说“苦楝树在记忆里永远开花”,实则是将米沃什的“凝视苦难”具体为一场与草木的终身谈判;当他在痛风中辨认阳明的足迹时,疼痛不再是身体的溃败,而成了精神的海拔仪。
那些被反复铭刻的大地风物与生命印记,那些时光切片中的凝神谛听,那些融通古今文字与文体的尝试与探索,此刻显露出真正的隐喻——它们都是时空倒置的彗星,根系在云端燃烧,树冠却深扎地心。这或许就是生命诗学最悖谬的真相:唯有在低处才能完成向上的测绘。远文用《大地时辰》证明,最饱满的呼吸来自俯身时,胸膛与大地形成的触感、痛感与连接,就像他十八岁那年,黑板擦得白灰沾满面颊,而博尔赫斯的沙之书,正在地球的另一端翻动无限的页码。
当然,远文作为有意还是无意的当下土地与生态文学书写者,在特有的地域化、边缘化与同质化的多重夹缝中试图确认并表达自身,同样存在着突破与新生的困囿,特别是在城乡转轨的裂痕中,如何抚慰退守的灵魂、摆渡分化的价值,亟待更深的叙事勘探,从而,呈现出乡土叙事内在格局的普遍性、异质性与镜像映射,形成变革浪潮中乡土精神的独有内核与文化价值的新形态。
合上书页时,我忽然有些明白,远文为何要固执地推迟苦楝的花期。在植物志之外,他预留了一处时间的暗舱:当现实的苦楝早已结籽,文字的苦楝仍在绽放。这是写作者的特权,也是匍匐大地者的秘密——所有被生活收缴的,都将在时光的飞翔里重新破土。就像此刻,我案头的《大地时辰》正渗出沅江的晨雾,而某个即将打开这本书的人,都将会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无法释怀的伤口里,种下一棵开花的苦楝树,让它的影子,成为大地的年轮。

张远文,中学高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生态文学分会理事。著有散文集《醒着的灵魂》《河流在人间》《大地时辰》等,曾获“中国当代散文奖”。
来源:红网
作者:陈源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