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旅战斗意象的“两栖”抒写
—— 从堆雪的军旅散文诗谈起
文/彭流萍
自古以来,军旅诗词以其雄浑激昂的阳刚之气,团结了中华儿女,凝聚起捍卫民族尊严的浩瀚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诗创作的洪流像潮汛般席卷而来,革命风云和抗日硝烟也催生了军旅题材新诗的发展和创作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涌现出一批抗战诗歌。其多为“战歌式”表达的口号诗,情感激昂,直抒胸臆,朗朗上口。 如杨靖宇将军的“世上岁月短,囹圄日夜长。民族多少事,志士急断肠”等等。这些诗句情绪激昂,剑拔弩张间尽显沥胆披肝之勇,令人血液燃烧,多有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豪情。这是民族大义与自我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再如,1942年,戴望舒创作的一首新诗——《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其语言表达方式,较以往之前有了更自由的形式及更加深刻的隐喻性。
新中国成立后,军旅新诗的创作不断从内容和形式上回应时代发展变革。实现了由“战歌”的口号式表达到“颂歌”式的赞美抒情(例如:徐放《新中国颂歌》、谢霞《“毛主席,毛主席”外一章》),以及演变为当代的“先锋性”特征的抒写(如周涛的《鹰之击》,简明的《更高的天空》)。中国是一个诗歌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中国新诗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军旅诗的文化因子又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诗歌文体——军旅散文诗。
这种新的诗歌文体巧妙地融合了散文的细腻描绘与诗歌的强烈表现力,在内容和形式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有学者指出,散文诗是表达心灵或主观情绪的文体,它以一种自由的形式抒发心灵或情绪及其波动。
在当代中国诗坛中,军旅诗歌的创作者们常常在散文诗的海洋中遨游,堆雪便是其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位诗人。他是一名渴望拥有暴风雪般的嗓子歌唱民族和家国的西北儿女,作为一位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军旅诗人,他的诗篇犹如西北狂风,粗犷中蕴含深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广袤土地的深切眷恋与对和平生活的热切期盼。
“我眼中咆哮而去的白天和黑夜/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我炎帝的龙袍黄帝的内经/我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我奔流不止 的青春光阴。”
——堆雪《黄河》
散文诗《黄河》气势恢宏,以其独特的诗意构建了思想与灵魂的内在联系,也深刻影响了读者的情感认知和情绪走向。
堆雪善于用灵动的词句将边关风雪、大漠孤烟、炮火硝烟和壮士乡愁进行诗意重组。句式大都短小精悍,意象清美,声韵悠扬,却又透出柔中带刚的动感。堆雪的散文诗饱含军旅生活的硬度,不仅有对军旅记忆的回望,还表现出作为诗人的巧思深情,成为触及军人精神和灵魂的钢铁赞歌。
综观堆雪的军旅散文诗,我认为他的作品兼具散文外观和诗学涵养的双重基因。他的作品不仅蕴含散文的灵动抒情,还融合了诗意的情感灵感与散文的深邃幻想。这二者缺一不可的灵性之光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空间的诗意浪漫,以致“情”与“景”融合抒情,从而形成了散文诗的“交叉体”,这些精神特质已成为堆雪诗歌气质的重要美学标志。我个人认为这 可概括为“军旅散文诗的两栖性”抒写现象。
堆雪在散文的形式上,赋予了诗歌更加动情与感性的诗意表达。这些句式结构工整,语言虽朴素却蕴含丰富情感,带着微妙的“隐性”色彩波动,其动感内容中隐藏着不动声色的智慧火花。从抒情本质来看,堆雪的散文诗有别于一般性的浅意表达,他的文本更倾向于隐喻性。每一个词语背后仿佛都有千言万语的诉说, 每一次停顿都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和思考。这种情感与哲理的交融,使得读者在赏析其作品时,不仅仅是对文字的解读,更是与心灵的对话。
“大风、大风。旌旗拂动,刀剑丛生。大风、大风。铁血交织,砥砺灵魂。大风。只有大风中片甲不留的厮杀,才能平息我挥戈边塞、壮怀激烈的心胸。”
——堆雪《雄关》
在《雄关》这篇散文诗中,堆雪善于用散文的美学特质,借助短句和标点符号调控抒情的节奏与起伏的幅度。同时,堆雪以“自我对话”的方式呈现了人物丰富的心理活动,增强了沙场点兵的现场沉浸感。不容忽视的是,诗人在其作品中一直保留了散文的抒情内核,其大部分作品是以舒缓柔和、清丽明亮的笔调,深情地谱写了一支支铿锵有力的剑胆琴心,呈现出灵动而又精巧的“音符式”抒情,这种抒情方式,在《雄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堆雪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出战斗与情感的交错,让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让读者在感受壮烈的同时,也能品味到那份深藏不露的悲悯与温柔。
堆雪的散文诗,其音律宛若清弦,其对诗意的凝练恰如热血边关与铁血丹心的气质展现。此外,堆雪还深谙散文的抒情和议论功能, 他擅长将散文的抒情元素和美学特质融入诗歌中,从而使诗歌作品散发出热烈而健硕的艺术气息。同时,他常将家国情怀与边塞风光的随想情绪巧妙融入诗歌之中,或许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其独特的“自我素描”。例如:
“寂寞落下来,成为今夜的月光,草里的霜降。哨兵肩枪,在三五平米的哨位,踱来踱去。”
——堆雪《夜岗》
“我看见很多山峰集合,在唱同一首歌。 那些钢铁与热血串缀起来的音符,都被歌唱成熊熊火焰和深情的玫瑰。”
——堆雪《军歌》
“枪,躺在战士怀里,像个熟睡的婴儿。战士怀抱枪支,在哨位上踱步。战士骑马巡边, 月光在马蹄下碎裂成冰。”
——堆雪《月亮》
深入剖析堆雪的散文诗文本,可以发现其中充盈着号角、硝烟、冲锋、阵地、担架、伤口等丰富的意象……不难发现所有的抒情对象不仅仅是“名词”或事物本身,其中既有金戈铁马的豪放、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和壮士思乡的凄美悲愁,更有反映边塞生活和大漠风光的新边塞诗。
边关的豪迈与战地的苍凉共同构成了堆雪笔下的世界,使得他的散文诗不仅仅是一幅幅雄浑壮丽的画卷,更是心灵深处的呐喊和时代的回声。堆雪的散文诗既有军旅生活的诗性抒写,也有士兵情怀的灵魂歌吟,它宛如铁血沙盘中的精神熔炉,更是诗人对迷彩青春的深情回眸。在堆雪笔下,每一场战斗不只是硝烟与战火的交响,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他用文字构建的沙场,不仅仅是对战士英勇的讴歌,更是对人性光辉与家国情怀的颂扬。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既能“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又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堆雪凭借诗人特有的细腻笔触,将声律的动感和丰富的情绪融入诗歌,借助散文与诗歌相互交融的“两栖文本”形式,在散文诗的广阔舞台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军队的时代风貌,深刻揭示军人内心深处那奔腾不息的热血、难以安放的军旅情感以及深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则汇聚成强大的诗歌力量,激励着读者,推动着读者团结奋进。
堆雪是诗人也是画家,在诗歌中对颜色、线条和彩光的运用,尤为巧妙精致。堆雪曾在散文诗集《兵词》中为自己创作了六幅插画,这些画作界限清晰、构图严谨、主题突出,且偶有抽象派风格的巧妙融入,从留白与填充之间可以清晰地品察到他握笔的速度和力度。这些画的线条刚劲流畅、黑白对比适中,画面视觉传达效果细腻光滑,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图和谐之美,从而铸就了堆雪独有的西北艺术风格。
作为散文诗作品中的艺术插图,他的画作内容形式与散文诗相辅相成。堆雪是根据散文诗作的内在灵魂进行创作,它们在绘画意义上和艺术表达上建立了必然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了图文并茂、情景交融的“晕染”效果。
堆雪将苍茫大漠、军人的硬骨豪情,精细入微地刻画成诗。那些具有金属质地般美感的句子,饱含了诗人的热血兵情。同时,他将散文和诗画的抒情基因进行了整合,从而产生了 独特的美学效应。在堆雪笔下,诗与画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字与色彩的堆砌,它们化作了士兵们内心世界的缩影,是情感与思想的载体。堆雪的创作,将散文与诗画的抒情元素相融合,催生出独特的美学效果,进而形成了“诗画独 立性”的美学特色。在堆雪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那股通过沙场烽火铸就的英雄气概,和那份对祖国山河的深情眷恋。
在军旅散文诗的广阔天地里,堆雪以其独具特色的西北风格笔触,为描绘军旅战斗意象的“两栖”书写增光添彩。他运用散文诗的语言勾勒出军人英勇无畏的形象,那是一种超越了平凡的热血与担当。这种“两栖”书写,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战斗场景下军人的心灵世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军旅生涯中战斗的多面性与深刻内涵。在未来的军旅创作道路上,相信这样的探索与书写会如璀璨星辰,持续照亮这片充满力量与诗意的天空。


彭流萍,青年学者,1987年生于江西大余,在《诗刊》《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诗探索》等近百种文学期刊、杂志上发表诗歌、长篇通讯和报告文学及文艺评论。 曾荣获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解放军报社和《人民文学》征文奖、“年度十佳新锐诗人”和《扬子江》优秀诗歌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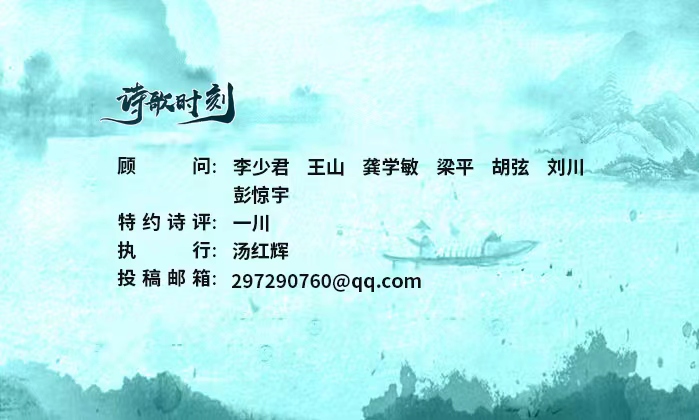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彭流萍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