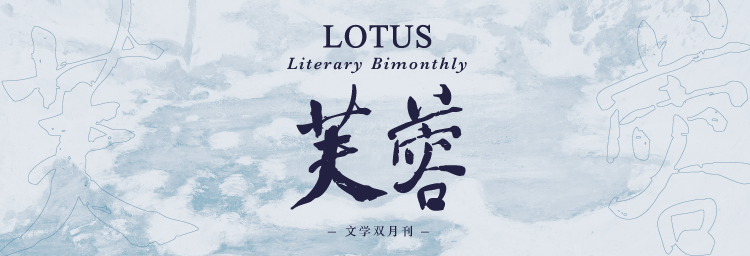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短篇小说)
文/东君
接到一个电话:我这就过来,你给我等着。
他怔了一下,想问你是谁,对方却已挂断。
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为什么要冲自己说这样一番话,口气里带着一股要把人放倒的狠劲。他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近来遇到的人与事,好像没有得罪过什么外人,也没说错过什么话。问心无愧,也就稍稍镇定了一些。回头翻看来电显示,对方手机号下显示的归属地是本市。会是谁呢?一大早给我打恐吓电话。他嘀咕了一句。妻子从被窝里伸出手来,说,可能是谁打错了电话。不对,他说,打错电话,现在如果反应过来,好歹也得跟我道一声歉。他由疑惑转为愤怒,根据原号回拨。对方已关机,他也就不加理会了。这一大早,接到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他的情绪莫名地变坏了。妻子伸出另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被子像波浪一样拱起来,她似乎要把他再度摁进水里面。
不对,他坐了起来,对妻子说,不管对方是否打错电话,我不能就这样草草打发过去,我得让对方给个说法。
算了吧。
既然对方说“我这就过来”,说明他已探明我的住址。
也许他打的是你的电话,去的是另外的人家。
沉默半晌,他又下了床。双腿滞重,两眼飘忽。那一刻,他察觉到墙上的木质挂钟竟出现了异样:时针、分针、秒针……不对,居然少了一根。细看,少的是短针,也就是时针。为什么会少了一根时针?他很纳闷。少了分针和秒针,大致还能判断现在是几点钟;少了时针,分针与秒针就仿佛是在一个圆圈内盲目地转动。他不知道是这个挂钟出了问题,还是自己的眼睛或脑子出了问题。有的问题,你不去关注或谈论它,就不会成问题。没有,哦,什么问题也没有。他这样对自己解释。这个时辰,他通常会在小区对面的公园跑一圈,但今天上午他断然取消了这项运动。他要坐在家中,等待那个说“我这就过来,你给我等着”的家伙。
你要吃点早餐?他转头问。不想吃,妻子说,只想再睡一会儿。他说,梦又不能当饭吃。妻子说,我的早餐就是梦,我是吃梦长大的。妻子张了张嘴,表明自己的舌头上也有一股淡淡的梦的气息。
桌子上有一瓶标有英文字母的药,已经吃了一半。
他正要打开冰箱取出做早餐的食材时,门铃响了。
这么快?他随手抄起一把菜刀,走到门口,一只脚往后挪了半步,重心就落在后脚。恐惧在手心呈颗粒状分布。谁?他问。我。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是隔壁大婶。他把菜刀换到左手,藏在身后。门虚掩着。隔壁大婶递上一个蓝色塑料袋,说,几天前你太太发微信给我,托我顺便给她带三斤生鲜鸡爪,说是要做泡椒凤爪,记得放冰柜哦。他打开袋子瞄了一眼,脑子里顿时浮现出美甲广告里那些鲜艳欲滴的手指。好吧,他说,我会记得放冰柜。隔壁大婶把头探进来,略带迟疑地问,最近怎么不见太太出门?他指着紧闭的房门说,她还在床上躺着呢。大婶立马接过话说,哎呀,是不是害喜病?恭喜恭喜。他只是微笑着,仍然没有打算把门敞开。他跟太太不同,不太喜欢跟这些称之为邻居的人交往,偶尔在电梯口遇见,也只是露齿一笑,或搭上一两句话,然后就是形同陌路。
隔壁大婶走后,他在门角站了一会儿,感觉她好像并没有走远。他透过猫眼,瞥见她依旧站在消防门的位置,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他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随即听见对面传来关门的声音。
他从客厅走到厨房,然后又从厨房走到客厅,就这样像挂钟里的那枚秒针一样,拿着菜刀转了几圈。他没有发现异样的东西,但异样的东西似乎就在看不见的地方。
早餐还在锅里热着。他拿着刀叉,对着空盘子,切着想象中的面包。刀叉闪烁着寒光,让他想起前阵子在手机视频中刷到的一起连环凶杀案。凶手连杀了七人。从种种迹象表明,他杀人没有明确目的,就是为杀人而杀人。他叫覃小勇,原生家庭有点复杂,其祖父、祖母以及父母均来自不同省份。他五岁那年,被诊断患有妥瑞氏综合征,经常会挤眉弄眼,抽动嘴角,有时还会发出一种猪啃槽的怪响。七岁那年,父母离异。九岁那年,他妈妈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被债主暴打、羞辱一顿。覃小勇读到初三就辍学了,从此外出谋生。
被覃小勇谋杀的人居然都是一些漂亮的女人,也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种“让人忍不住要回望一眼的女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初恋女友。杀她的理由简单得让人吃惊,据说是因为“她总是带着纯净的微笑”。为什么凶手不能忍受那种纯净的微笑?据覃小勇自述,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她突然告诉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结束了。他很平静地接受这个结局,但他每天还是照旧经过她的理发店,有时隔着玻璃张望一眼,有时会进来打一声招呼。每回闻到她头发里危险的气味,他就想提醒她,赶紧离开,赶紧。但她对眼前的人一无所知,总是保持着那么纯净的微笑。
她死在我刀下,活该。覃小勇说这话时眼角与嘴角习惯性地抽搐了一下。
面对纯净的微笑,覃小勇的脑子里出现了肮脏的想法。这是一名青年警察的描述。
视频中还回放了这样一个镜头,这名警察扭住了覃小勇的手,覃小勇没有丝毫反抗。
他的目光落到覃小勇的手上。这双手,纤细而白净,哪里像一双杀人凶手的手。他摁下了视频暂停键,仔细打量,竟发现,自己的手形竟跟凶手如此酷似。这个发现让他打了个寒战,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真凶。
事实上,他关注的不是凶手的手,而是这双手携带的一件作案工具。
警察抓住凶手后,收缴了几件作案工具,其中包括一把匕首。但警察的说法有点神奇,他声称自己进入凶手租住的房间时,就感觉空气里透出一缕血腥气息,嗅觉告诉他,有什么家伙就藏在床后某个地方。警察进去一搜,果然从一个印花布袋里搜出了一把匕首。他还发现,这把匕首上镌刻着三个古雅的字:覃世堂。跟凶手同姓。这就引发了警察的好奇心。在审讯中,警察问,覃世堂是谁?凶手说,他不知道覃世堂,只知道这把匕首是祖传的。警察又问他祖上有谁叫覃世堂。凶手说,他父亲上面的男人都死光了,他对那些“死鬼”(凶手的确是这样表述的)一无所知。警察审讯完毕,就找了凶手的父亲,出示匕首,让他确认这把匕首的来源。凶手的父亲承认,这把匕首的确是祖传的,而覃世堂应该就是他曾祖父的堂号,他原名叫什么已经没人记得了。清朝末年,覃世堂就在北京的骡马市大街开设了一家铁铺。有一天,一位姓黄的远房亲戚找到了他,要订制一个大铁罐。数日后,这名姓黄的远房亲戚过来取货,随行的还有一位仪表不凡的摄影师,姓汪。摄影师请覃世堂吃了一顿酒,还给他拍了一张照,作为回报,他回赠一把匕首。又过了数日,官府在后海北岸的银锭桥下发现一个大铁罐,里面埋有炸药。谁都知道,银锭桥是摄政王载沣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一旦引爆,必定发生大片死伤。清廷迅速派出警察,一边布下疑阵,一边在暗中侦查。警察根据京城内的铁匠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骡马市大街铁匠铺主人覃世堂,并拘捕了他;之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此次实施暗杀计划的两名主谋,姓黄的那位名叫黄复生,姓汪的那位就叫汪兆铭。有关这起刺杀未遂的事件,史书上已有记载,当然,细节方面各有出入。覃小勇的父亲在新闻记者的追问下,还补充了一个史家不曾提及的细节:当时,警察从汪某身上还搜到了一把匕首,而匕首上赫然镌刻着“覃世堂”三字。因此,覃世堂即便没有参与此次行动,也受到株连。他只是一介普普通通的铁匠,因此就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或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警察为了查明这把匕首的真实来历,竟联系到了一位京城的文史专家。那位文史专家谈起了汪兆铭当年与另外几名热血青年刺杀清廷大员的经过,他认为,那次行动缺乏严密的计划、周详的照应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后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清廷大赦政治犯之后,汪、黄二人也因此获释,成为被世人追捧的英雄。尤其是汪兆铭,他的才华与气度在当时曾被京城内外的开明人士屡屡提及。
谈到这里,文史专家拿起那把匕首说,虽然汪兆铭曾写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但现在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把匕首跟刺杀摄政王的汪氏有关。坐在他身旁的一位文物专家对匕首做了鉴定,认定它确系一百年前所铸,所用的材质虽然并非什么上等精钢,但刀鞘的确漂亮,是用鲨鱼皮制作的,上面还分布着一些凸起的珍珠颗粒。
采访画面很快切换至覃小勇的父亲那边。覃小勇的父亲说,他的曾祖父就是因为这起刺杀事件死在牢里的。他究竟怎么死的,无人知晓。他死了之后,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英雄。但据他祖父说,有一天,有个穿洋装的人带着一把匕首来到“覃世堂”店铺,亲手交给覃世堂的儿子(也就是讲述者的祖父)。这个穿洋装的人说,这是一位名叫汪兆铭的人出狱后用几两碎银从狱卒那里赎回的,并托他送还“覃世堂”。但京城的文史专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此事查无实据,只能当作民间野史来看待。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东君的短篇小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有《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鱼》《面孔》等,另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树巢》。曾获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东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