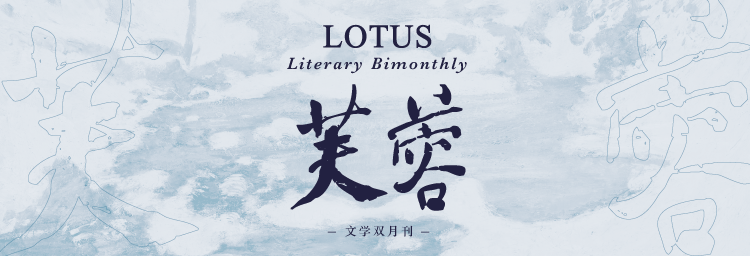

复兴巷(中篇小说)
文/冉正万
老照片
当我发现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时,不禁吃了一惊。桌子上有我最喜欢的两个菜:新花椒焖新洋芋、折耳根炒老腊肉。除了五花肉,其他都是本地出产的新鲜食材。每个新洋芋拳头般大小,匀称光滑,焖熟后再浇上花椒做的肉末辣椒酱。花椒要早上挂露水之前采摘的闭口椒,小把放进冷油浸一会再加热,不可煎炸,更不可一粒粒摘下用,摘零散的花椒容易误吃,一口嚼碎,嘴像被电击一样麻。老腊肉来自黔西北,夜郎古国的黑毛猪,已有两千多年饲养史。肉煎熟后,肥肉上鱼子般半透明的小泡泡,里面全是香味,咀嚼时在口腔里爆炸,几十个香味炸弹同时释放出香味,让人猝不及防。野生折耳根半生熟,是另一种冲劲十足的气味,既能解腻,又独具药腥味。两种香味叠加,魂魄飞出去三分钟才重新回到肺腑里。两个菜我都尝了一口,什么味道也没有,就像它们并非真正食材,是只能看不能吃的道具。我喝可口可乐,同样尝不出味道,没有气泡在舌头上跳动,连冷热也尝不出来。像在表演,像在假装喝。我可是真喝了一口的。安安自言自语:“不晓得爸爸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我们好开始吃。”她妈妈说:“吃吧吃吧,他吃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不吃也罢。我对自己有小小的不满,但没有沮丧,因为我没有胃口,并且一点也不饿。
我最大的不满是最近拍摄的照片。没有一张满意,看上去极其陌生,内容空洞,只有大块几何形状,没有细节。
我叫孟多,住在南明河畔复兴巷,从小就住在这里。二十七岁开河畔相馆,对复兴巷每个角落都熟悉,也拍过不少照片。给相馆带来广告效应的是闻梅和她男友的合影。他们两个都不是复兴巷的人,闻梅是一医护士。贵阳人说“一医”语速快了像“爷爷”,它确实是一所爷爷辈的医院,1919年创办,当时叫贵州省立医院,一九六二年改叫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简称一医。一医叫省立医院时名字很大,占地很小,凌空俯视,博爱路像大树主干,复兴巷像枝丫,省立医院像枝丫上的鸟巢。随着市政改造和医院扩建,医院越来越大,博爱路越来越短,复兴巷越来越窄。原本不那么宽的都市路反倒变得又宽又直,一医成了都市路上最大的机构。如果都市路是一条大河,一医就是大河边上的博爱号轮船。面向都市路,背靠复兴巷。
闻梅出现在复兴巷是因为护士长齐兴。齐兴上白班时请闻梅来照看四岁的儿子胡老三。闻梅也是护士,几年前齐兴带过的实习生。胡老三的舅舅和街坊都叫他胡老三,齐兴对此非常不满,“他才四岁,为什么要加个老字呀。”她叫他三或小三。三是小三的昵称。那时“小三”一词并无歧义。三是她的小儿子,她没有再生。小三的爸爸是一医心内科医生,早出晚归,也没法照看儿子。
闻梅的男朋友是飞行员,机场当时在花溪区潮湖乡,磊庄机场,从贵阳过去五十多公里,没有公交车,闻梅的男朋友只能乘坐机场通勤车进城,来一次非常不易。
闻梅的男朋友每次来都把皮鞋擦得锃亮,是贵阳最亮的一双皮鞋。复兴巷全是黑瓦房,黑瓦的黑厚重,闻梅男友皮鞋的黑青春。他走进巷子,像踩着一团发亮的冰火。巷子里的人说不是他擦得亮,是他的皮鞋太好,是飞行员专供,其他人想买也买不到。我把他们的合影放在相馆外面。这么英俊和漂亮的人并非没有,但那双皮鞋一定没有。我给他们拍的是全身照。镜头微微上扬,皮鞋变宽了,但亮度得到最好呈现。有人问我,他们是不是演员?得知男生是飞行员,照片里的人得到的赞赏远远超过演员,飞行员不但帅,还很神秘,据说他们的待遇和饮食比市长还高,这虽是道听途说,但没人不相信。飞在天上,不把最好的给他们吃怎么行。
“天天吃鱼吧?”
“天天吃鱼哪个遭得住,肯定是熊掌和海参换起吃。”
只有胡老三不把飞行员当回事,他自己也有一双小皮鞋,并不喜欢,他喜欢光脚。飞行员进屋后,闻梅阿姨叫他自己玩。他玩了一会就感觉闷闷不乐,心头有股小小的怨气出不来。他不知道这叫吃醋,只知道飞行员一来闻梅就不准他进屋。他的下巴前突,生气时下嘴唇嘬得更加厉害,他用下嘴唇包住上嘴唇,从而包住了眼泪。哭或不哭于他不是看心情,而是看有无好玩的事可做。这天他找到比平时玩过的游戏更好玩的事情,他看见飞行员锃亮的皮鞋放在门口,他一下有了主意。他把它拎起来,丢进屋檐下的烂泥沟。这是排屋檐水和生活用水的土沟,邻居养了两只鸭,它们整天在土沟里拱来拱去,造出半沟稀泥。皮鞋掉进去后,慢慢下陷,在泥浆即将灌进鞋子时停了下来。胡老三干完这件惊天大事后跑去找小朋友玩,他知道肯定会挨骂,闻梅阿姨不骂妈妈也会骂。
他误解闻梅了,闻梅从烂泥沟里拔出皮鞋后谁也没骂,她以为是复兴巷某个街坊看不惯她和男朋友在护士长家约会,他们毕竟没结婚嘛。她借故不能再帮护士长带孩子,再也不来复兴巷了。她和男朋友的合影是飞行员第二次来复兴巷叫我给他们拍的。他们恋爱已经两年,飞行员还要飞行一年才能和她结婚。
我自己最在乎的照片不是闻梅和男朋友的合影,而是我唯一的摄影作品。
南明河流到复兴巷一带转了个大弯,以前叫杨柳湾,外弯有片沙滩,水浅处芦苇茂盛,有上百只水鸟在芦苇里做窝。我去给省实验中学毕业班拍照,从河边路过,拍了幅大鸟给小鸟喂食的照片。我只会照相,不懂摄影。在报社工作的街坊把照片投到《贵州画报》,编辑取名《母爱》发表,给了我十块钱稿费。十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大钱,可以买八十个鸡蛋。但我高兴的不是十块钱,是自己的名字被印在画报上。我被书籍的神圣感震慑,一直以为它与我这样的人无关。看到母爱后面“孟多摄”三个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后来自己投了几幅,编辑回信说:“你还是好好照相吧。”好吧,我好好照相。
这天齐兴突然带着全家来相馆,叫我给他们拍全家福。原因是胡老三大醉。单位登记住房情况,胡医生中途回来拿户口簿,看见胡老三歪在新做的沙发上人事不省,忙把齐兴叫回来,齐兴把儿子翻过来,看见嘴角挂着一粒米,拈起来闻了闻,发现是醪糟,贵阳人叫甜酒。齐兴早上给胡医生煮汤圆,罐头瓶子没拧紧,胡老三被香甜的气味吸引,把剩下的甜酒喝个精光。这奠定他一生对酒的喜爱。胡老三昏迷的样子把胡医生吓坏了,他们决定拍张全家福,齐兴叫我给胡老三单独拍一张。胡老三坐在比他身体小得多的藤椅上,在我按动快门之前险些一头栽下来,幸好被他大姐拉住。照片效果出奇地好,胡老三笑得特别深邃,或许是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好笑的场景。每个看见这张照片的人都会被他的表情逗笑,没有人不好奇,他到底在笑什么。他的笑容吸引了不少家长,他们纷纷带孩子来照相。那几个月生意非常好,比以往两年赚的还多,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和胡老三这张相比。我不得不承认,按下快门的瞬间已不是我在做主。在艺校当老师的街坊出钱让我把照片放大到二十四寸,这是我的放大设备所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画油画的老师,照片拿回家照着画,画了半年也没把胡老三神秘的表情画出来,他不好意思说,把照片带到学校,给一个叫谢啸冰的同事画,谢老师倒是把胡老三的表情画出来了,不过看上去不像小孩,更像一个老头儿,他抓不住胡老三的年龄。
放在橱窗里的照片也是二十四寸,和闻梅与男朋友的合影一样大。这是橱窗里最大的两张照片。橱窗是我自己设计的,做好才发现小了点。不过和整个复兴巷很般配,为了省钱,我们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因此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胡医生在屋檐下挂了个鸽子窝,是从乡下捡回来的蜂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复兴巷养蜜蜂。
非常可惜,闻梅和男朋友的合影,胡老三深不可测的笑连同底片都在大火中被烧掉了。那是疯子婆无意中点燃的大火。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冉正万的中篇小说《复兴巷》)

冉正万,1967年生,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部。曾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第六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
来源:《芙蓉》
作者:冉正万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