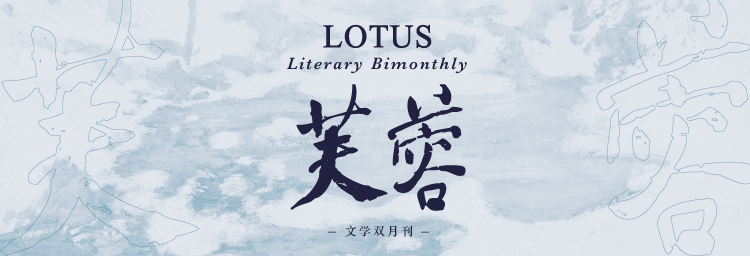

紫藤为门
文/欧阳娟
叶和庚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伐木工。认识他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对大多数跟我一样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来说,伐木工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职业。熟悉,是因为从小在书本上经常读到。陌生,是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交集。书本为这个职业提供给我的印象,是一群肌肉发达、衣衫褴褛的汉子一边从事着高强度劳作,一边用牙咬开借以补充能量的烈酒仰头往胡子拉碴的嘴里灌。我从没想到,他们当中的一员会有一天穿着西服、戴着礼帽、挺着瘦小的胸膛出现在我面前,满怀激情地告诉我,用紫藤搭架花门是极好的,到了四月,花穗会像瀑布一样垂挂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县城的宾馆开会,中场休息时,一个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靠过来说:“老顽童让你先别走,他要送东西过来。”我不知道老顽童是谁,也不确定这位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对我说话。他撇下这句话就走到男厕所门口的垃圾桶边去抽烟了。我一个女人,不好跟过去,也不好高声询问。我的工作环境中充斥着热络而又疏离的人际关系,这位工作人员便是其中一例。他在认为需要表现热络时,会拍着我的肩附在我耳边谈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他在认为需要疏离时,就是当下这个样子。我在忽冷忽热的淬炼中,逐渐打磨出随机应变的性子,别人想热便跟着热,别人要冷也跟着冷。那位工作人员冷冷地走开了,我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散会时,我和同事们簇拥在一起,有个年近七十的老人挤进人群向我鞠了一躬。一位老人行这样的大礼,我和同事们都不禁后退了两步。在人均后退两步的情况下,那位老人身畔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空地,跟舞台上的追光灯打出的效果类似。
三年前,伐木工叶和庚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瘦瘦小小、身板笔挺,着西服、戴礼帽,站在追光灯般的圆形空地里。
在我略显慌乱地向他还了个礼——也潦草地鞠了一躬后,他一手捂在胸前一手提着个塑料袋,以西方电影中常见的绅士对尊长或女士说话时使用的姿势微微躬着身体抬眼看着我说:“我是xxx,大家都叫我老顽童。”原来他就是那位工作人员所说的要送东西过来的人。他捂着胸前微微躬身的姿势和从下往上抬起眼睛注视我的神态,让他看上去更像在表演一幕话剧。
我没听清xxx是哪三个字。事实上,直到我预备写下这些文字时,才打听到那三个字是“叶和庚”。如他所说,大家都叫他老顽童,“叶和庚”的使用率几乎为零。
但老顽童的言谈举止一点都不顽童。他做完了自我介绍,放下捂在胸前的手,双手提着塑料袋缓缓递到我面前。我知道,那么个轻飘飘的塑料袋压根用不着双手去提,他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尊重。
他把塑料袋打开,以略带宠溺的眼神望着袋口说:“这是我从深山里挖来的紫藤,自己育的种。拜请您帮我带给李家辉老师。”
他的眼神让人错觉塑料袋里装的是某种活物,但他的语言显然说明并非如此。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两颗新出土的百合样的东西,剥开了加点西芹够炒一大盆的样子。如果没见过刚出土的百合,可能第一眼会联想到大蒜子,虽然形象偏差略微大一点。总之,我见到那两颗紫藤的幼种时,跟见到老顽童鞠躬时一样意外。日常所见的紫藤都是枝繁叶茂矫若游龙的,实在令人难以跟塑料袋里那两颗菜种联系在一起。
“……一颗是给李家辉老师的,另一颗本来是给他哥哥的,”在我思绪游移之际,老顽童还在继续说话,“但他哥哥在美国……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另一颗就送给您吧。”
送给别人的东西突然变成了送给我的,这让我尴尬又为难,连连摆着手,连措辞都零乱了。
他听着我结结巴巴的拒绝,解释说:“这东西很好养活的,能活几千年。”
几千年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此刻,我更为关心的是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有我这么个人?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开会?
老顽童对这种一般会主动加以说明的问题似乎毫无意识,只顾介绍紫藤的好处:“紫藤花可以吃,皮可以入药。紫藤花饼特别香,做起来也很方便。”
我从一连串小意外造成的无措中恢复了过来,客套着说:“东西是好东西,只是我没地方养。谢谢您的一片好意。”
老顽童忽然举起双手,围成一个门框的形式:“用紫藤搭架花门是极好的,到了四月,花穗会像瀑布一样垂挂下来。几千年,花穗都会像瀑布一样垂挂在您家门前。紫色的、花瓣组成的瀑布。”
他眼里露出孩子般的欢欣,等待着我的反应。我又被无措给捕获了,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他的双手便以门框的形式定格在那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的电影。在电影镜头里,此时或许该有紫藤花门的影像叠映:花穗像瀑布一样垂挂着的紫藤花门、几千年来花开花谢的紫藤花门、我从中年步入老年而后儿孙满堂的紫藤花门……
可惜现实不是电影,周围的人看着他,跟我一样错愕。
“那个,确实很美。”我轻咳了一声。
“你还别说,真养得好的话,确实很有观赏价值。”有一位同事凑了一句。不知是有感而发,还是为了帮我缓和气氛。
“我听说你跟李家辉老师是忘年交。”在哪里听说?听谁说?老顽童一概未加说明。就跟他对于如何得知有我这么个人、如何知道我在这里开会一样,毫无加以解释的意识。在我们正置身其中的那个县城,以及我生活过的所有其他县城,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交好,不管年龄差距多大,等待她的基本是数不清的流言蜚语。然而老顽童就这么在人来人往的大会场上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好像我跟李家辉老师交好是尽人皆知的事。事实上为了避免给我造成麻烦,李老师从不对人提及与我的关系。
我顶着即将被流言蜚语淹没的压力点了点头。
我的点头让他得到了某种激励,他两眼像按亮了的手电筒射出一道光:“我和李家辉老师的哥哥也是忘年交。”
那束光,又透露出孩子般的欢欣。我大致看明白了,“老顽童”的称呼,正是来源于他眼里时而流露的孩子般的神采。
“李家辉老师是文的,他哥哥是能文能武。九滚十八跌的滚子拳,我打一遍他就能记全了招式。我的武艺他是全都带到美国去了,只是这紫藤过不去。他小时候跟着我在山上伐木时,我们爷俩穿过一丛一丛的紫藤花海……”
老顽童越说越带劲,我却又涌起了看电影般的错觉。什么“能文能武”,什么“九滚十八跌的滚子拳”,什么“一丛一丛的紫藤花海”……这一切,不都是电影里才有的台词和镜头吗?
这位老人家,从言谈举止到思维模式,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这会场上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呢?会不会疑心我碰到了神经病?
我正担心老顽童还要继续讲,他却戛然而止了:“耽误您的事了。这两颗紫藤幼种,就拜托给您。”
我有些羞惭,老人家比我预设中识趣得多。
“有机会再去拜访您。”临别前,他对我作了个揖。
以作揖为礼,是我幼时在老辈人身上常见的,称不上稀奇,只是成年后再未得见,还是有些陌生。我涌起一种类似翻看老照片的温馨,在泛黄的记忆所营造出的氛围感里,合起双掌,也向他作了个揖。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欧阳娟的散文《紫藤为门》)

欧阳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杂志,已出版及发表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烟视媚行》《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天下药商》、散文集《千年药香——中国药都樟树纪事》,撰写纪录片《千年药都话樟树》。
来源:《芙蓉》
作者:欧阳娟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