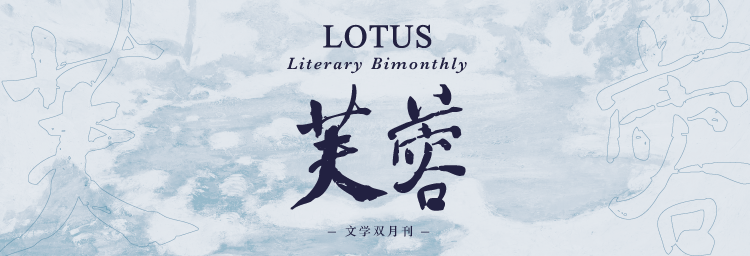

红头发姑奶奶的旅行见闻(中篇小说)
文/辽京
临行前,我把钥匙交给房东,托她帮我浇一浇阳台上的那些花,如果有空的话。没空,当然也没关系。我提着行李箱走到室外,一直提到能叫车的位置,天还未亮,不想让滑轮丁零的声音惊扰邻居。黎明是深蓝色的。
在火车上,我睡了一觉。上次坐火车,还是我父亲病重,我回家陪了他几天,送他到最后。在那以后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这次在火车上,我梦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背靠着一张世界地图,实际家里并没挂那样一张地图,它却在梦里出现,好像是我爸爸平常爱看的《新闻联播》的附注,这里战火、饥荒,那里山洪、海啸……从前,我回家看望父母,我爸爸就会说起电视上有什么新闻,哪里又打仗了,我想这跟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好久才回来一次,见了面,他就大谈世界形势,索马里、海地、巴以,还有什么,这些地名像桌子上的花生米,嘴里嚼着就不必说别的话了。
我装着在听,跟我妈妈一样。我妈妈去世后,我就很少回家,后来我爸爸也不在了,他们的房子也卖掉了,除了跟侄子一家偶尔联系,别的亲戚都断掉了。这次出来,打算先去北京看望他们,再去别的地方转转,趁着还没太老,人总是活一天少一天的。十几年前,我经历了一场大病,死亡在我头上拍了一拍,又站起来走掉了,像一个温和的陌生人。小时候我也遇见过他,在我爷爷家,乡下地方,一天午后,没人看管,我一个人悄悄来到池塘边,岸边是斜坡,下去两步,又下去两步,不知怎么就滑了下去,爬不上来,手也抓不住东西,眼前是浑浊的泥水和一点点太阳。按道理三岁的孩子还不记事,我偏偏记得那一回,一个人把我拉了上来,是我的叔叔,恰巧路过,我爸爸当兵出来了,离开了农村,我叔叔还在种地——如今他还在世,我应该去看望他,我的救命恩人。上次见到他还是我爸爸的葬礼,他对着遗体,深深鞠了一躬。
我水淋淋地坐在地上大哭,我大哥也来了,把我抱回家去,因此他挨了一顿骂。活到今天,死亡一共放过我两次,我想事不过三,下次就要来真的了。人到暮年就是有这些迷信,相信事情总有预兆,或者规律,藏在影影绰绰的命运之中。比如我特别留意偶然遇见的数字,比如火车的车次、座位编号、菜单上的价格,想着我的死日将与哪个数字相合。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星盘算命这些东西,相信人之有灵,可通天地,还交了学费,跟一位大师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在上班休息的间隙,给同事们算命。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几乎差不多,女儿何时能够出嫁,儿子何时能够娶亲,自己什么时候能当爷爷奶奶……大师教我的知识,朦朦胧胧,似是而非,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东西,他没有一对一地跟我解释过什么,当时我是在一个微信群里,付费进入,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奇怪呀,现在的年轻人,我年轻时不相信命运或者天意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由人造成的,好事好人,坏事坏人,因果脉络,清清楚楚。
总之我学到一些皮毛,足够作为消遣。正式退休前的最后几年,我在一间大学食堂干活,负责打扫和盛菜,也在那里解决自己的早饭和午饭。这对一个独身的人来说,再方便不过。除了我,同事们都有家庭,有孩子,很多都是一个地方来的,沾亲带故,是老板的远亲之类,只有我和一个厨师是看了招聘启事过来求职的,启事上写明包三餐住宿,实际上是两餐,住的是四人间。
“比学校的学生还强。”睡在我上铺的同事说,她叫金子,“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
过两天她又说起她在老家的房子,两层小楼,前后两个院子,不像城里,挤都挤死了。
当时,我跟前一个单位闹得很不愉快,拖欠的工资一直不发,我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把钱讨回来。我把这些事讲给金子听,金子说:“你真厉害,我可不敢打官司。”不过,大部分时候,我说着说着,她就睡着了,打起呼噜来,或者一边刷着手机,心不在焉,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她儿子要结婚了,等她再多存点钱,就要把老家的房子再翻盖一层,
金子管着清真炒菜的窗口,我在主食那边。晚上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肩并着肩,金子说她要给孙子攒学费,将来也上大学。她曾梦到,透过那些热气熏蒸的雾蒙蒙的窗口,已经看见了她那未谋面的孙子,看见她的孙子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背对着她。她想象不出脸孔,只能想象一个背影,那男孩从未转过脸来。她说那一定是个好兆头。
她得知儿媳妇怀孕的消息时,对我说:“你还不信,我的梦就是准的!”这一天她把每个学生的餐盘都堆得满满的,分享她的快乐,尽管那快乐中也有焦虑。早先跟儿子说好,一有孩子,她就要回去帮忙带,不能再打工了。我说好哇,反正这儿也累得慌,没几个钱,不如回去,让年轻人出去挣钱。
“到哪里都是累得慌。”金子说,“我在这里干,钱都存下来。他们出去打工,一年到头,存不下几个钱。”
“年轻人爱花钱。”“有了孩子要改改脾气呀。”
那年春节,金子邀请我跟她回老家,我没地方可去,就跟着她一起走了。南方乡下,阴冷如针,又十分热闹,前后两个院子,各种着一棵枇杷树,像伞盖一样撑开,遮挡冬天稀薄的阳光。家里人把早上的漱口水吐在树根底下。我住在一间又白又大又冷的房间,下午有一点阳光,偷偷摸摸,小耗子似的钻进来,在人脸上嗅嗅闻闻,一点温暖的活气。金子说:“这屋子将来给孩子住,你看这大窗户,亮堂堂的,写作业不费眼睛。”她儿媳妇说:“我们将来不在这边上学,学校太破了,好几个村凑一个班,老师也不行,冬天还烧土灶呢。”
金子听了,当面没说什么,私下对我说,他们想去县城买房,到县城上小学,意思是还要她出一笔钱,说买房越早越合适,她想的还是把老房子翻新加盖,已经吵过两次了。金子早年丧夫,一个人把儿子带大,在家里,一说什么事情,就爱把这些话挂在嘴上,“我一个人拉扯你长大不容易呀”,像一句听旧了的歌词,听得人都厌烦了。在老家的金子仿佛不是那个我认识的金子了。在食堂里,她手脚麻利,言谈爽快,大小事不爱计较,对着学生总是笑眯眯的,没见她有过愁苦的模样。“这些事,跟小时候干的农活比,差远了。”她总爱这么说。厨房闹老鼠,她用铁锹拍死过两只,将它们铲了出去。
在家里,她忙个不停,嘴里也说个不停,每拿起一样东西,就跟我讲这锅、这碗、这井、这树、这照片、这奖状的一切来龙去脉,她的父母、公婆,她死去的丈夫和女儿,活下来的儿子,拉拉杂杂的亲戚,好像一只蜘蛛在检点它织出来的复杂的网。她变得非常敏感,一直在品评别人或者咂摸别人对自己说过的话,忽然怒火升腾,低声地骂一句,又忽然忘掉,准备年夜饭的时候,我想给她帮忙,她一再地把我赶出去,嫌我妨碍她干活。
“你是客,什么也不用管,咱们就说说话。”于是我站在小厨房外湿冷的空气里听她滔滔不绝,腊鱼腊肉摆得满眼,狗在旁边觊觎。灶上的火很久没有熄灭,金子把她的前半生都讲给我听,全是苦的,好像在老家触景生情,想的都是不开心的往事,孤儿寡母怎么被人欺负,不过现在都好了,她喜欢加上一句,现在都好了,好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结尾总得是好的。
我更喜欢食堂里的金子,那个金子更熟悉、更亲近,更像我——真是自恋。我乘她不备,偷偷捡起一块腊肉,扔给旁边苦等的小狗,狗叼起肉就跑。一晃好几年了,这次出来,我打算再去看看金子,她的房子早盖好了,后来增建的那一层,外墙白得耀眼,金子抱着她的小孙女站在小楼前,对着镜头微笑。按计划先去北京,跟我侄子一家人见面,秋晨问我要不要住家里,他可以睡客厅,让我和米兰睡一张床,或米兰去睡米豆的上铺,下铺睡的是他的岳母,我说不用了,我还是回旅馆。秋晨已经有了这么多亲人,我对他的记忆还尽是他的小时候。“时间过得多快呀。”我说。
“二姑,你说话像个老太太了。”
我是一个老太太了,我知道衰老正像藤蔓一样慢慢缠上来。我妈活着的时候,总说寒从脚底生,衰老也是一样。我的膝盖不像从前那样听话灵便,它好像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而我,对抗衰老的办法就是,不向别人,尤其是晚辈去诉说,假装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饭后我跟米豆下了一会儿跳棋,她输了不会哭,秋晨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小时候被我父母惯坏了,下跳棋一定要赢。这套玻璃跳棋还是家里的旧东西,秋晨拿回来了,他是个念旧的孩子,卖老房子的时候,他还哭了一鼻子。人哭起来的神态,最像小时候。那样子,在秋晨的脸上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完全是一个中年人了。米豆赢了我两盘,输了三盘,她歪着头,鼻子皱起来,显露愁容。
“我的压岁钱啊,姑奶奶。”
我当然不会要侄孙女的压岁钱。棋盘上的彩色玻璃珠亮晶晶的,我给米豆表演了我的杂技,拿起三个珠子,轮番抛向空中,不间断地形成一个圆形,一个杂技动作,我跟小秦学的,他是我年轻时的对象,这种动作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一旦学会就再也不会忘记。
像爱一样。
米豆也要学,她爸爸当年就学不会,怎么也不行,讲解不行,示范不行,米豆几分钟就学会了,好像是潜藏的技能被发掘出来,被唤醒了,她嬉笑着抛起玻璃珠。我跟小秦也这样玩,赌谁的玻璃球先脱手落地,我赢了,学生胜过了老师。这次是米豆赢了,保住了她的压岁钱。
一个晚上像许多个晚上,跟家里人在一起的、长长的晚上,我几乎忘记了这种感觉。秋晨家里暖烘烘的,回到酒店那股暖意还在,我把外套脱下来,又脱掉毛衣,剩下一件长袖的内衣,腋窝下有一处凹陷,是手术留下的痕迹,跟我在术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仿佛是身体上长了个酒窝,配上刀口的痕迹,像半张狞笑的脸。动手术是快十年前的事情,我没告诉家里的任何人,这是一个秘密,像隐藏起来的刺青,仿佛它不是伤口,而是一种叛逆。拆掉缝线的第二天,我把头发染成了红色。
公司要求我染回去,理由是这个颜色影响顾客的观感,高档商场,员工不能奇形怪状,我不肯,他们就让我离职,我收集了证据,开始漫长的劳动仲裁。我想真实的原因并不是红头发,而是我得了癌症,他们想摆脱我。然而这世道不是他们几个人说了算的,打官司我也不怕。
最终我赢了,我拿到了应有的补偿,数额不小,我觉得世界偶尔还是公平的,如果不公平,到死亡跟前,也就一切公平了。死亡再一次放过了我。手术后的第二天,我就可以下床,第三天我躲着护士,到卫生间里抽烟,看着窗外一小片蓝天,我没有因病戒烟,尽管抽烟这件事在这个时代受一些人诟病,我还是保留了这个不健康的习惯。跟小秦分手后,我开始抽烟,我就喜欢把时间分割成一根烟的时间、一盏茶的时间、一顿饭的时间、一炷香的时间、一辈子的时间……我用了前半生去当一个听话的女儿,以为我爸会对我感到满意,然而他只会越来越不满意。从我父亲身上,我看出来了,听他的话如同以肉饲虎,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逼近,是没有尽头的。
为了小秦,我同他大吵一架,他颤抖着,最后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我想那才是我爸爸的真身。我说:“我大哥是解脱了,我也死了的好!”当时我大哥刚走几个月。从头到尾,我妈坐在一旁,一声不出。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她劝我别回嘴,别继续惹怒爸爸,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好,我对我妈说,他脾气好一点,少管点闲事,身体就能好了。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我们说好了要结婚,我去偷拿户口本,给我点时间,一定偷得出来。大概是从哪个电影里学来的,结局也像电影:他一个人离开了。唯一不像的是,他没留下只言片语——也好,至少没撒谎。
竟然被我爸说中了,说他是个没出息、没担当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小王八蛋。就因为说对了,我更加不能原谅他。到最后,我在他的病床边上,点上一根烟,不是平常抽的牌子,是我爸爸爱抽的那种,如果他有一丝清醒,就会懂我的意思,可惜他没有。一辈子结束了,恨和怨就跟着结束。秋晨坐在板凳上,头靠着墙,眯着眼睛。年轻人睡得多,到我这个年纪,深夜醒着并不难。
我爸爸去世那天,我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醒来天已经黑了,恍惚以为是黎明,隔着房门,我听见客厅有规律的嗒嗒嗒的声音,像极了一个人拄着拐杖走路,我听了一会儿,起床,拉开房门,那声音便消失了,客厅空荡荡的。接着我闻见烟味,是我中午时抽的,我打开灯,看见对面的窗户亮着灯,灯光一动不动。是晚上,不是早晨,不用起床,可以一直睡下去。那些灯光凝固着,如同雕刻。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辽京的中篇小说《红头发姑奶奶的旅行见闻》)

辽京,80后,北京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小说界》《花城》《钟山》《芙蓉》《山花》《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出版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长篇小说《晚婚》《白露春风》。
来源:《芙蓉》
作者:辽京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