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当代边塞诗的扛鼎之作
——读李立《黄河长调》之深度阐释
文/吕本怀
历时性阅读:文本重量与灵魂共振
2025年6月13日,厚重的《黄河长调》抵达案头,直至7月12日深夜,当最后一粒文字沉入心湖,这场历时整整一个月的阅读远征方告结束。这不是普通的翻阅,而是一场与21首长诗构建的“边塞精神长城”的持久对话。这部诗集以其独特的题材聚焦——囊括了长城雄关的千年风霜、黄河九曲的奔腾血脉、若尔盖草原的无垠牧歌、上海都市的现代边陲意象,更延伸至塔里木盆地的瀚海孤烟、可可西里的生命禁区、南海深处的蔚蓝疆域——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汉语诗歌地理空间。对我而言,除了长城、黄河、若尔盖草原、上海几处曾有缘踏访,其余辽阔疆域皆是地图上的遥想与文献中的符号。李立以诗行铺就轨道,以赤诚点燃引擎,牵引着我的精神列车,穿越时空的屏障,在文字的疆域里进行了一场弥补生命地理缺憾的壮阔巡礼。
尤为关键的是,李立绝非浮光掠影的观光客。其壮举背后,是出行前经年累月的案头深耕,是对历史卷帙、地理与民族志书、生态报告的深度咀嚼;更是旅途中身体力行的持续叩问,是与当地牧人、戍边战士、护林员、考古学者、普通百姓的促膝长谈。这使得他对每一处边塞之地的自然地理肌理、历史人文血脉、当代生存状态都具备了近乎“在地者”的深刻洞察。他以学识为精准的罗盘,以生命体验为燃烧的火把,引领读者穿透地理的抽象概念与历史的尘封记载,直抵土地的温度、风物的呼吸与人心跳动的真实节律。阅读《黄河长调》,绝非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深度置换与生命版图的剧烈扩张,其震撼与满足,足以抚平此生足迹未至的永恒遗憾。
千年回响:边塞诗史的辉煌、局限与当代困境
当我们谈论“边塞诗”,其艺术巅峰必然矗立于气象恢弘的大唐。高适的《燕歌行》以其“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尖锐对比,喷薄出雄浑磅礴的悲愤与穿透历史烟云的家国忧思;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则以“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奇崛想象,将西域的苦寒与壮美熔铸成惊心动魄的诗意画卷,其色彩之浓烈、意境之雄奇,堪称边塞诗美学的极致;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以简练如刀的语言,刻画出穿越时空的苍凉与征战的永恒悲剧,凝练中蕴含千钧;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在壮阔与孤寂的强烈张力中,升腾起一种豁达高远的宇宙意识;李颀的《古从军行》则弥漫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沉郁顿挫,将军士的苦闷与战争的残酷抒写得入木三分。他们共同以如椽巨笔,在烽燧狼烟、孤城冷月的背景布上,刻画出将士的豪情血泪、思乡的肝肠寸断与深沉的家国大义,其诗境如瀚海般无涯,情感如地火般奔涌,至今仍激荡着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灵。
然而,辉煌之下亦有历史的局限。唐代边塞诗,受限于时代审美与诗歌载体,多为精悍短章,纵使偶有《长恨歌》般的叙事长制,在纯粹的边塞书写领域,也罕有突破千言的鸿篇。在这方寸之间,雄浑壮阔的轮廓得以勾勒,历史烟云的宏大叙事得以点染,但那些构成边塞真实血肉的幽微细节、具体生命,却往往被宏大叙事所遮蔽。边塞独特风物的细腻纹路——如胡杨千年不倒的肌理、戈壁风蚀岩的奇异造型、雪莲在绝壁绽放的瞬间;戍卒边民日常的呼吸脉搏——他们脸上的沟壑、手上的老茧、口中的乡音、篝火旁的歌谣;历史褶皱中具体人物的悲欢离合——某个无名戍卒的家书、一场小型遭遇战的惨烈、一次胡汉贸易的生动场景——这些都难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充分展开。它们如同散落的珍珠,需要后人凭借无尽的想象去串联,依赖学者皓首穷经的钩沉去考证,方能拼凑出相对完整的图景。这不能不说是盛唐边塞诗留给后世的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审美留白与历史追问。
时间流转至现当代诗坛,边塞题材并未成为绝响,但真正能接续盛唐风骨、与之在精神气度与艺术高度上比肩而立者,却如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其一在于体裁的自我设限:创作多囿于精巧的短章小制或结构松散的组诗形式,缺乏驾驭宏阔长诗、构建史诗性框架的雄心与笔力;其二在于视野的局促:地理关注点常被束缚于诗人工作生活的狭小半径,如某个特定的兵团农场、一段熟悉的边境线、一个长期生活的边疆小城,罕有将整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中国边疆全域,系统地、有机地纳入诗性观照版图的宏愿;其三在于体验的浮泛:偶有诗人于旅途中捕捉边塞光影,然行程往往仓促如旋风,所见所感难免沦为车窗外的惊鸿一瞥。这类作品,或许有瞬间的灵动与意象的新颖,却普遍缺乏历史的千钧重量、对生存本质的深层叩问,以及与大地的血脉交融感。其情感根基,常显悬浮与轻飘,难以承受“边塞”二字所蕴含的沧桑与厚重。
《黄河长调》:破壁而出的史诗壮举与生命淬炼
正是在这历史回响微弱、当代创作乏力的背景下,李立《黄河长调》的横空出世,具有石破天惊般的破壁意义。这部诗集以其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厚度(逾三百页),以21首皆为长诗体裁、皆聚焦边塞题材的纯粹性与规模性,在现代汉语诗歌史上矗立起一座醒目的孤峰。诗人为何选择如此艰难而宏大的书写?又是在何种惊心动魄的生命境遇下完成了这浩大的精神工程?答案不在抽象的理论阐释中,而是深藏于诗集中那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里。这篇后记,其情感的烈度、生命的质感与精神的纯度,远超当下无数徒具分行形式却灵魂空洞的所谓“诗歌”,它本身就是一首以滚烫的生命为墨、以广袤的大地为纸、以生死考验为笔锋写就的壮烈史诗,其震撼力足以让许多精致的诗艺黯然失色。
诗人以朴质而饱含力量的文字,袒露其决绝的心路历程:
“2021年初,北国冰雪尚未消融,南方依旧寒气峥嵘,在命运的沉沉浮浮之中,我突然萌生出挑战生命极限的念头。挥之不去,日甚一日。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信念如一面开路旗帜,在远处猎猎作响。于是乎就忍痛辞别摸爬滚打二十余载的高薪职场,毅然决然。汕头是祖先下南洋闯荡谋生的始发地,选择在此启程,是祈望得到祖先在天之灵的加持,八千里路云和月,始终照耀我脚下的未知。”(《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绝非一次浪漫的采风之旅或舒适的文化考察,而是一场置于全球新冠疫情阴霾笼罩下的、充满未知与凶险的孤勇长征。2021年3月至12月,在世人普遍收缩活动范围、寻求安全的时刻,李立却做出了逆流而上的选择:辞去令人艳羡的高薪职位,单人单车,启动环行中国大陆边境线的旷世壮游。其车轮碾过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袤土地,行程累计超过十二万里。这十多万里路,是风餐露宿、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生存挑战;是披星戴月、与时间赛跑、同疲惫抗争的意志极限跋涉;更是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生命禁区边缘行走的惊魂历险。无论是陷车于无人区的绝望,还是穿越怒江99道拐时头顶随时可能坠落的飞石,抑或是高原反应带来的窒息感,每一次危机都是对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淬炼。如此以血肉之躯丈量国境线、以生命为赌注换取诗性真知的壮举,将其置于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诗歌史册中进行观照,亦属绝对的凤毛麟角,称之为诗人中的“大熊猫”已显不足,实乃独一无二的生命诗学实践。
后记中那些铭刻着生死印记的瞬间,是理解《黄河长调》精神内核的钥匙:
绝境中的“哈达救援”: 陷车于茫茫荒野,孤立无援,“在求助几辆过路车无果的情况下,一辆挂藏A牌的越野车主动停靠在路边……因为没有专业的汽车救援牵引绳,用哈达和就地捡拾的钢丝绳拖拽了三次都以失败告终……正当万念俱灰时,另一辆挂藏A的越野车主动停了下来……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终于把陷在沙坑里的车拉回到正道……两个藏族小伙子连名字都不愿意如实相告,只留下一句‘在219国道总会遇到好人’……在生命禁区,此话不亚于隽永的诗句,足够留白,令人回味无穷,温暖无限。”(《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哈达牵引绳”与“219国道箴言”,已升华为超越民族、直抵人性光辉的精神图腾,它让荒原的冷酷瞬间被人类互助的温暖所融化,成为诗集情感基座中最坚实的部分。
知行合一的诗学:以生命践履铸就诗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箴言早已道破真知的源泉在于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反观当下诗坛,诸多作品之所以遭遇读者的疏离甚至冷眼,其症结往往在于书写的悬浮与生命的缺席。那些被反复摹写的“乡土”,永远定格在袅袅炊烟、阡陌鱼虾、老牛哞叫的陈旧图景里,乡民被简化为淳朴谦让的符号化存在。当读者深知现实的乡村正经历着空心化、老龄化、生态与伦理的双重困境,此种虚饰的田园牧歌,除了制造认知的隔膜与虚假的审美,何来直击人心的力量?城市书写同样陷入困局。诗人若不肯俯身进入沸腾的、充满烟火气的现代性漩涡——去感受建筑工地钢筋水泥的冰冷与汗水的滚烫,去体会外卖骑手在算法驱策下的争分夺秒与疲惫不堪——笔下缺失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尤其缺失了构成城市基石的芸芸众生,其文字必然沦为空洞的能指游戏,苍白、冰冷、悬浮于现实的真空之上。
李立及其《黄河长调》的弥足珍贵,在于他以近乎决绝的生命实践,为“知行合一”的诗学理念写下了滚烫的、不可复制的注脚。只为心中那个执着的念头——“挑战生命极限”“追寻诗与远方”——世俗的功名利禄、安逸的职业轨道皆可抛却。这场“说走就走”的壮行,其动机纯粹得令人动容:不为博取发表虚名,不为换取稿费薄利,更非完成任何机构或个人的命题作文。这是灵魂深处自我觉醒后的神圣使命,是生命个体向广袤时空主动发出的探寻信号,是内心升起的、指引前路的信念旗帜。其创作过程与旅程本身已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诗路一体”模式:车轮所向,即目光所及、心灵所感、诗笔所至。他力求在风尘仆仆的第一现场,在肾上腺素尚未消退、心灵震颤最为强烈的时刻,以文字“抢拍”下最新鲜的悸动,同步沉淀最深切的思索。因此,《黄河长调》中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跋涉的咸涩汗水,甚至隐约闪烁着高原烈日灼伤的印记与遭遇险境时渗出的血色;每一行诗句,都是他脉搏的强劲共振,心跳的轰鸣在纸页间的真实回响!这是一部用脚步丈量、用汗水浇灌、用勇气开拓、用生命担保的诗集,其份量源于其不可替代的亲历性与身体性。
多维诗境的交响:地理、历史、人文、自然的深度织锦
打开《黄河长调》,便开启了一场穿越浩瀚时空、融通天地万物的多维精神远征。李立以其宏阔的视野、深沉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边塞诗学宇宙:
山河地理的史诗性呈现:诗人如同一位掌握广角与微距双重镜头的语言导演。《塔里木盆地》以粗粝的笔触勾勒“死亡之海”的洪荒伟力与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图腾;《可可西里》则聚焦“生命禁区”中藏羚羊精灵般地跃动与巡护队员如雕塑般守护的身影,奏响一曲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生态悲歌;《雪山赋》以冰峰雪线的冷冽光芒,映照出自然的永恒与人类的渺小;《青色的海》(青海湖)在碧波与鸟岛的协奏中,展现高原明珠的静谧与丰饶;《大戈壁》让读者置身于风蚀城堡的迷阵,聆听砾石在风中滚动的亘古回响;《谒莫高窟》则穿越壁画与彩塑的千年光晕,复活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辉煌记忆;《河西走廊》宛如一条历史的通道,回荡着金戈铁马与商旅驼铃的交响;《昆仑山》更被赋予“万山之祖”的神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源头的象征。这些篇章共同铺展出大西北摄人心魄的空间辽阔感、时间纵深感和自然原始力。而《伊犁河谷》的塞外江南风情,《若尔盖草原》的湿地牧歌画卷,《东北大平原》的黑土粮仓气象,则挥洒出迥异的笔墨,尽显祖国边疆的丰饶柔美、蓬勃生机与多元禀赋,使教科书上抽象的“地大物博”概念,化为了可触、可感、可呼吸的生命沃土。《黄河长调》本身作为核心乐章,以黄河从源头细流到入海狂澜的跌宕历程,象征民族精神的奔涌不息;《南海蓝》则以深邃无垠的蔚蓝,拓展了“边塞”的海洋维度。黄与蓝的交响,不仅昭示着国土的辽阔多元与色彩交响,更无声诉说着先民筚路蓝缕、胼手胝足、一寸山河一寸血开疆拓土的万古艰辛与不朽功勋。
历史脉动的深度聆听与当代回响:李立的笔触具有贯通古今的穿透力。《赞诗》作为开篇的宏大序曲,其首节即展露其全球性的人文视野与宇宙性的悲悯情怀——他将对祖国的礼赞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宏大坐标之中,彻底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独吟。这份礼赞属于地球母亲,属于全体生灵。他心中的祖国,绝非抽象的政治符号或冰冷的地理轮廓,而是具象为戈壁滩上一株倔强的骆驼刺、雪线上绽放的一朵雪莲、高原天空中一只孤独盘旋的鹰隼、牧民帐篷前一只警惕的藏獒、界碑上一道风雨侵蚀的刻痕,尤其是途中邂逅的每一张被风霜雕刻的面孔——哈萨克牧马人黝黑的笑容、东北林场老工人讲述伐木史时浑浊的泪眼、南海老渔民掌舵时青筋毕露的手——以及史册中那些曾照亮黑暗的名字:张骞、班超、左宗棠……直至《可可西里》中那位以血肉之躯阻挡盗猎者枪口的英雄索南达杰。李立赋予书写的每一个生命(无论人、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的山川)以跌宕的命运故事——这故事可能是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如昆仑西王母),可能是尘封青史的传奇(如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悲欢),可能是几十年前惊心动魄的壮烈史诗(如筑路官兵的牺牲、垦荒者的奋斗),更多则是他此时此刻亲历、亲闻、亲证的鲜活现场。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这片土地及其子民(包括所有生灵)深入骨髓的挚爱、感同身受的悲悯与发自肺腑的景仰。正是这种深沉博大的情感,构成了支撑我们民族穿越无数惊涛骇浪、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最核心精神动力。
风土人情的生命温度与文明对话:《黄河长调》堪称一部流动的、充满呼吸感的中华边疆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塔里木盆地》的章节,不仅呈现了塔克拉玛干的浩瀚与胡杨的悲壮,更深入挖掘了绿洲居民(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迥异于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文化与原始萨满信仰的交融)、节庆歌舞(麦西来甫的狂欢)、手工艺传承(艾德莱斯绸的绚丽)及其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坚守与嬗变。那些基于严酷环境而形成的、可能被外人视为“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极端干旱区的坎儿井灌溉系统),其内在的生存韧性、对自然的敬畏以及独特的快乐哲学,都促使我们反思关于生命本质的单一答案,领悟文明形态的多元之美。后记及诗中反复咏叹的那句“在219国道总会遇到好人”,以及藏族青年用哈达拖车、施援不留名的事迹,正是边疆大地淳朴民风、人性本善未被现代性洪流完全吞噬的最温暖、最有力的证词。这些具体而微的相遇,比任何宏大的民族理论都更能诠释不同族群间最质朴的善意、最本真的互助以及超越语言文化隔阂的理解可能。《东北大平原》中鄂伦春老猎人对山林消失的叹息,《南海蓝》中疍民“水上吉普赛”生活方式的变迁,都在诉说着现代化进程中边缘族群的文化阵痛与适应韧性。
自然万物的生命礼赞与生态哲思:李立的诗行是一座珍稀动植物的基因宝库与地理地貌的微型百科全书。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会不断遭遇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顽强生命: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藏野驴如何在稀薄空气中疾驰;羌塘的雪豹如何成为雪山之王;红树林滩涂的招潮蟹如何演绎自然的韵律;天山雪线附近的雪莲如何绽放生命的奇迹……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酷寒、极旱、缺氧、盐碱、强辐射)中,以令人惊叹的进化智慧与生存韧性,完成着生命的传承与演化。诗集对地理奇观的呈现更是气象万千:李立并非单纯的科学记录者,他在描绘这些生命与地貌时,始终贯穿着深刻的生态意识与生命平等观。无论是《可可西里》对盗猎罪行的控诉与对索南达杰的礼赞,还是对荒漠化、冰川退缩、海洋污染等现象的忧虑笔触,都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沉思考: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唯有敬畏、共生,方能守护这瑰丽而脆弱的星球家园。这些壮丽的自然拼图,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不可或缺、不可复制的生命共同体,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生命庄严最有力的礼赞。
诗艺的根基:千钧之重与赤子之诚
《黄河长调》这部体量庞大、意蕴深重的诗集,能让我在三十个昼夜中保持高度的专注,逐字逐句地精读、啃读,甚至掩卷长思,其根本魅力与强大吸附力,源于诗句内在的千钧历史重量、磅礴山河气韵以及如岩浆喷发般不可遏制的生命真挚。李立的每一个字,都源自车轮碾压过、双脚丈量过的真实土地,带着泥土、砂砾、冰雪、盐霜的质感;每一句诗,都经过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缺氧眩晕的肉体淬炼,以及面对壮美时的灵魂震颤、目睹苦难时的锥心之痛、邂逅善意时的热泪盈眶等复杂情感的深度发酵。这不是书斋中凭借想象力和修辞术编织出的轻飘呓语,而是无数次在旷野中凝神屏息的仰望、无数次在遗址前灵魂出窍般的沉思、无数次因自然伟力或人性光辉而引发的浑身战栗、无数次在篝火旁或帐篷内聆听故事时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后的结晶。唯有当个体的灵魂被存在的真实本身狠狠撞击,当心灵被山河的壮阔无垠与人性中至善至勇的光辉深深灼伤,灵感才会如压抑的地火奔涌而出,诗意才能如积蓄已久的江河冲破堤坝,一泻千里。那份落笔时充盈于胸的对山河的挚爱、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与对普通人的深切景仰,力透纸背,汹涌澎湃,足以唤醒任何一颗被现代生活麻痹的心灵,引领读者重返存在的本源与生命的庄严。
扛鼎之誉:《黄河长调》的诗史定位与不朽价值
综上所述,《黄河长调》的出现,以其史诗般的宏大规模(21首长诗构成有机整体)、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十二万里生死跋涉的亲历性)、深邃的历史洞察(贯通古今的时空视野)、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普世关怀(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多元文明与自然生态的深刻观照,以及驾驭长诗体裁的成熟技艺,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当代边塞诗歌领域当仁不让的扛鼎之作。它成功地突破了唐代边塞短章在细节与深度上的历史局限,极大地弥补了现当代边塞诗歌在规模、视野、体验与精神重量上的普遍匮乏。这部诗集是李立个人生命能量与艺术才华的一次火山式喷发与里程碑式的结晶,其意义远超个人创作范畴。
它更填补了当代汉语诗歌一个重要题材领域的深度空白与精神高地。在充斥着个人化絮语、都市小感伤、语言游戏和解构狂欢的当代诗坛,《黄河长调》如一股来自高原的强劲罡风,以其沉雄博大的气象、扎根大地的品格、敬畏生命的伦理和直面存在的勇气,重铸了诗歌的重量、尊严与担当。它雄辩地证明:真正的诗篇,永远诞生于行走的脚步之下、滚烫的生命体验之中、与大地的深度对话之间、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关切之上。这部用生命书写的边塞史诗,必将在中国诗歌的璀璨星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独特的、耀眼的光痕。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已经完成的书写,更在于其昭示的方向——诗歌重返生活现场、重返历史纵深、重返精神高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长调》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面旗帜,一种召唤,它激励着后来者以更虔敬的姿态,走向大地,走向历史,走向生命本身,去追寻那永不枯竭的诗意源泉。


吕本怀,60后,笔名清江暮雪,湖南省华容县人,分行为录世,读诗以自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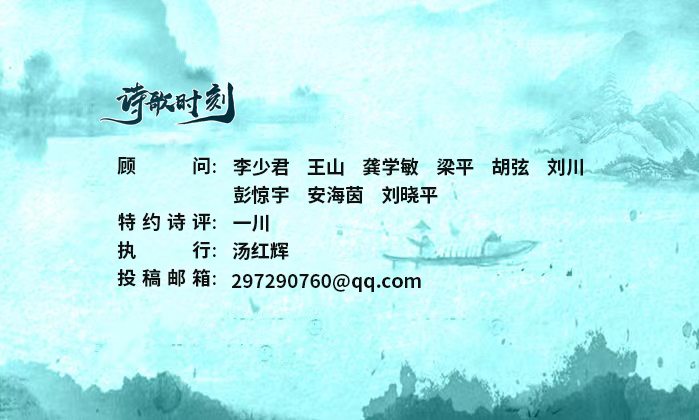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吕本怀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