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自由诗:种在近体诗与现代诗之间的“杂交稻”
文/李盛
先虚拟一个前提:
一一假设,百多年前,先贤们取法欧美诗,不只是横向移植彼自由之形式,且横向移植彼独擅音美之本质,它会不会成长为又一株号称国宝的“杂交稻”?
于当今,文本形式散文化,与声韵失序的烦恼,把我们与读者的距离拉开,再拉开,形同挽不住的流水;当我们于惴惴不安中,诘问自己,又自相矛盾地安慰自己一一于汉语近体诗与现代诗之间,左右踌躇。我们是否该下定决心,修正文本,以缩短拉开的距离;还魂音色,以继续开拓自由诗的新境界。
于文本认识论,若放任形式,疯长的可能是形式,若过滤音美,余下的可能是聒噪。这与发生在身边形形色色的所谓艺术创新何其相似。
于创作追求论,现代诗仍汲汲于争取读者认可。如一枚抱蛹化蝶的茧子,我们除了欣赏茧子足够耐看的外观,更欣羡茧子足够深厚的内涵。
兀兀如恒者,要把它编织得天衣无缝,飞动得绚烂无比;如涅槃之美。
不假思索,你的现代自由诗,在你的作业田里,已由字词句读组合而成了,甚至搭上AI的快车,嗒嗒的键盘音有如韵律。但是否如读者所愿,从茁芽长成结穗,形神丰满,既耐看更耐咀嚼:譬如外在有形,如字词句,生音色彩;内在有容,如思想(感受或认识),情感浓缩,善于传递,且合乎逻辑;甚至还会权衡一下,如在场一语境一意义一主题的构成,能更好地将认识与发现、惊喜、希望,传递出去?!
诗嘛,是感情浓度最烈,修辞程度最高的文类。诗人又是天生的主观主义者,这种主观认识与主观体会,往往包裹一层又一层情感的外衣;包裹你对客观事物认识与体会,愈彻底愈深刻,表达的情绪和欲望愈强烈,也愈感人。
无疑,在这些节点上,古近体诗还是现代自由诗,其创作指向并无差别。于客观上,它构成诗的形象;于主观上,它裸露你的灵魂一一真实、纯洁、永恒。
说自由诗之挠人,或者说它的妙处,在于每一次创作是一次创新。说难者亦难,易者亦易。但为人称许的新文本,每读来句式上口,结体自然浑成,情感充沛,有起伏的声调,声声抵达心坎。
言及声韵,遂想起《楞严经》里那个有趣的故事。
佛问:“汝等菩萨及阿罗汉……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定地观地禅地,即认识自己认识万物,观照的方法)?”惟陈那五比丘即白佛言:“于佛音声,悟明四谛(苦集灭道,即认识痛苦解除痛苦的方法)。”又言:“我于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
夫音声尚可以抵达佛性,唤醒觉悟。现代诗人之言诗,理在当然。如此推断,彼西人之诗美,亦不亚于佛之音声么?!
故,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故,诗为心声,不可不慎。
如前述,汉文字之美,不止于象形寓意有声,兼具可塑之性,简约之美。其可塑与简约的本质,更是构成诗语言的秘方。可与现代提纯的稀土元素类比。
偿有人谓某诗某句之妙,不可增减移易一字,真是千锤百炼中得来。
然,自由乃自由诗之灵魂。就其生存生长发展来说,发现与一枝蒲公英飞动的体验相仿佛。它有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得而知。但飞起来,飘然那一刻,与落地那一刻,那种感觉,是典型的自由体验。
当一粒种子有自由飞行渴望的时候,相信它就一定会飞;当诗有自由飞行渴望的时候,它会招手我们一起去体验,去扩充认知和幻想。这似乎是生活当然,是现实使然,是规律必然;亦是戏剧性偶然,寓言式释然。
文学这门功课,经专家学者分门别类,很是具体。譬如农家园子,有五谷杂粮,瓜果豆茄之属。它们各具形态,各有品味,生息各有风格,酸甜苦辣各有特性,甚至用途。
殊不知,诗另有别称,还有坛子圈子,分大众小众,分学院、草根、第n代……不追问现代汉语诗生成的“父本”与“母本”。
泛观诗之为体,即以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文本推导,诗大致以“纪事为劣,说理或可,亦难当行”。即是说,冗长的叙事,一逗三百句,是为低等级的写作,只满足于事件的再版,或者新闻式,说明书式的叙述。于自由诗,是更大的沦陷。
诗固有定格,是偏重于抒情的语体;诗善于跳跃,所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长于写意,与写实的散文缓步或快步行走的叙事迥然有别。当然,理性与逻辑是必要的;抒情滥觞,亦是必予节制的。
可大多数时候,往往因为一堆情绪(或者灵感),总是交织冲动着,散乱且迷茫,找不到安放的地方。除了反复折磨,还缠着你不放,这时有关主题的选择与确定就十分重要了。梳理或沉淀一下自己,所要传递出去的是什么?情感的目的地指向何处?把主题找准,把它拧出来,便十分重要了。譬如战术上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此,属于它的意义也就十分重大了。
写作的自由性何其广大,正应了那句口头禅语:道在“日常用间”,可你偏说道在“屎溺”。的确够直观够实在,却不怎么够雅观。若被之管弦,让人张口唱来,总觉得别扭。可以出自你之口么?
释手为有先锋思想的诗句鼓掌;释手为结构零乱,气韵隔断的文本而惋惜。但终究,那被我们发现的闪光点,成行的好句(或金句),经再三锻炼,也是可以写成一首好诗的。
可恨者,支离破碎的语言,矻矻磕磕的语言,被捧为先锋。
不幸的是,有人异口同声加以赞叹!甚至追捧。还真有大堆趸足,甚至豢养者。
譬如麂子这个物种,俗称四不像,说重组出优势,可不可以得个高评分?至今令人怀疑,好处在有个比较,多一个物种不是坏事。
据说,自然界中每天发生这样的生息死亡,人类似乎没有恐惧,但自然就有,而且很自觉。这么想,脑筋短路也就通了。
蔡元培先生教诲: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不知善恶,谈何道德。道德沦丧,何以为人?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诗教史,是美学审美学史,贯穿几千年。比照一下,在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有那么多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诗人。即是至暗的时刻,有他们存在,人间尚有一丝温暖,或者希望。
缘何每翻阅书案上的那些经典读本,原本惶惑的心突然又安静下来?原来诗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经历隐藏在作品里。
好的作品有如精金美玉,哪怕是一个穷诗人,咀嚼再三,也会觉得自己是很富有的人。
捋一捋我们的创作,较为成功的作品里,确是有个自己在,有时显而易见,有时须品嚼才能发现,在读者读来,亦有感同身受,能体会到真情实见的认知。
原来把自己隐藏在诗里,是诗意栖居之一种。譬如人海茫茫,我们如何安顿此身?如何学习做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人,学会怎样观察认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
知世而人情练达,且这等练达之意,恰到好处。这便是生活的诗意与诗意的生活,亦是生活最美的部分,亦是汉语言文学最美的部分。
2025年8月18日,9月9日改定于熙园。


李盛,男,湖南平江人。湖南省作协会员,曾在国家省部级报、刊及市级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多次获奖;另有小部分作品译介国外。著有诗集《劳动者札记》等2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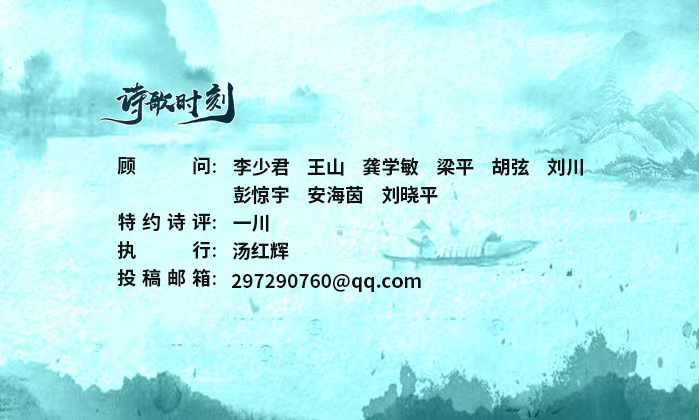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李盛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