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裤线(组诗)
◎哥哥打来电话
哥哥打来电话,我在贵州的云霭里倾听
音质里慢慢洇开滏阳河的水纹
“清明祭扫”这四个字像一支火把
三十年前的光,似乎正在
14.7平方米的蜗居里巡夜
哥哥在诉说——
父亲叠裤子的手势像折叠纸船
床单下藏着起讫点和经停点
规范的航线
裤线笔直得如他未弯的脊梁
在一间屋子半拉炕的暗影里
撑起五个晃动的碗盏
左手在病历本上开花时
拐杖正沿着晨雾练习正步
衡水的酒量缩成牛眼酒盅
二钱烈度,在血管里
趟出三十年未结冰的河
告诉哥哥——
这么多年我不吃海带和大蒜的秘密:
父亲曾说海带能缠住血压计的水银柱
大蒜在瓷碟里会举起杀菌的火把
而父亲所信赖的它们
把他留在1995年末的门槛上
把拐杖戳成望乡的碑
母亲93岁了,开始在时光里
迷路。她的斗志还在,还在
与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作
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母亲却记不得
那个把裤线叠进岁月的人
如何用光头照亮过
我们够不到的天空
此刻高原的风正通过哥哥
穿过父亲的平原
哥哥没有多余的话语,好像我俩
天各一方都在想起父亲左手写的字
是写在时光背面的
未拆封的星光

◎滏阳河在母亲瞳孔断流
上次去看望母亲时,天空的云坠成铅块
那十四平方米的老宅总在眼前摇晃
床单一厂的光头男人正用碎布头
缝合五个饥饿的洞
他总把黎明叠成直角
让华北平原的褶皱在炕沿平展
左手的笔迹洇开
病躯里游出滏阳河的支流
牛眼酒盅盛着微缩海潮
咸腥漫过1995年的门槛
海带和大蒜在记忆里发芽出三十个春天
我无法吞咽
93岁的母亲把往事砌成新堤坝
在母亲舒展的皱纹里
父亲正随碎布沉向河底
唯有父亲那笔直的裤线
在高原的雨平原的雾中
笔直生长
刺破所有向下的重
◎滏阳河的支流在高原奔涌
高原的风是倾斜的秤杆
吊起三十年光阴。摇晃着
十四平方米的蜗居正从西北角浮起
父亲的光头在泛黄的床单下闪动
像永丰楼未熄灭的灯盏
他总在凌晨三点翻身
把华北平原的褶皱压平
床单厂残留的碎布头
裹着五张饥饿的嘴
吞咽海带、大蒜和左手临摹的余生
牛眼酒盅里
滏阳河泛起微醺的涟漪
拐杖叩击楼梯的韵脚
比衡水老白干更固执
二十年病躯竟走出千里堤坝
如今母亲眼里的河流已改道
唯有我们仍记得
那些被压出棱角的清晨
在贵州潮湿的雾气里
重新长出笔直的裤线
◎床单褶皱里的华北平原
坐在高原33层的平台等雨。等老天的心酸
在华北平原大姐、大哥、二姐的
掌心返潮
那个把裤线压成田埂的男人
他的二钱月光让我们吞下
三十个未成熟的春天
每年祭扫父亲时,姐弟四人
总把旧相框擦成迷雾
姐弟各自的厨房里
蒜瓣正一粒粒褪去外衣
像褪去所有关于光的证词
唯有那笔直的清晨依然生长
在高原的褶皱里
刺破所有向下的引力
◎病历本上的平原
在贵州的坡地上,父亲的平原正在缩小
像他当年塞进裤腰的滏阳河,皱成
14.7平方米的版图是折叠的船
他叠裤子的手势,比水银柱更宁静
床单下藏着永不弯曲的标尺
笔挺的裤线,是拉直的井绳
垂向五个等水的瓦罐
光头在旧镜子里生了锈
却始终是未剪的灯芯,照亮
母亲数粮票的指节,照亮
哥哥和姐姐课本上洇开的墨水渍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病历本
把他的右手钉成标本
左手才从故乡的墨水瓶里
游出,在纸上写下秀气的反字
像一群逆水的鱼
◎单向的铁扶手
一楼的铁扶手在左边,二楼也是
左扶手只通向二楼
三楼到六楼的扶手还是单向的
是公共设施,冲右
单向的铁扶手是哥哥当年带着
工厂同事利用节假日
用废料焊接的
单向的铁扶手每天被父亲
攥拽着放牧日出和日落
如今,楼里的街坊在替父亲
扶着或攥着单向的铁扶手
回家
楼上楼下的街坊们都知道
单向的铁扶手是永丰楼的
——界碑
(2025年4月3日于贵州六盘水水城古镇)


罗广才,1969年出生,祖籍河北衡水,常居京、津、黔三地。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诗歌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天津诗人》读本编辑部总编辑、京津冀诗歌联盟副主席、天津市朗诵艺术协会副会长。作品散见于《诗选刊》《诗刊》《星星》《大家》《作品》《特区文学》《草原》《北京文学》《都市》《诗林》《诗潮》《诗歌月刊》《绿风》《延河》《鸭绿江》《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和500余种选本和文摘报刊。诗歌《为父亲烧纸》《纪念》等作品广为流传,著有诗集《罗广才诗选》等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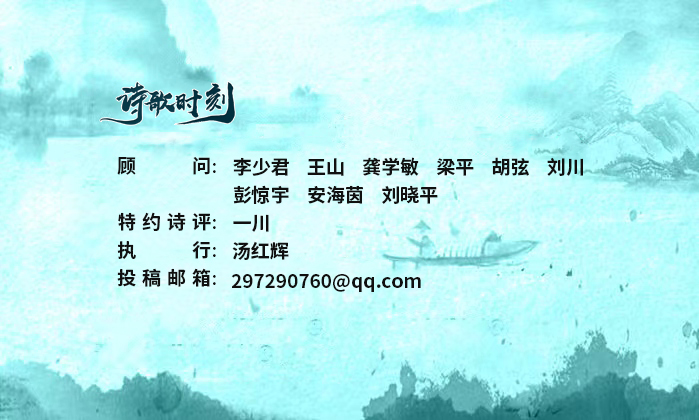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罗广才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