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理尽头与精神源头之间
——李立《南极洲诗抄》的行吟诗学初探
文/吕本怀
行吟的终极场域:南极作为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极地
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李立从未停下过脚步,也从未禁锢过思想,这一次他踏上了南极洲。至此,李立的行吟足迹与诗意遍及南极、北极和高极(第三极——青藏高原)等全球七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行吟”始终承载着士人精神漫游与文化寻根的厚重意蕴。从屈子泽畔行吟的孤愤,到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放达,再到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旷达,行走与吟咏构成了中国文人认知世界、安顿自我的基本方式。李立承续了这一古老传统,却将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他的行吟不再是山水田园间的闲适漫步,而是朝向文明边缘、地理尽头的极限穿越。《南极洲诗抄》正是这一极限书写的巅峰之作,它标志着中国行吟诗歌从“山水审美”到“生态伦理”、从“自我抒情”到“人类忏悔”的深刻转型。
南极在这组诗中具有三重象征意义:首先,它是地理的终极——地球上最后一块未被完全人类化的大陆;其次,它是生态的镜像——映照出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所有病征;最后,它是精神的净土——在一切喧嚣之外的寂静之所,人得以直面最本真的自我。李立的南极行吟,本质上是一次朝向源头的回溯之旅:既是在地理上向地球末端的行进,也是在精神上对文明病症源头的追溯,更是诗学上向抒情本质的回归。
忏悔诗学的建立:从自然书写到伦理自觉
《南极洲诗抄》最震撼的突破,在于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忏悔诗学”。在中国古典山水诗中,诗人多作为观察者、欣赏者乃至占有者出现,生态往往只是情感的投射对象或人格的象征载体。但李立彻底颠倒了这一关系——在《鲸的控诉》中,诗人放手让自然主体直接发声,人类反而成为被审判的对象:
“蓝海和冰山,这里原本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祖辈在南极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自从被人类发现,几乎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此处采用的鲸鱼第一人称叙事,并非简单的拟人手法,而是一种深刻的伦理立场转换。诗人充分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从而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暴力逻辑。当鲸鱼控诉“爆炸鱼叉技术/让我们五内俱焚”时,那些被技术进步光环所掩盖的残酷真相被赤裸裸地揭开;更尖锐的是第三段对“人类虚伪”的揭露——在“有识之士”呼吁保护的背景下,“有人假科研之名/继续为非作歹”,这种对“合法化暴力”的批判,使诗歌获得了政治生态学的批判锋芒。
忏悔意识的彻底性更体现在《南极,请接受我的忏悔》中。诗人不仅代表抽象的人类忏悔,更将自己也具体地纳入到了罪责共同体:
“我请求企鹅原谅,是人类的征服和占有作祟
打扰了你们平静的生活,我们的脚印试图
篡改你们赶海回家的路,枉顾了宝宝们的饥饿”
“我们的脚印”这个意象极富张力——脚印本是行吟者存在的证明,在此却成为了侵略的罪证。诗人意识到,哪怕是最善意的接近,也可能构成对自然秩序的扰动。这种对“人类行为本身即可能构成侵犯”的觉悟,达到了生态伦理的深层境界。而“我为人类的残忍与贪婪,感到痛彻肺腑的追悔”中的“痛彻肺腑”,显然不是矫饰的情感夸张,而是良知在见证巨大创伤后的真实生理反应。
动物意象的精神转喻:漂泊者、受难者与启示者
李立对南极动物的书写,超越了传统的咏物诗范式,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精神象征体系。“漂泊信天翁”成为行吟诗人的完美转喻:它们“从不成群结队,一生选择孤独和漂泊”,这几乎是古往今来所有思想者的命运写照。“生命的密码,无须解锁尘嚣”,则道出了精神独立的核心真谛——真正的生命意义从不需要在喧嚣里认证,它自有其内在的节律与逻辑。信天翁“一生都在追逐自由,一生都在删除风浪”的双重运动,恰是精神生活的本质:既积极追寻,又不断净化。
鲸鱼则承载着受难者与启示者的双重角色。在《鲸的控诉》中,它们是工业化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但在《我的头发被南极的阳光大肆渲染》中,诗人看到“鲸鱼受过多么巨大的委屈,不也挺了过来/早上,我还看见鲸鱼自由自在地嬉水/开始了新生活,早已不计前嫌”。这种从创伤到新生的叙事,赋予鲸鱼以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它们不仅是苦难的象征,更是生命韧性的见证,而鲸鱼的“不计前嫌”与人类的耿耿于怀形成鲜明对照,暗示了自然相较于人类的某种精神优越性,以及自然相比于人类所具有的更强的修复力。
企鹅的意象处理最为精妙,在《亲爱的企鹅》中,凸显出了一种“克制的爱”的美学:
“亲,远远地望着你,是你给予我的荣耀
驻足徘徊,请宽恕我支用这份窘迫的矜持”
这种爱不是占有的,而是守望的;不是侵入的,而是尊重的。于我看来,在这其中仿佛也有着诗人初恋时的影子。“你的呢喃就是我无可救药的药”——将疗愈的力量归于自然而非人类自身,这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人赋自然以意义”的范式,企鹅的“天真无邪”成为一面镜子,照出来人类“红尘滚滚”的污浊与疲惫。
物象的哲学升华:浮冰、黑冰与冰洞的诗学建构
李立对南极物象的观察,达到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浮冰在他笔下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成为存在状态的隐喻:
“浮冰与浮云,一个基于柔软,一个浮于虚无
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虚空、轻佻、膨胀
飘忽不定,且总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个对比堪称绝妙。浮冰的“基于柔软”暗示着一种根植于现实的坚实——它虽然漂泊,但始终与海洋亲密接触;而浮云的“浮于虚无”则象征着脱离根基的轻浮。这不仅是两种自然物的区别,更是两种人生态度、两种文化品格的分野。浮冰“行事收敛低调/对外展露出来的部分,往往只是冰山一角”,这既是对冰山物理形态的准确描述,也是对东方美学中含蓄、内敛精神的呼应。
黑冰的意象更具哲学深度。这种需要“一万年才能形成”的冰,在海水中呈现黑褐色,打捞出水方显晶莹本色。诗人从中悟出了存在的真谛:
“当雪一次又一次疯狂数落我的时候
寒风,总是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浪
我唯有收缩自己,不做任何徒劳的解释”
这是对误解的深刻体验,更是对坚持的绝妙隐喻。黑冰的“一万年修行”,将个体遭遇置于地质时间的宏大尺度下,瞬间消解了当下的委屈与不平。“雪越是挤兑我,越发激发我的沉静”——这种将外力转化为内力的能力,正是个体精神成熟的标志。而结尾“只有真正想读懂我心思的人/抱起我,就知道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晶莹剔透”,则道出了理解的真义与可贵:真正的理解需要接触、需要拥抱、需要肌肤相亲的认知。
蓝色冰洞的意象则指向认知的陷阱与启示的双重性:“不仅迷惑眼神/有时候还拥抱脚踝”。自然的瑰丽往往与危险并存,人世的温情常常与算计相伴,而人类常常被表象迷惑,陷入看不见的危机。这种对自然复杂性的认知,既避免了简单的浪漫化倾向,也可以将其衍生到人类社会。
时空的折叠艺术:记忆在地理极限处的复活
在南极这个地球的时空尽头,记忆以奇异的方式复活与重构。《大海啊母亲》完成了三重时空的折叠:南极现时的惊涛骇浪、童年记忆里的母亲摇篮、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海洋母神原型。当“大海摇晃着游轮/仿佛摇篮”时,个体生命史与地球演化史通过“摇篮”意象瞬间融通,母亲“那颗心/依然大海般不知疲倦”,则将具体的母爱赋予海洋般永恒的生命力,又将自然的海洋人格化为母亲的怀抱,这种双向隐喻创造了惊人的诗意密度。
《站在南极半岛的甲板上数星星》则构建出一个宇宙尺度上的认同政治。诗人在南极星空辨认出的不是西方天文学传统的星座,而是“袁隆平星”与“屠呦呦星”。这个细节意义深远——即便是在地理和文化的最远端,诗人的精神坐标依然牢牢锚定在中华文明的底座与贡献者之上。这既是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诗意表达,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困境的回应。“越是黑暗的夜,他们散发的光明就越是耀眼”——诗人将科学家比作星辰,既符合其探索宇宙的本质,又赋予其照亮人间的伦理意义。
行吟诗学的当代转型:从审美到行动
李立的“南极行吟”标志着中国行吟诗学的重要转型。传统行吟诗多以“抒情自我”为中心,自然往往是背景或心境投射;但李立的行吟则建立了一种“伦理主体间性”——诗人不再只是孤立的抒情者,而是处于人类与自然、罪责与忏悔、破坏与修复等复杂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
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察视角的转变——从人类中心视角到生态中心视角;其次是情感结构的转变——从审美愉悦到伦理痛苦;最后是诗歌功能的转变——从自我表达向社会介入。在《格里特维肯捕鲸站》中,诗人面对历史遗迹时产生的不是怀古幽情,而是直接的行动冲动:“我突然想代表人类给它们说一声:对不起!”这个“突然”很重要,它表明伦理觉悟不是理性推导的结果,而是直面创伤时的本能反应。
《过德雷克海峡》则将这种诗学提炼为存在哲学:
“谁的人生之路上没有埋伏过几条沟壑
谁能在漂浮不定的尘世,闲庭信步
谁的眼泪如水般清澈见底,且无个中苦涩”
这三个“谁”的排比,将德雷克海峡的风浪普遍化为人类共同的存在境遇。而诗人给出的应对智慧极具东方特色:“举步维艰时不如就地蹲下/有时候吞咽下去的,必须加倍吐出来”。这不是消极退缩,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生存策略。在“当一个时代开始摇晃”的普遍焦虑中,这种强调内敛、沉潜的智慧尤为珍贵。
语言的重力与光:极地写作的修辞特征
南极的极端环境塑造了这组诗独特的语言质地。李立的诗歌语言有一种“冰雪的重力”——既清澈透明,又沉甸甸地压在心间。《鲸的控诉》中“蓝海中汹涌的腥红血色”形成残酷的色彩对比;“雪原上和海底里那些白色骨架”的意象简洁而惊心,“白色”在此不再是纯洁的象征,而是死亡与空洞的证明。
比喻系统呈现惊人的原创性。在《浮冰》中,浮冰被比作“漂泊的缪斯”——将诗歌灵感与自然物象直接等同,暗示真正的诗意不是书房中的冥思,而是天地间的漫游与邂逅。“浮冰清出于水而澈于水”化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赋予其全新的生态意涵:自然物经过时间提炼,可以达到比其源头更纯粹的状态。
节奏控制与内容高度统一。《过合恩角》中急促的短句模仿了风浪的节奏:“雪粒用力地叩敲着玻璃船窗,浪涛的叫阵声/把两只通透的玻璃杯,吓得浑身颤抖”。拟声词“叩敲”“叫阵”与拟人化的“吓得浑身颤抖”相结合,在语言层面再现了合恩角的狂暴。而“大西洋和太平洋选择在此分手,但水们/并没有因此分道扬镳,而是乌合成一股势力”中,“乌合”一词的贬义褒用,暗示了自然力量对人类秩序的漠视与颠覆,也凸显出海洋的巨大威力与生生不息。
行吟传统的现代重构及其文化意义
李立继承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理性,但将其推向全球尺度;他延续了“山水证道”的精神追求,但将“道”的内涵从个人心性扩展至生态伦理;他保持了“即景抒情”的审美传统,但将抒情对象从风光景物延伸到受伤的地球与受苦的生命。
这种重构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至少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在地方感消逝的全球化时代,李立通过极限行吟重构了“地球公民”的具身认知。他的诗歌证明,真正的全球意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以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的身体经验。
第二,在生态危机深化的今天,《南极洲诗抄》提供了一种“创伤书写”的范本。诗歌不再逃避文明的阴暗面,而是直面人类施加于自然的暴力,并通过语言的赎罪效应,尝试愈合人与地球的裂痕。
第三,在诗歌边缘化的现实下,李立展示出诗歌介入公共议题的可能路径。他的诗歌既保持高度的艺术性,又承担沉重的伦理责任;既是个人精神的记录,也是时代病症的诊断。
《南极洲诗抄》的最后一瞥落在合恩角:“更多的桅杆选择/从这里启帆,是阳光面对雾霭总能占据上风”。这个结尾充满象征意味与乐观情绪:尽管航行充满危险,尽管历史血迹斑斑,但启程的勇气本身,就是抵抗现实与重建未来的光源。李立的南极之行,最终启示我们的或许正是这一点——在一切都看似太迟的时代,诗歌仍是那面不屈的帆,语言仍是那束不灭的光,而行吟本身,就是一场永恒的启航,朝向地理尽头,也朝向精神源头,在忏悔与希望之间,寻找人类重新学会栖居于这颗魅力星球的可能路径。
这组诞生于冰雪尽头的诗篇,如同南极本身,将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坐标——它标记着文明的限度,也指示着重生的方向;它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也闪耀着未来的霞光。当李立的诗句在读者心中激起回响,那便是又一场行吟的开始:从纸张走向内心,从语言走向行动,从诗歌走向大地,从此刻走向未来。


李立,著名环球旅行家,环中国大陆边境线自驾行吟第一人,足迹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学批评家喻为“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创世纪》等100多种主流报刊,获博鳌国际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和悉尼国际诗歌奖等十数次。《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诗丛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和报告文学集共7部和英文诗集1部。现居深圳。


吕本怀,60后,笔名清江暮雪,湖南省华容县人,分行为录世,读诗以自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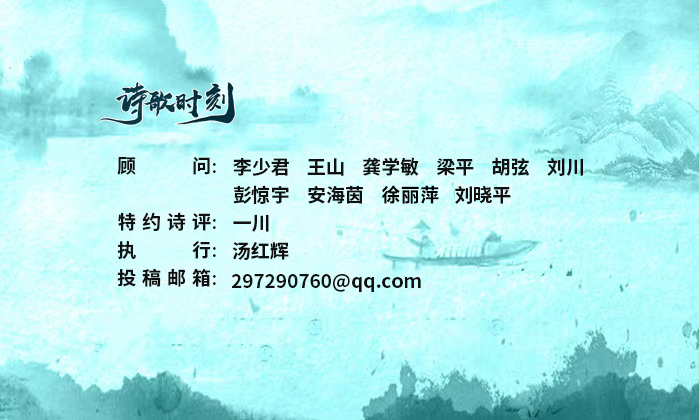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吕本怀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