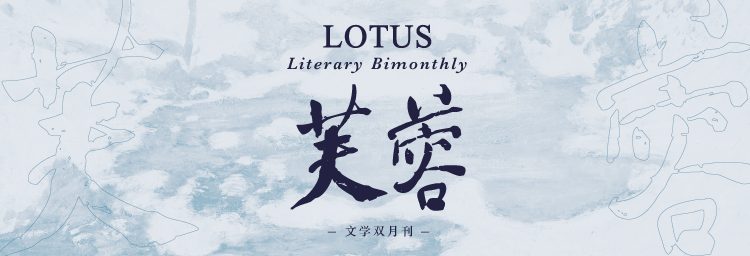

屋檐(中篇小说)
文/罗伟章
很久以前……这样开头,像是讲故事。
其实不是故事,是一段经历。故事是别人的,经历是自己的。是的,很久以前,久到什么时候,我不想说,说出来就显得我很老一样。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州城教书。学校名叫州城第一中学,简称一中,不仅是重点,还是州城老大,城区内的学生,包括各县尖子生,百川归海,都朝这里奔赴。水大了,船多了,艄公也多,职工不算,教师就有接近五百。学校地盘有限,没房子给我们住,就去两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租了一层楼,隔成单间,安置如我这等“新毛团”。那医院很有些历史,是某兵工厂修的,供其内部使用,只有代号,名叫163,我们住进去时,厂子自然早已迁走,医院也在多年前转为民用,而且日渐萧条了,房子大半空着,便用来出租。我们租的那层,以前是病房,睡到半夜,往往听到木楼上响起沉缓的脚步声,还有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呻吟,偶尔,甚至会传出一声惨叫,感觉那惨叫声被封存到时光深处,昏迷了很多个日月,但在某一刻苏醒了。曾经的痛苦以及对痛苦的承受,被褐色的楼房和楼外的林木杂草,保留下来,让我们知晓生命之重。
可对二十出头的人来说,虽免不了青春的惆怅,却也有惆怅里的茂美和轻盈,我们沉浸其中,对闯入梦乡的伤情和病苦,非但不能体味,还心生恐惧。163又相对偏僻,出一中后校门,过条街区,就踏上土路,在土路上走三里地,才到医院门口。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到这段路夜色中的样子。学校要保住老大的位置,既靠师生质量,更靠时间堆积,就像某些大夫,之所以能起死回生,不是手段高强,而是敢下猛药,时间就是我们的猛药。老师实行坐班制,白天坐了,晚上还坐:学生没下晚自习,老师就必须在场。夜里九点半下课后,我们才能去走那两公里。就是走。那时候,我们连自行车也买不起。土路是通向城外的路,并非没有路灯,却昏黄得照不出影子。我们成了没有影子的人。
这也罢了,毕竟可以结伴而行。最糟的是我和梨木月,我教语文,她教英语,间天就有早自习课,六点半开课,动作再快,五点半也得起床。热天还好,那时已有了青色的天光,要是冬天,黑魆魆压下来,走在路上,四周静如往古,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又不像自己的,是从后面跟来的,禁不住频频回首,越回首越怕。加上州城的冬天,早晨爱生大雾,雾从地面涌起,嘶嘶有声,那声音是在“吃”,把本就昏黄的路灯吃了,把路也吃了,我们就像不会游泳的人,眼睛一闭,扑进海里。来辆车也好,车灯能刺破雾障,让我们知道自己还在大地上,可我说的是“那时候”,那时候车很少,大清早出动的车,更少。黏稠的浓雾裹住我们的身体,还钻进我们的脑子。脑子里苍苍茫茫。
唯一的安慰,是突然听到挑担响。那是进城赶早市的农民,他们挑着蔬菜,想抢在城里人清早醒来心情愉悦的时候,卖个好价钱。兄弟们哪,现在的人千里迢迢去追星,想看他们的脸,想听他们的歌,而我们当年,心里最美妙的乐曲,是农民挑担的摇响,还有他们的说话声;若几人同行,他们就说话——说收成,说东家长西家短,对肩上的重担,全然不顾。那重担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一日三餐,是他们梦想中的房子和即将娶进家门的媳妇……我们听着这些,内心踏实,并因此想到,我是个老师,我这么早起来,是去辅导学生,这也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跟农民担子里的菜棵一样,新鲜而饱满。
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委实不多。
农民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同,我们的时间是钟表规定的,农民的时间是鸡鸣、天气和自己的心情规定的,这两种时间往往不能合拍。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一浪一浪地,独自在雾海里漂。如果那天出太阳,雾重,伸手能摸到雾的颗粒,颗粒密集,结成固体,我们就不是漂,是撞,每行一步,都禁不住全身用力,仿佛不这样,就撞不开。如此,待走到学校,就像刚刚卸下重担的驴马。
但这不是最难的。
163虽然早已军转民,却依然遵循旧制——别的不知道,单知道围墙和大门。围墙高过五米,墙端架设电网,或许并不通电,但森森然绕过去,谁也不知道通没通电;大门高过三米,铁栅门,顶上竖着三角矛,晚上十一点半关,早上六点半开,雷打不动。当然也有个门卫,就睡在旁边的小屋里,可以叫他,然而,把全医院叫醒,也叫不醒他。学校去交涉过,估计其他租赁单位也去交涉过,都只是交涉那几天有用,过了,又是老样子。我和梨木月,如果等到六点半才出门,跑步去学校,早自习也已过半,而早自习的铃声刚响,就有教务处的若干员工,拿着本子,分头考勤,这事五分钟内就能做完,意思是,如果你迟到五分钟,考勤的走了,你名字后面没画上“√”,就是旷课。那就完了。当年,市里打造精品名校,全城教师动态组合,一中的可以去二中、三中……二中、三中及更低等次的,可以去一中,根据表现而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跟水不一样,如果人变成了水,就会被看不起。我们是有脸面的人,也是有追求的人,不能被人看不起,因此再难,也不想“动态”到别的学校去。
那怎么办呢?
翻。
叫不开门,就从铁门翻过去。
第一次翻门时,我被自己吓住了。
门口是个浅浅的坡道,手往门上一抓,脚朝门上一搭,铁柱子就在坡上扭动,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这是世间唯一的声音,巨大,并因巨大而令人惊恐。我想到了入室行窃的小偷,也想到了飞檐走壁的大盗。此时此刻,那些与我毫不沾边的角色,成了我自己。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自己,是那样不堪。父母含辛茹苦,送我读书,是希望我成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家里增光添彩,没想到读出个小偷,读出个大盗。这让我涌起一丝悲伤。我立即把手松开,把脚放下,又去旁边打门,边打门边叫“师傅”。门口有盏大灯,可那道门是瞎的,门里是否有一个“师傅”,我也全不知情。打门的声音,叫师傅的声音,由平静而愤怒,由愤怒而无奈,由无奈而乞求,回答你的,都是无声的静默。与此同时,听到啪的一声,抽在脊梁上。那是时间的鞭子。焦急掩盖了疼痛,赶快撤步回来,又走到铁门边。动手动脚之前,先朝上望,望见了铁矛,也望见了挑在铁矛上的破碎的天空。
实话说,那时候,我完全没想到梨木月。
直到有一天上午,我从政教处领了粉笔出来,见梨木月也来领粉笔。她腓骨处的裤脚上,有片血迹,血迹上端,露出个蛇头似的小洞。分明是铁矛戳的。数九寒天,都穿着毛裤,却还是戳透了皮肉。早自习和第一堂正课之间,只有四十分钟,即使她放弃早餐,跑回去换裤子,也怕来不及,因此便将就了。
虽猜出原委,但我还是问了一句,咋啦?她笑一笑,没啥呀。可话音刚落,她猛然间双手捂脸。她的脸很小,手却不小,这一捂,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只看见泪水从指缝间迸出来。那泪水泛着浅浅的紫光。或许是太阳照过来的缘故。她整个人,还有她的泪水,都跟阳光一样静。然后她跑向厕所。政教处旁边,有个厕所。我没动。我像是在等着她哭出来。但没有,依然是安静的声音。好一阵过去,才是哗哗的水响。她要洗去脸上的泪水,还要擦去裤子上的血迹。
她是个讲究人,特别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

罗伟章,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风和微风》,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曾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五佳、《南方周末》好书五佳、春风悦读榜白银图书、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好书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罗伟章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