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锋诗学的未来向度
——论子非花《崭新的时刻》的汉语新境
文/秦风
“真正的先锋,是词语在虚无悬崖上的纵身一跃,是于存在的废墟中重新指认光晕的勇气。”子非花的新诗选《崭新的时刻》,正是在汉语诗歌的断裂带上点燃词语引信、爆破时间容器的先锋之作。它以其凌厉的实验锋芒、深邃的未来意识,以及对中西诗学资源的创造性熔铸,不仅标识出诗人个体创作的崭新高度,更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上,烙印了一道指向未来的、不可磨灭的先锋路标。同时也是其宣言“诗歌是直接抵达人类永恒的宿命感的一种方式”的激烈实践,是在“崭新的时刻”这一命名的宣示下,对存在本相的深度勘探与诗学重构。
一、词语“暴动”与现实坍缩:超现实主义的当代回响
子非花的先锋性,首先表现为一场针对日常语言逻辑的、蓄谋已久的词语暴动。他拒绝平滑的抒情与澄明的叙事,转而探索词语内部的断裂、歧义与生成潜能,将现实置于超现实主义的炼金炉中,淬炼出令人惊悸的意象表征。
意象嫁接的暴力与诗性
“当早晨抛出一条水迹”(《崭新的时刻之一——光影》)——时间实体“早晨”被赋予投掷的动能,“水迹”成为被抛出的绳索,瞬间连接起夜的深渊与昼的苏醒。这一“抛”的动作,撕裂了时间平滑的表皮,暴露出其内部的断裂与张力。紧接着,“昨夜的痕迹依然在井喷:啤酒,残渣,碎裂和眼泪”,记忆的伤痕以“井喷”般的暴力姿态涌现,与“抛出水迹”的早晨形成猛烈撞击。这并非简单的隐喻,而是布勒东所推崇的“意象最随意的嫁接”,它强行打通了潜意识与意识、过去与当下的壁垒,释放出被理性秩序压抑的能量。
“日光咔嚓咔嚓吃着斑马线”(《童年》)——日光被赋予动物性的咀嚼能力,“斑马线”成为被吞噬的客体。这一超现实的饕餮图景,将日常街景瞬间异化为充满威胁性的梦幻剧场。它超越了象征主义对物象的依附,直抵超现实主义追求的“绝对现实”——那个潜藏于表象之下,由梦幻与无意识法则统治的、更真实也更荒诞的领域。这种书写,是词语对现实的一次成功“离间”,迫使读者在惊愕中重新审视被习惯遮蔽的世界本相。
“牛奶在表白”(《崭新的时刻之二——日常生活》)——沉默的物质(牛奶)被赋予言说的冲动与主体性。这是典型的“物之自动书写”,物挣脱了被观察、被描述的被动地位,获得了内在的生命意志与表达欲望。它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暗示着一个万物有灵、众声喧哗的隐秘宇宙。正如布勒东所言:“美将是痉挛性的,否则就不存在。”子非花通过这种痉挛性的意象组合,释放了词语与物象中被囚禁的野性力量。
空间的异化与存在的悬置
“让空间离奇的失踪”(《崭新的时刻之四——雨夜》)——空间不再是稳固的容器,而成为可被操控、甚至“失踪”的流体。这种对空间确定性的消解,呼应了后现代地理学对空间流动性与建构性的认知。当“灯火一下子被黑夜吸走——最后的闪烁!”,光与暗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黑夜成为一种具有吞噬力的实体,空间感在瞬间的坍缩中荡然无存。这种体验,精准地捕捉了现代人在高速流动、信息爆炸时代所普遍感受到的“存在的晕眩”与无根性。
“身影不断地被搬离、拉扯、撕碎/直到消失”“我们在人间的位置不停地挪移”(《崭新的时刻之七——搬离》)——个体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碾压下,其存在的痕迹如同“小小痕迹膨胀成一个水泡/然后,爆裂,消失”。子非花以近乎残酷的精确性,描绘了后现代语境下主体性的碎片化与流动性。这种“挪移”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是精神与身份的漂移,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个体生存的悬浮感与认同危机。
子非花的超现实主义实践,并非对西方流派的简单模仿,而是植根于自身对当下生存经验的深切体察。他让“雨滴在不间断的应答中/过滤出隐藏的细节”(《崭新的时刻之四——雨夜》),正是在这种超现实的透镜下,世界显露出其被日常逻辑掩盖的、充满荒诞关联与神秘回响的深层肌理。
二、碎屑诗学与微观显影:后现代境遇下的存在勘探
子非花的诗作尤重“在存在的裂缝处点亮烛火”。他诗学的核心密码之一,便是对“碎屑”的执着凝视与深度赋魅。他将目光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整体性幻象上移开,聚焦于那些被忽略、被遗弃的“世界的碎屑,最微小的单元”(《崭新的时刻之三——四月》),从中勘探存在的深渊,并试图打捞救赎的微光。这形成了他独特的“碎屑本体论”。
日常的碎屑与生命的涌动
“面包碎屑发酵”“五颜六色的小颗粒在太阳里爆炸”(《崭新的时刻之二——日常生活》)——面包碎屑的“发酵”不再是微不足道的物理变化,而是微观生命意志的无声涌动与能量转化;“小颗粒”的“爆炸”,则将平庸的市井景象瞬间提升为一场微观宇宙的壮丽庆典。利奥塔所倡导的“微小叙事”合法性,在此得到诗意的确证。子非花赋予这些“生活的碎屑”以戏剧性甚至史诗感,宣告了日常生活的诗性现象学。
“你大口大口吃着眼泪/酸辛刺骨”——情感的碎屑(眼泪)被具象化为被迫吞咽的苦涩食物,“酸辛刺骨”将味觉转化为尖锐的体感。生活的重负与伤痛,以如此直接、生理性的方式呈现,具有强烈的痛感冲击力。这是对生存艰辛不加粉饰的裸呈。
存在的碎屑与消逝的挽歌
《崭新的时刻之六——木头的故事》(献给逝者)是“碎屑诗学”的巅峰呈现:“你内心的碎屑,全部的柔软/在刹那完成”。个体生命最核心、最私密的情感与记忆,被凝聚为“碎屑”与“柔软”,并在死亡的临界点“刹那完成”——这是一种在消逝中达成的生命结晶。而“只有温度,偶尔的上升/在木头,温暖的底部”,则是子非花对抗虚无最有力的诗性武器。逝者存在的证明,不是宏大的纪念碑,而是残留在木头(象征物/载体)中的、偶尔上升的“温度”。这微弱的余温,是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哲学的诗意回响,也是在本雅明“灵晕”消散的时代,对生命痕迹最卑微也最坚韧的守护。木头作为“温暖的标记”,其“底部”上升的温度,成为连接生与死、存在与消逝的理念电流。
“喧嚣碎了一地/安静突然从中心弹跳出来”——世界的“喧嚣”最终崩解为“碎了一地”的狼藉,而真正的“安静”并非死寂,而是从这破碎的中心“弹跳出来”的、充满生命韧性的力量。这揭示了子非花“碎屑诗学”的核心:在彻底解构(碎)之后,蕴含某种更具生命力的、意外生成的(弹跳)可能性。破碎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起点。
“碎屑”中的神性与危险
子非花清醒地认识到碎屑的双重性:“孕育着无所不在的危险” 与 “你们是最卓越的精灵”(《崭新的时刻之三——四月》)。尘埃般的“世界碎屑”,既是构成世界的基础,也潜藏着毁灭性的力量;那些被遗忘的“小零碎”,在特定的时刻(“喷火游戏中”)又能焕发出神性的光辉(“最卓越的精灵”)。这种辩证的认知,使得他的“碎屑诗学”避免了沉溺于琐碎或滑向虚无,反而在微观的深渊里,勘探到存在的复杂性与救赎的潜能。他将后现代的解构碎片,锻造成了承载存在之重与生命之光的容器。
三、时空炼金术与“崭新时刻”的创生:未来诗学的维度
“崭新的时刻”不仅是一个诗题,更是子非花诗学探索的终极命题和核心方法。他通过对时空经验的先锋性重构,实践着指向未来的诗学构想,展现出强烈的未来性维度。
时间的液态化、碎裂与多维体验
“事件冲出全新的直线/抵达问候”(《崭新的时刻之一——光影》)——时间被赋予“冲出”的爆发力,其“直线”的轨迹被暴力打破,“抵达”的不是终点,而是充满开放性的“问候”。这瓦解了牛顿式的绝对时间观,呼应了柏格森的“绵延”说与德勒兹的“块茎”时间论。时间不再是均质、线性的河流,而是充满异质瞬间、爆发力与可能性的立体网络。
“水滴空中碎,水滴水中碎/水滴镜中碎”(《崭新的时刻之三——四月》)——时间(水滴)在三种不同的介质/空间(空、水、镜象征的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幻象空间)中碎裂,呈现出时间经验的多维性与非连续性。镜中之“碎”尤其关键,它暗示了时间在自我观照(反思、记忆)中的内在分裂与异化。这是对时间本质的深度勘探。
“觉察,总是在早晨/第一根脉管直插天空/把意识注满”(《崭新的时刻之五——早晨》)——子非花执着于捕捉意识觉醒的巅峰“时刻”(“觉察”)。这个“早晨”被描绘为“脉管直插天空”般具有穿刺力和灌注感的体验。这是对“此刻”的极致体验与永恒化尝试,试图将流动的时间凝结为饱满的、充满创造力的瞬间。
空间的流动、召唤与语言建构
“让空间离奇的失踪/再召唤一些新叶”(《崭新的时刻之四——雨夜》)——空间成为可被“失踪”(解构)和“召唤”(建构)的对象。“召唤新叶”不仅是对自然生命的呼唤,更是通过语言行动(“让”“召唤”)对空间进行诗性的重构。这指向了一种语言的创世潜能:诗歌可以成为建构新型感知空间的方式。“街道,哦,盛满生活/驶向明日”——街道作为容器“盛满”流动的生活,并具有“驶向明日”的动势。空间在此被动态化、未来化,成为承载生活之流并指向未来的通道。
“攥住时间颗粒”,在流逝中锚定存在
“掌纹急切地/攥住时间颗粒”(《崭新的时刻之五——早晨》)——这是子非花对抗时间流逝、创造“崭新时刻”的核心意象。流动的、不可捉摸的时间,被想象为可被“攥住”的实体“颗粒”。掌纹(个体生命的独特印记)与时间颗粒的接触,象征着个体在时间洪流中奋力锚定自身存在的悲壮努力。“急切地”一词,道出了这种努力的紧张感与迫切性。这种在语言的炼金术中“攥住”时间、创造意义的行动,正是诗歌作为“直接抵达人类永恒的宿命感的一种方式”的具体实践。他的诗歌,就是在词语的针孔里,捕捉那些均匀流动的“细小的可能性”,并让它们“冲出全新的直线”,最终“抵达问候”——一种对存在本身的确认与呼应。
子非花的时间、空间炼金术,并非组合概念,而是源于对“人世匆匆”这一根本处境的深刻体认(《崭新的时刻之六——木头的故事》)。他的先锋性在于,他拒绝被动接受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固化,而是以词语为武器,主动地解构、重塑时空经验,在语言的实验室里,不断进行着创造“崭新时刻”的悲壮实验。
四、东西融贯:在汉语的根脉上重构汉语新境
子非花的实验性以其先锋姿态的根基,深深扎入汉语诗学的传统土壤,同时又大胆嫁接、消化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资源与艺术手法,实现了大胆的中西化合,为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新范式。
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与禅意升华
“母亲的小院/阳光飞驰”(《崭新的时刻之三——四月》)—— 寥寥几字,物象(小院、阳光)与极具动感的“飞驰”结合,瞬间营造出温暖静谧又饱含时光飞逝之感的意境。其凝练与留白深得古典诗词精髓,“飞驰”则赋予传统意象以强烈的现代性张力,在静穆中注入时间的动感与生命的流逝感。
“安静突然从中心弹跳出来”(《崭新的时刻之六——木头的故事》)——以动写静,“弹跳”一词将抽象的“安静”具象化为充满生命力的、瞬间爆发的存在。这种悖论修辞,在出人意表中抵达了禅宗“动中之静”“空故纳万境”的妙悟,体现了东方智慧对“空无”与“生机”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
象征的深度与跨文化共振
“电”成为核心象征物:“你从墙壁上挖一些电/让石头颤栗/让树木惊恐地行走”。无形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电”,被具象化为可“挖”的物质(类似采矿),并赋予其搅动自然秩序(石头颤栗)、赋予非生命以生命意志(树木行走)的神奇/恐怖力量。这既令人联想到西方象征主义(如波德莱尔对“恶之花”的发掘)对抽象力量的具象化表达,其内核又融入了东方“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和萨满教的“附灵”观念。对工业力量的魔幻书写,既包含批判性的间离(布莱希特),又隐含了某种敬畏。
“水滴空中碎,水滴水中碎,水滴镜中碎”——对“水滴”这一意象在不同空间/介质中碎裂的反复咏叹,其形式上的复沓与执着,带有《诗经》重章叠句的韵味,而其探索时间/存在本质的深度,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如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形成深层次的共振。
语言的悖论、生成性与东方玄思
“让答案充满水”(《崭新的时刻之四——雨夜》)—— “答案”本应清晰、确定、固态,却“充满水”——流动、无形、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悖论式表达,瓦解了传统认知对确定性的追求,指向一种液态的、生成的、充满可能性的真理观。这既是对后现代哲学(如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的诗意呼应,其表达方式本身又带有东方玄学(如道家对“恍惚”“混沌”的推崇)的思辨色彩。
“从春天偷渡来的一些嘴吐出麻雀,树枝和空气”(《偷渡》)——将季节更替(春天)想象为一个能“偷渡”、拥有“嘴”并能“吐出”万物的神秘主体。这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想象,将抽象的季节概念神话化、人格化,既是对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诗性反动(接近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其思维方式又可追溯至《山海经》等古典文本中对自然神的崇拜与描述。
形式探索与边界融合
子非花在组诗内部灵活运用了不同体式。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将散文化的叙事与诗性的突转穿插其间。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松散还是凝练,其语言内核都保持着高度的诗性浓度、先锋锐度与意象张力。这种自由本身也是先锋精神的一种体现。
子非花成功地将西方先锋诗学的锐利刀锋(超现实的意象爆破、后现代的解构策略、象征的深度开掘),锻打在汉语诗学浑厚沉实的砧板之上(古典的意境追求、禅宗的妙悟、语言的凝练与张力)。他既非简单的“拿来主义”,也非沉闷的传统守成,而是在东西诗学的激烈碰撞与深度交融中,淬炼出属于当代汉语的、具有鲜明先锋品质和未来向度的崭新诗性语言。他的实践,证明了汉语在消化最前沿的文学思想后,依然能保持并焕发其独特的魅力与生命力。
五、重构与救赎的临界:在语言僭越之上的崭新出发
“回到事物本身”的诗性转化。子非花的实验性,创新了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进一步体现在他对物质世界近乎粒子化的显微观察。他捕捉“世界的碎屑,最微小的单元”,这些平凡物象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意志与表达冲动。碎屑的发酵不再是单纯的物理过程,而是成为微观生命意志的觉醒仪式;在物中灌注情感温度、在消逝中锚定存在的书写,体现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智慧,也彰显了诗歌作为“直接抵达人类永恒的宿命感的一种方式”的本体价值。由此,子非花似乎在构建一种独特的“碎屑本体论”:世界由无限增殖的碎屑构成,诗歌的任务并非整合或升华,而是深入这些碎屑的缝隙,勘探其内部蕴藏的“无所不在的危险”与“最卓越的精灵”的双重性。
“词语在自身内部的自我搏斗与救赎”。子非花最刺目的特点是语言僭越,将沉默的物质推至言说的主体位置。这种书写策略,超越了象征主义对物象的隐喻性依附,更趋近于超现实主义的“物之自动书写”——物质在诗的场域中获得了自身的语言与灵魂。子非花让我们在词语的震荡中,重新聆听“寂静突然从中心弹跳出来”的声响,在“崭新的时刻”的命名中,确认诗歌作为人类抵抗虚无、锚定存在的最古老也最崭新的仪式。子非花的语言实验具有强烈的未来性指向。时间的多重碎裂,揭示了其非连续性与多维性,充满强烈的未来主义动能感与解构色彩。这既是对整体性幻象的祛魅,也是对微观宇宙无限可能性的勘探。这种在消逝中锚定生命余温的书写,是子非花对后现代虚无最有力的诗性抵抗,强烈地体现了生存的痛感与诗意的救赎:在碎屑中重建光晕。“让答案充满水”这种悖论式表达,瓦解了传统认知的确定性,指向一种液态的、生成性的真理观,既呼应了后现代哲学对“元叙事”的解构,其表达方式又带有东方玄思的韵味。
“身体知觉与世界关系”的本体转向。子非花突破了“身体主义”(庞蒂)知觉体验,更擅长通过意象的奇异嫁接,构建极具超现实冲击力的视觉图景。这是对后现代主义“表征危机”的深刻回应——知觉体验不再能稳定地指涉世界,它自身就是不断生成、不断逃逸的谜团。充满想象力的表达,打破了传统咏物抒怀的窠臼,在象征与超现实之间开辟了新的感知通道。生活日常瞬间蜕变为吞噬性的超现实剧场。这种意象暴力拆解了现实的逻辑链条,迫使读者进入布朗肖所谓的“文学空间”——一个由词语自身法则统治的异托邦。他更擅长捕捉物质世界隐秘的“灵晕”与怪诞的生命意志。这种书写,超越了象征主义对物象的隐喻依附,抵达了超现实主义追求的“绝对现实”——那个潜藏于表象之下、由梦幻与无意识法则统治的更高真实。子非花让“雨滴在不间断的应答中/过滤出隐藏的细节”,正是在这种超现实的透镜下,世界显露出其荒诞、破碎却又充满内在关联的隐秘肌理。
“在深渊边缘与日常废墟上重建光晕”。子非花的诗歌先锋性,体现为一种在语言的极限处挑战虚无、在存在的废墟上重建意义的悲壮努力。当“火车在跑步/而人世匆匆”,子非花以他锋利而充满温度的诗行,创造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的时刻”。《崭新的时刻》以其锐利的先锋意识、深刻的实验精神与饱含未来感的语言实践,他拒绝在词语光滑的表面滑行,而是执拗地掘进存在的碎屑与光晕的临界地带,在时空的废墟上重建诗歌的意象与意义。他竭力在碎片的深渊之上架设词语之桥,在光晕消散处点燃语言之火——它标记的不仅是子非花个人诗学的“崭新时刻”,更是汉语诗歌在当代境遇中,寻求突破与重生的一个耀眼的路标。《崭新的时刻》是当代诗歌的一次“崭新出发”,闪亮了汉语诗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崭新路径与无限可能。必将启示后来者继续在词语的深渊与光晕的交界处,寻找那刺破永恒的诗性光芒。
文化接骨的错位与可能。子非花先锋诗的价值恰恰在于暴露并企图拼接当代诗歌的“断骨”。在先锋性的实验中,诗人应对词语的“施暴”避免滑向失控,更加注重意象内在逻辑的深度焊接,在感官错位的表层,继续深入掘进潜意识的真实,预防意象的密集繁殖冲淡本体论重量危险。关键的困境在于诗学本体的悬置,汉语的骨相(虚实相生、意在言外)与移植的先锋技法(暴力嫁接、意识流)仍在激烈博弈,更需如阿尔托所言“灼烧存在的假面”。先锋诗歌的未来,或在于“僭越”之后的“重建”,诗性弥合在表现与再现,解构与重构之间词语的缝隙,让词语再次建立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即世界”)。子非花的探索已撕开一道词语的窄门,未来诗学之路在于:让碎屑的锋利更深地楔入存在之核(如《木头的故事》中“温度在底部上升”的深沉),让超现实的惊奇多维度地关照于对“光晕消散”的诊断(如“灯火被黑夜吸走”的惊悚),最终在汉语的“气息底部”(诗人自用语)完成对西方文化诗学的消化与转生——唯有如此,词语的暴动才能真正刺破未来的暗幕,“崭新的时刻”,即是未来。


秦风,本名蒲建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文学博士。著有诗集《独步苍茫》《风斯在下》,《四川诗人》诗刊社执行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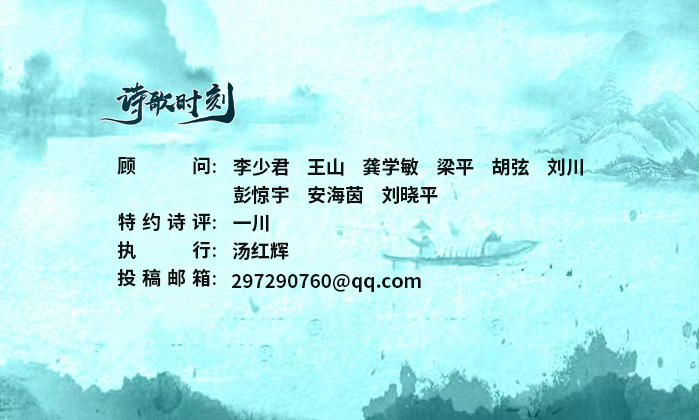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秦风
编辑:史凌松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