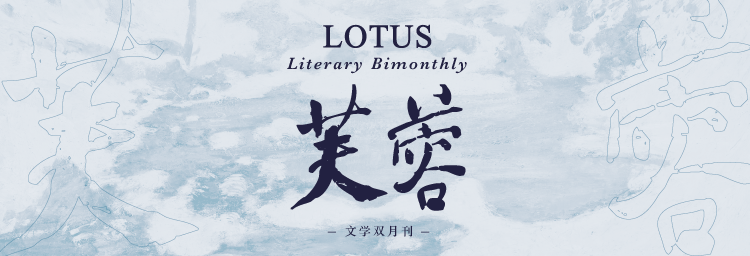

温州记
文/汗漫
问舟与拍岸
用整棵树刳制而成的这一独木舟,长约十米,中间宽,两端微扬如巨鸟展翅,姿态很美。美,就是力量。美的法则,暗通于力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原理。这一叶舟,大约可乘坐二十人,扬桨击浪,到瓯江对岸去,到瓯江上游龙泉、下游东海去,到温瑞塘河这一条人工开凿的古老河流里去。舟来桨往,打猎、捕鱼、游荡、采莲、结亲、经商、对垒、征伐、送葬……
当一叶舟划过,岸边的水痕线微涨,而后平复,像少年的春心被拍打着,激动三秒而后平复。
温州亦即东瓯或曰永嘉,水系密集,如人体中的毛细血管输送生机。舟、舟子、舟歌,繁盛不息。于是,建设起这一座龙舟博物馆,合乎逻辑。博物馆外,一泓碧水,是不久前落幕的亚运会划船比赛场址。博物馆即当时的赛事服务中心,这一功能转型,同样合于逻辑。
在本地生长、写作的友人周吉敏,陪我在博物馆内穿行,看各时代的龙舟,从实物,到模型,再到龙舟延展成的艺术品,或龙舟贯穿其中的风俗仪式图景:成人礼、婚礼、祭礼……
任何一种事物,都能焕发出全世界,类似从任何一人起笔,都可以叙述全人类。一叶舟,同样有能力激起我对万千人事的怀想。比如山水诗人谢灵运。他遭南朝刘宋政权贬放,来永嘉亦即温州任太守,乘坐一艘客船,那显然是眼前这一独木舟的升级版。到任后,屡屡去山陬水湄游荡,河流细微处,乘独木舟为宜——“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在《游赤石进帆海》一诗中,他写到的“虚舟”,就是独木舟。舟行桨响,搅乱周围的水草和鱼虾。
“我们这里能工巧匠多,与水多土地少有关。造船匠、银匠、木匠、锁匠、画匠、泥瓦匠……手艺人到处都是,甚至远赴异国他乡谋生。你看,彩纸楼船里的那些面人,就是用糯米捏的呢,多逼真……”吉敏感叹。我看看她,白脸长发大眼睛,也像糯米捏的呢。“你,也是捏笔杆的手艺人。”我说,她笑:“我写的字,流传多远,打问号。这一叶舟,可是来自东晋的呢!1960年,在建筑施工中发现了它,地下埋藏一千六百多年了,还像是新造的一样,有斧痕,类似作家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我笑了。在用电脑写作的时代,毛笔或钢笔的修改痕迹,荡然无存,文本的来路就显得可疑——手迹的圈画涂抹里,暴露出一颗心的狂喜、剧痛或犹豫。
手摸这一独木舟,坚卓如初。它所经历的东晋以后各时代,风吹云散。不知谢灵运坐过它、见过它没有?问舟舟不语。
温州朔门前,新开掘出土的三艘古船,谢灵运肯定没有坐过见过。它们分别是北宋、南宋时期的产物。吉敏引领我到瓯江边,俯视地平面下深约二十米处,古船的隔舱板与船舷犹在,如同巨人们溃散不全的遗骸。为何沉没?问船船不语。本地史料未曾言及。这一发掘工程仍在进行中。沉船周围,清理出九座码头、干栏式建筑群、数以百吨计的浩瀚瓷器碎片遗存,它们表明:瓯江上游著名的龙泉青瓷,向海外和内陆输出时的路线,与此地密切相关。古港与古船,首次以实物证明,东瓯或曰永嘉亦即温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这一遗址,发现于近年的越江隧道工程。考古队的探杆,在滩涂积淀而成的江岸地区下,竟触及坚硬的存在!遂确认:众多密集有序的条石,在泥土深处,连绵而成一条由低而高的道路。意味着,一座港口湮灭于此。发掘中,相继有食物、乐器等遗迹显现,表明周边存在酒肆餐馆、歌管楼台,商贾、水手、官吏、士兵、文人、少年、囚犯、烟花女子……闪现其间。
“前辈写字人失职了,竟没有记录这一港口的存在。即便写了,大约也是空泛抒情、咏叹一番,缺乏具体、写实的方位描述。一支笔,还没有考古队的一根探杆有力呢。”我嘀咕。吉敏捂嘴笑:“我数学就不太好。”我倒是数学系毕业的人,也走了感性强于理性的一途,思辨力、行动力都很匮乏。
这一古港遗址,可上溯至宋元明清数代,与当下瓯江隔着一条滨江大道。滩涂渐次成陆,流量不减,流速与东晋时代相比更迅疾,江水拍岸声就更加响亮激越吧?
三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在江边广场上相互追逐,像低低飞掠的江鸥。
当一艘巨轮驶过江面,岸边的水痕线微涨两厘米,而后平复,像少年的春心被拍打着,激动三秒而后平复。不知巨轮上承载着什么。是谢灵运熟悉的瓯柑、瓯绣、雁荡山铁皮石斛、乐清细纹刻纸、泰顺三杯香茶叶、龙泉宝剑、松阳红糖,也可能是他不知道的、温州制造的现代工业产品:智能胶印机、减震器、断路器、电磁阀、真空包装机……我知道,这巨轮,与龙舟博物馆里的独木舟有关,与古港遗址里的沉船有关。任何一艘船的出现,绝非破空而至,必由其他船、树木、钢铁、焊花……促动而成。正如,任何一个人的出现,绝非破空而至,乃由他人、场景、事件……促动而成。类似陶渊明和田园,促动谢灵运;谢灵运和山水,促动孟浩然、王维……
眼前,流水中央一沙洲,就是著名的江心屿,谢灵运最早发现其胜景,作《登江中孤屿》。可见,这一沙洲当时尚未命名。从中,他看见孤屿般的自我:“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高傲自赏,符合“旧时王谢”子弟的身份和气质。两座宋塔,一东一西,使江心屿像留恋东瓯之美而迟迟未出发的双桅船。那宋塔,也起着灯塔作用,在暮色中点亮灯盏,为进出瓯江口的水手,提供信心和勇气。
多年前,我曾登上江心屿,像步入一卷史册,成为其中渺小的省略号:文公祠、宋高宗仓皇登临处、英国领事馆旧址、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江心屿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面对它,心潮何不似江潮,拍胸拍岸两相高。这一孤屿密布各种形制的古亭:谢公亭、问舟亭、临清亭、来雪亭、卓公亭、归鹤亭、花柳古亭、独凉亭、怀青亭、妙高亭……一个亭子,承载一段记忆、一种情愫。亭者,停也。匆忙的路人啊,请你停一停,想一想来路再奔前程,像一叶舟、一艘船,祝愿你顺水且顺风。
我喜欢那一座问舟亭,与孟浩然有关。他曾迢迢来访谢灵运遗踪,过钱塘江,作《渡浙江问舟中人》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至瓯江,又咏叹:“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问舟复问舟,可见其心情之急切、情感之灼热。
癸卯秋,我乘高铁自上海来访,还能算是孟浩然的同舟客吗?算。当然算。情志相通,风雨与共,怎能不是同舟客?有无数前贤以才华照破孤穷,后生晚辈何其有幸!我只要打开山水诗、中国画,随时到永嘉。
一千七百年前,一个名为郭璞的人,选择这一方山海江河交汇之地,建城,先后名之“东瓯”“永嘉”“温州”。一次更名,意味着版图与建制的一次调整。但每次命名,均保持汉语美感:东方大海边这一盏瓯,可盛三餐、新茶和美酒;永远保持良善和卓越;温暖之州雁徘徊……
本文,将把三个不同时期的地名混用不分——此地已把上述三种美感,融通如一,如何能分?
(节选自2024年第5期《芙蓉》汗漫的散文《温州记》)

汗漫,诗人,散文家。现居上海。著有诗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琦君散文奖、雨花文学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汗漫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